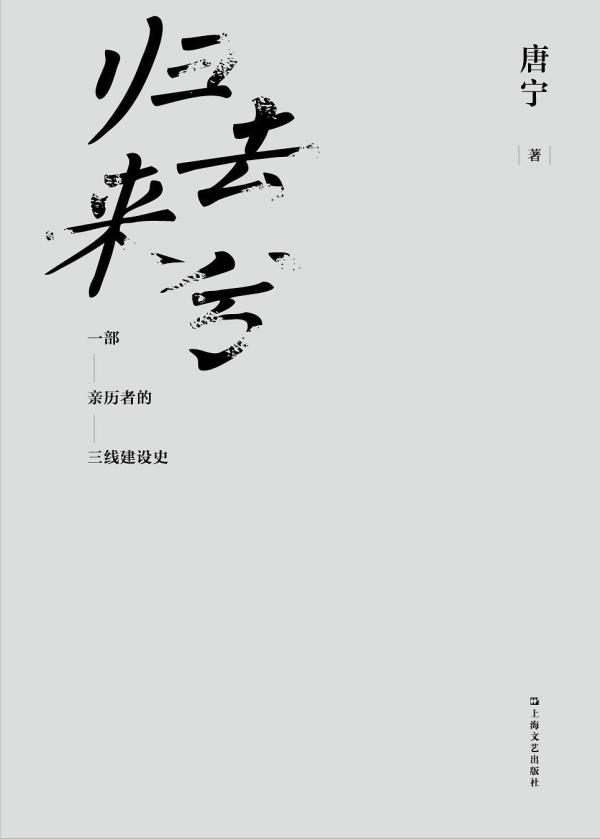当我偶然翻到《归去来兮》后记里的一句话,我决定将这本书从头至尾读完。
那是唐宁三年采访写作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在此期间,她父亲罹患重病。父亲弥留之际,脸上所流露的“深厚的仁慈与护佑”,深深触动了陪护的女儿。由此,唐宁体察了父亲不惜命也要将她赶回书桌前的用心——那里有一众与父亲同龄的受访者,他们有的已经离世,有的已丧失记忆。她写道:“随着一代人的年迈体弱和离去,那些故事也将随风而逝。”
估算起来,唐宁应该是《归去来兮》中“迁二代”的同龄人,或许稍长一些。她的写作,其实是在兑现对父辈的承诺。可以想象她在书桌前的情景,电脑开启,现世的纷扰被屏蔽了,而她独自走向过往,去追逐即将随风而逝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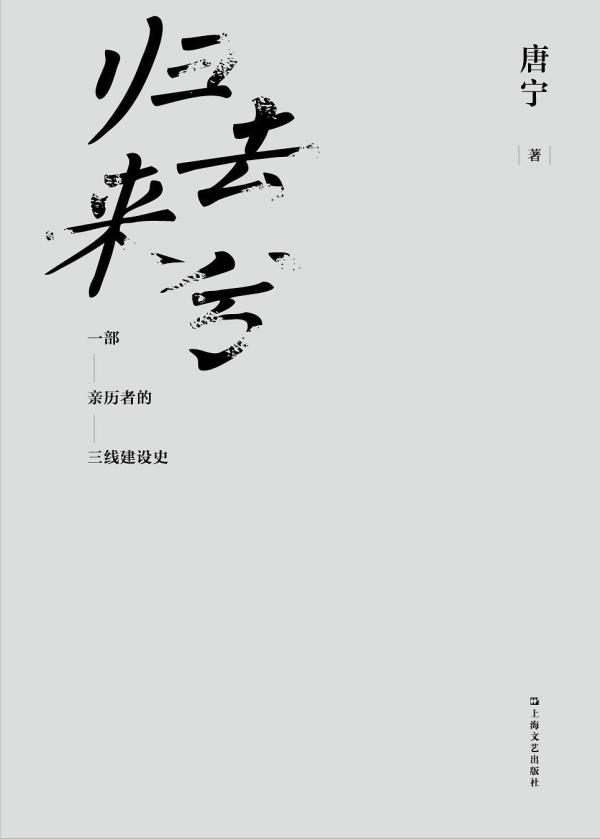
《归去来兮》
故事的第一推动力,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准确说是1964年,毛泽东在《关于工业的发展问题(初稿)》上的一句批示:“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于是建设大三线的战略决策出台。于是,上千万人的命运被改变。
在传统话语里,关于这场工业大迁徙的描述多少有些罗曼蒂克。那是规模空前,史无前例的布局;那是志在千里,四海为家的豪迈;那是在偏僻的崇山俊岭中开山平地,安营扎寨的阵势;那是刘伯温“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的预言;那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壮怀激越……
从中,你分明能读出一种国家被当作画布擘划时的气派 。话虽如此,另一重事理却无法回避。常识告诉我们,往往是国家的命题越宏大,个人的际遇越渺小。譬如,当“被改变命运者”的基数是千万时,作为分子的“1”便犹如恒河里的沙粒,何足挂齿?哪怕他(她)的故事同样鲜活生动,哪怕他(她)的经历足够跌宕起伏。
好在唐宁躬身把部分沙粒捡拾起来,庄重的、敬畏的,又是审慎克制的。我想说的是,这种姿态值得人们脱帽致敬。
当然,唐宁写作《归去来兮》没有包罗万象的企图。她只是截取了大三线建设时代洪流中的一脉,由上海西迁的304个项目、411家工厂、9.2万职工里的一个典型样本:上海光学仪器厂拆分援建的贵阳新添光学仪器厂。你可以将此视作从杨浦黄兴路到贵阳新添寨的一次时空连线,铺就这根线的,是西迁800位职工和更多随迁家属的口述、笔记、回忆录、档案材料,以及不知所云的碎碎念。
这一个个“无一虚构”的人物,是恒河沙数里的“1”。渺小的、不足挂齿的,也是丰富的、百分百的。所谓每一个看似平凡的个体,对于他(她)自己而言,都有着波澜壮阔的遭逢。大潮中的一叶浮萍,令人动容之处就在于它不可知不可测不可把握的前程。厂址勘察小组的飞机在强气流中失控、起落架发生故障时,场景是惊险的;先行营造厂房的工人突然接到“一律留下、安家落户”的指令时,表情是惊愕的;工厂西迁不到两年,中国首台潜艇指挥潜望镜便完成研制安装,成就让人惊叹;而2002年,曾经的明星企业——新天光学公司破产资产拍卖的消息登上《贵州商报》的头条,其间落差叫人惊诧。
上述种种,或许是《归去来兮》中蕴含戏剧冲突的一幕幕,而经历这一切人们,有着真实的兴奋、快慰、苦恼、彷徨和幻想。唐宁将他们的故事打捞,拼接成一段完整的人生。她要为他们立传。
以支内花名册上排序第一的葛民治为代表的“迁一代”已经或者即将谢幕,他们中部分回沪的老人,在每年续保时,甚至要手持当日报纸拍照以证明自己存活。以内地第六代导演王小帅为代表的“迁二代”用作品诠释着父辈的爱与怕。王小帅的父亲、随迁家属王家驹,晚年为了宽慰觉得连累自己的妻子,挂在嘴边的话是:“是你的错吗?那是大洪流啊。”
用不可抗力来解释施加于自身的创痛,是对那个时代的理解与宽容。我相信,理解出自本意,宽容也发自内心。岁月是最好的劝降者。那些当年举家西行的人们,很多年后当他们东归回到故乡才发现:让他们感到陌生的故乡,而他们无比熟悉的竟是他乡。此时此刻,乡关何处已不是问题,因为岁月本身就是回家的路。
人的一生,无非就是无数次的出发与回归,离散与团聚。人与人关系的结局,恐怕离散还更多一些。而唐宁犹如一位有心的主妇,以“新天厂”的名义将终将离散的人们聚拢在一起,共同诉说着属于他们的往事。这多么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