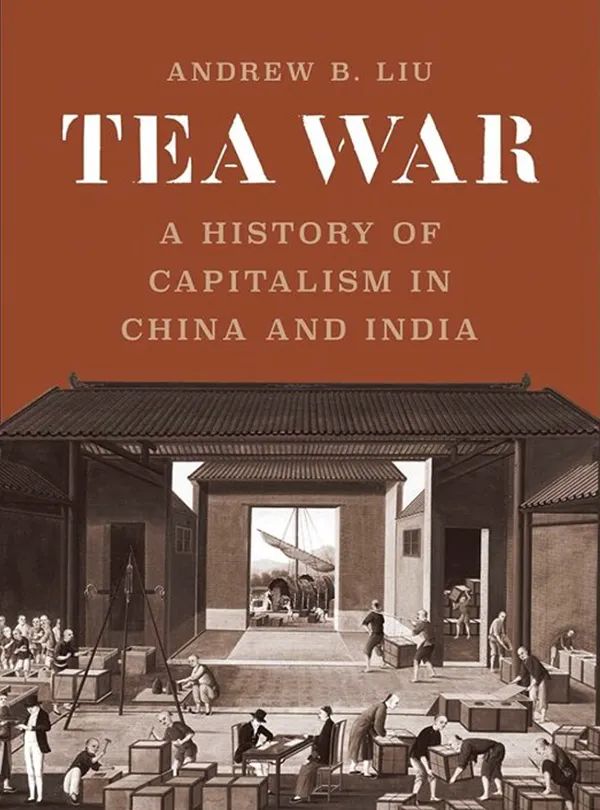
《茶叶战争》(2020)书封
文|Andrew Liu
译|苏子滢
1
茶叶,最早由荷兰商人在进口到欧洲,但到了17世纪晚期,由国家垄断支持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主导后人所说的“广东贸易(Canton Trade)”。在18世纪的黄金时代,茶叶是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卓越地位的象征。欧洲贵族和资产阶级将它推崇为一种独特的亚洲商品,是所谓“中国风”这一类更广的东方异域艺术、瓷器、丝绸的潮流的最新时尚。茶叶象征着古老的天朝帝国的物质辉煌,年轻的欧洲列强羡慕它,并试图效仿。
在整个18世纪,普通英国家庭对混合了糖和牛奶的茶叶消费量增加了五倍,利润飙升。对茶叶的需求如此强烈,以至于催生出一个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其税收占英国政府收入的十分之一,为英国向南亚扩张提供了担保。正如东印度公司的审计长在1830年宣称的:“印度确实完全依赖于中国贸易的利润。”
英国人提供不了什么中国商人想购买的商品。因此,到了18世纪晚期,英国殖民官员开始把印度鸦片走私到港口城市广东(现称广州)。当道光帝(从1820至1850年统治中国)试图强制执行存在已久的禁毒令,英国官员和商人便打着捍卫贸易自由的旗号宣战。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中压倒性的胜利,标志着如今在中国被称为“屈辱的世纪”的开始。简而言之,茶帮助建立了大英帝国,也触发了中国和清朝的长期衰落。按照民族主义者的说法,直到共产党崛起并在1949年取得胜利,当初的军事失败和殖民主义耻辱才得以被洗清。
鸦片战争
中国种植茶树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种在茶农的精心照料下产出的神奇作物。而英国装备着铁船、强大的火炮,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后盾,加入了这场竞赛。对于欧洲帝国和现代亚洲的学者来说,恰恰是当西方的崛起已经牢固地确立时,中国的茶叶贸易开始从人们的视野中褪去。
但事实上,鸦片战争后的茶叶贸易能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些重要部分。放眼北大西洋以外的世界,尤其是19世纪中国的茶叶产区,现代资本主义持续发展,其特点是灵活且面向全球。即使在中国内地,我们也发现资本积累既不依赖于引人注目的技术创新,也不依赖于特定的阶级关系,而是体现在全球竞争这一新的社会逻辑中。毕竟,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施行的中国通商口岸制度并不意味着茶产业的消亡,而是它的扩张。
在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随着欧洲大陆和美国的买家也加入英国的行列,茶叶出口量增长得甚至更迅速了。到了20世纪初(第一次系统调查时),茶叶贸易雇佣的人数——从农村到通商口岸的农民家庭、妇女、儿童、季节性工人和搬运工——比中国早期的任何城市产业都多。同时,印度殖民地、锡兰、日本、台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出现了竞争产业。当大多数历史学说把注意力转向了别处,中国的茶叶贸易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增长,海外纠葛也越来越深。
中国的茶叶贸易实际上代表了中国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切入点。茶叶被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交换鸦片、秘鲁银、加勒比糖、英国纺织品和缅甸大米。这种活动构成了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分工,由殖民世界经济作物的区域专业化推动——或者,正如杜波依斯(W.E.B.Du Bois)在他的书《黑人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1935)中所说:一个“跨越中国、印度、南海和整个非洲的黑暗而广阔的人类劳动之海;在西印度群岛、中美洲和美国……孕育出全世界的原材料和奢侈品——棉花、羊毛、咖啡、茶叶……”这种全球分工也以动态和新颖的方式重塑了中国农村。
2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专家将中国视为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他们通常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工业化和发明,等同于燃煤发动机、钢铁厂和化学机械工程的进步等引人注目的标志。这些技术突破区分了“西方”和“其他国家”,正是它们在中国——以及亚洲大部分地区——的缺席,使其成为“前资本主义的”。
粗略地看,19世纪中国茶叶贸易的确证实了这一观点,因为商人和农民沿用了传统的工具和技术。唐朝(618-907)的僧侣是最早定期出售茶叶的人。早期的办法是劳动力密集型的,比如把茶叶压缩成茶饼,或者把它磨成细粉(这些方法在今天仍然存在,如云南普洱茶和日本抹茶)。人们熟悉的烘焙散茶的方式,首次有记载是1539年,距离茶叶传向西方只隔了数十年。绿茶品种产自安徽省东南部的徽州,记录显示绿茶烘焙的发明可以追溯到隆庆年间(1567-72年),该方法南传至福建西北部的武夷山,那里的僧人烘制出了一种新的半氧化黑色茶叶,被称为“红茶”。
根据20世纪的考察,散茶生产的第一阶段是在农民家里进行的,主要是妇女,她们种植、采摘茶叶,轻度烘烤以防止过度氧化。这些家庭会在他们烧饭的厨房里加工茶叶,之后把茶叶装在大袋子运到当地市场,按照杠杆作用,讨价还价的商人知道他们只需等待农民找上门,因为装袋的茶叶会慢慢腐烂。商人会在他们自己的临时作坊里——通常是自己家里的空房间,或是租来的小房子——完成精炼的工序。他们从本地和邻近的郡县雇佣的季节性临时工,完成筛选、碾压、烘烤和包装的工作。他们的工具并不比竹篮和柴炉更复杂。
清代福建附近茶叶种植园
工具和技术的发展向来是现代工业的标志,但我们不应一味关注它们,而忽略对人类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分析。戴維·兰德斯(David Landes)这位备受尊敬的的欧洲工业革命历史学家,对技术革新十分看重,他声称在中华帝国,提高生产率的动因是“未知的”。相反,“忙碌,对自己的工作的不懈努力,是最大的美德”。作为证明,他在《时间革命》(Revolution in Time,1983)一书中指出,和欧洲相比,中国缺少能精确测量和调节生产力的机械钟和计时设备。
中国的历史却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找出特定的尖端技术,也能发现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盛行——或者如韦伯所说(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时间就是金钱”的信念的盛行。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已经是这样:一个商业化的农业社会迅速被推入一个新规模的全球工业市场,为它生产、与它竞争。我们可以把中国茶产区实际采用的特殊计时方法看做一个清晰的例证,这种计时方法远非最先进,但它无疑是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
3
1810年代,撒米尔·鲍尔(Samuel Ball)在广东南部港口任东印度公司的检察官。尽管从未亲眼目睹茶叶生产,但他从线人那里了解到,在安徽农村,管理人员会用一种奇特的、看似有异国情调的计时设备来管理茶叶生产:一种按固定速度缓慢燃烧的香。这些香粗细各异,但一般设计为能持续燃烧40分钟。用燃香或烧绳头计时的办法可以追溯至5世纪的中国和日本,这与古代世界其他地方用沙漏和水钟计时的原理相同。零碎的证据表明,在现代中国,熏香也被用来调控采煤和农田灌溉的时间。
鲍尔在《论中国茶叶的种植和制作》(1848)中写道,中国的茶商用燃香来记数茶叶烘焙的各个阶段的时间。他写道,“烘焙的时间是通过一种叫“香烛”的工具来调控的。为什么制茶过程必须记录时间?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工业与加勒比地区新生的大规模工业蔗糖种植园有许多共同点,后者也在大致同一时期发展成熟。根据美国人类学家文思理(Sidney Mintz)在《甜与权力》(1985)一书中的说法,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这些大型庄园的工业时间规划。首先,甘蔗通常在一天内就会变质,因此存在着要及时处理它的自然压力;其次,种植者感到在市场竞争的社会压力下,需要将生产成本降至最低。在世界的另一端,中国中部的山谷中,也能观察到类似的动力。
由于茶叶是产自土地的易腐自然物,它的质量取决于及时的烘烤、筛选和揉捻。在鲍尔和商人谈话时,为了保证最终产品的自然物理品质,商人对制茶的工作进行了监控。以时间单位为指导原则,个别工人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各个步骤的时长。鲍尔写道:“尽管烤制的时长是以‘一炷香’为单位控制的,但这种计时工具主要是作为指导,而不是规则。”他们给工人们提供茶叶样品,工人可以自行决定延长或缩短烘焙时间,直到茶叶呈现出恰当的色泽和外观,就像按食谱烹饪那样。
我们也知道,在鲍尔的叙述之后的几十年间,安徽南部地区用来计时的熏香也开始被用来管理劳动活动。徽州歙县商人蒋耀华(Jiang Yaohua,音译)在屯溪集镇经营一家生意兴隆的茶叶加工厂,每年春天他都把数千磅茶叶运往上海。在他的茶叶制作手册中,他提到炒茶工人要先在凉爽的地方搅拌茶叶,直到“烧完一炷香的八成”,然后将茶叶压入炉中加热“半炷香”的时间。最后,工人把锅直接放在火上加热二又四分之三炷香的时间。
蒋氏的手册中简述的茶叶制作流程,和鲍尔之前的说法一致,它关注如何保持产品的高质量标准。然而,手册还设计了一套长达18炷香,也就是12小时的完整的工作日安排。蒋氏安排了一个时间表,为了在他雇佣的劳动力的体力允许的条件下,将生产活动量最大化。几十年后,一位名叫范和钧的社会调查者来到徽州茶产区,对这种18炷香的工作日安排的影响做出评论。他写道,“那时,一整天的烘焙工作会耗尽肌肉的全部力量。范和钧还注意到,烧香也被用来调整雇工的工资:
以四篮茶叶为一个班次,熟练工人可以赚到四个单位的工资,每个单位约15分钱。每班次只能烤两篮茶的非熟练工人,在18炷香的时间内只能挣两个单位的工资。
按照这个排得满当当时间表,香被用来让工人们不停地工作,鲍尔那时观察到的灵活调整时间的态度已经几乎不存在。
因此,虽然徽商延续了烧香这种古老的计时法,这种操作的性质却已经改变。起初,制茶者关心的是生产质量最好的产品,也就是说,他们关注的茶消费。而最后,商人以让生产最大化为目的,用烧香管理劳动活动。计时不再只在茶叶加工的自然过程中,发挥被动作用;相反,抽象的时间单位开始积极地调节劳动者的身体活动。这不像兰德斯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前工业化的“忙碌”,而是以提高人类劳动的生产率为目的的有指向性的冲动。
为了尽可能地延长劳动时间、提高效率,徽州的工头把工人的身体逼到了极限,甚至超出了极限。范和钧写道,炒茶的人“被要求靠在火炉边”,“太阳和炉子一起对付着工人”。1930年代屯溪的茶叶厂被称为“蒸笼”, 范和钧指出:“由于劳动太过繁重,工人们有时会中暑倒下,甚至倒地而死。”
伦敦东印度公司
4
商人为什么如此拼命地使唤工人?简而言之,是因为竞争。茶叶出口额在19世纪末飙升,1886年达到了2.95亿英镑的峰值。然而早在19世纪60年代末,茶叶价格就开始回落了,这反映了中国茶叶生产商的供应过剩。在通商口岸开放后的最初几十年里,蒋耀华的父亲蒋文钻(JiangWenzuan,音译)把茶叶生意从广东转移到上海,在那里苦苦挣扎。他写信给他的妾说:“家族企业正处于危机中;它正在消失得一点不剩。”到了19世纪末,东印度和锡兰的新竞争摧毁了中国的贸易。
起初,商人不知道是什么打击了他们。正如一位清朝官员在1887年所写的:“贸易繁忙的时候,人们似乎迷失了方向,好像身在云雾中”。到了1903年,上海的报告可能会说,“现在锡兰生产了这么多茶叶……中国经销商就更难卖出他们的产品了”。面对这些竞争对手,耀华和其他茶商都想方设法地降低成本。
武夷山的红茶产区也实行类似的劳动纪律。和徽州一样,工具和技术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变化,但一味关注技术连续性,使人误解了对生产者而言的生产和经济生活的性质。来自邻省江西的劳工承包商,被称作“包头”,他们甚至没有用古老的燃香计时法。相反,他们通过一系列习俗和神话来约束这些工人,其中许多工人都是来自经济萧条的上饶县的兼职农民。1930年代的研究员林馥泉注意到了这些传统神话,谴责它们是迷信的神秘主义。
例如,林馥泉指出,武夷山的包头每天都会毫无预兆地宣布停工抽烟休息。休息时,工贼会把茶篮交给包头,包头当场称重并记录重量。这种意想不到的“秘密称重”( 暗称)在技术上很简单,但其功能和徽州的香类似。通过在同一个时间点上暂停采茶,包头确立起一个“投入”的基准量,用于衡量每个工人的“产出”,从而了解他们的相对劳动效率。包头没有用机械装置计时,但他们仍然有简单有效的方法来奖励采茶最多的工人,惩罚采得最少的工人。林馥泉清楚地看到:“采茶劳动的报酬是按效率原则确定的,奖惩的规则十分明确。”即使不采用机械钟,也能把这种新的生产制度强加给工人。
茶叶采下后,下午要放在户外氧化,使它们呈现出特别的黑色。晚上,工人从小睡中被叫醒,被指派到室内的工场,在严密的监视下炒茶、揉搓和筛选茶叶。包头依然会根据操作速度奖励或惩罚分拣工。速度快的工人一班能拣完七篮子的茶叶,速度慢的工人只能拣完四篮。事实上,动作最慢的工人要在油灯下分拣茶叶,从黄昏干到黎明,黎明时新一轮的户外采摘又要开始。一首流行于工人间的工作歌,唱出了这种秩序的严苛无情:
清明过了谷雨边,
想起崇安真可怜;
日复一日树下过,
三夜没有两夜眠。
5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只有当土地、劳动力和原材料彻底异化并商品化的情况,现代资本主义才能腾飞,也就是说,它需要共有财产的私有化,以及原先社会秩序(如农民耕种、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和自由人才发现自己完全受制于市场压力,或者更乐观地说,只有到这时,企业才能最有效地配置资源。这些步骤被认为是培养现代工业时间观念(充分体现在机械钟上),以形塑工业生产和工作条件的必要步骤。
然而,在中国的茶叶贸易中,农民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茶树,在私人住宅里运营作坊。工人要么是不拿报酬的家庭成员,要么是季节性雇佣的流动劳工。中国茶叶生产的现状与传统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共识不一致——那种共识是根据欧美的历史经验得出的。那些学者把无产阶级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体,与农奴、奴隶和农民这些传统人物形象(殖民地形象)对立起来。但在中国农村的茶产区,商人和管理者为了应对国际价格的下跌,也开始用一种在精神上和实质上都是工业性的方式,衡量和调控雇员的工作时间。
茶叶贸易中的这些场景告诉我们,19世纪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已经被市场逻辑激活,其市场化程度甚至比当代人觉察到的更多。清帝国晚期的中国作家,倾向于把农村描绘为独立小农农场的集合,但经济的现状比这更复杂。蒋耀华的农村茶叶作坊,要依赖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的金融家的贷款。对于种茶的家庭来说,茶叶平均占他们总收入的60%,即使这样,也不足以维持他们的温饱。为了熬过冬天,徽州的家庭经常会借贷粮食,作为交换,他们会提前以来年春天的茶叶作为抵押。粗略地看,他们出售的茶叶似乎是他们自己的土地的产物,因此是他们的财产。但事实上,在茶被采下之前,茶叶就已经被卖给了茶贩了。因此,尽管福建总督扁宝坻(1824-1893)等清朝官员极力劝说这些家庭放弃经济作物,回归自给自足的农业生活,这些家庭还是无法仅为自己的需要而种植。为了生存,他们需要为市场生产,进而与整个亚洲的许多其他人竞争。
这种原始的社会形式与现代经济动力的结合,也是在现代早期的全盛时期,除茶叶以外的许多其他商品的生产特征。糖和棉花是由受奴役的非洲人种植的,纺织品是由英国受胁迫的年轻妇女织成的,鸦片则由担负重税的巴特那(译注:东北印度)农民提供。
至于印度阿萨姆邦的殖民茶产业——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那里的英国种植园主依赖于一种劳动契约制,按照官方的说法,这种制度是几个世纪以来“主仆”法律的延伸。这些安排不是自由的。尽管如此,监工还是对法律禁止的“苦力”进行压榨,从事开垦土地、采摘和烘焙的工作,这些苦力是从印度东部招来的,主要是妇女。英国种植园主大卫·克罗尔(David Crole)在《茶》(Tea,1897)一书中评论道:
苦力现在的劳动量比二、三十年前多得多。比如,与过去的需求量相比,锄地等工作的日常任务(nirrik)的工作量增加了25%至30%。
种植园主和监工赢得了生产率的提高,一部分是由于巧妙的组织策略,一部分是通过对不自由劳动力的殴打、鞭打和监视。亚洲各地的这些巨大的努力和转变,使茶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水的消费最广泛的饮料——这一地位延续至今。
在中国,和在印度以及世界大部分地区一样,资本主义经常通过改变“传统”技术的用途占据上风。比如在中国的茶叶贸易中,燃香计时的办法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但是设计一种独特的方式使它们融入现代积累机制这一点,是新颖的。
最近几十年的全球化已经清楚表明,资本主义扩张的程度始终是不均衡的,它依赖于阻力最小的道路,吸纳一切现成的技术、材料和人员。如今,全球分工不仅有资本密集型、纵向一体化的企业,也包括(尤其是在后殖民世界)劳动密集型工厂的横向网络——有些甚至就设立在客厅中——它们在形式上类似于中国早期的茶叶作坊。正是因为劳动密集性,这些汽车、纺织品和电子产品工厂实际上比它们在本世纪中叶的前身更便宜、更灵活、更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这种战略推动了东亚在20世纪后期的“崛起”,从那时起它就已经传入扩张中的中国,中国政府正试图恢复国家从“中国风”时代起的早期世界地位。
自20世纪后期以来,亚洲故事一直是全球政治经济转型的基础,但在重点关注少数欧美知识分子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叙述中,它经常被边缘化。相应地,这些叙述试图解释中国的崛起,却没有更深入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是如何与该地区长期交织的。如果我们希望讲述一个更整体化的故事,那么一个重要的起点便是认识到中国——以及更广泛的亚洲——不仅仅是18世纪资本主义在欧洲诞生的旁观者。这里的人民从一开始就协助推动了遍布全球的资本积累循环,尤其是通过茶叶贸易,这产生了导致扩张和加速的客观压力。这些与工业世界的其他地区共有的社会动态,往往被忽视了,因为它们的表现方式是本地化和独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