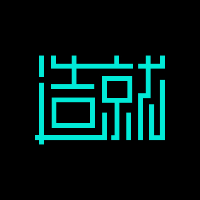「4月7日著名城市经济学家Richard Florida在City Lab发表了关于新冠病毒在美国的城市分布,从经济地理视角阐述了密度和传染病流行的关系。」
城市经济学家Richard Florida
新冠病毒(Covid-19)在全球肆虐,波及了亚洲、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城市:先是武汉,再是米兰和马德里,现在又是西雅图、纽约、底特律和新奥尔良。似乎没有哪里可以幸免。但是有些城市看起来更容易出现新冠病毒的破坏性的传播,也更易受到病毒最潜伏性影响(译者注:无症状感染)的冲击。
许多评论家在观察了病毒传播轨迹后,将疫情加剧归咎为密度(译者注:人口聚集)。他们将新冠病毒与“9·11恐怖袭击”和2008年经济危机一起视作让人们从密集、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迁出的推动力,认为病毒有效地为过去几十年的回归城市运动 (the back-to-the-city movement) 画上了句号。
与从前的流行病一样,人口密度是造成传染病大流行的一个因素。人口的聚集为我们的大城市带来了更多创新性和更高的生产率,也使城市在面对传染病时更加脆弱。
然而,密度可能只是决定不同地方面对病毒会有多么易感的众多关键因素之一。新冠病毒已经在全球扎根,不同类型的地方都遭受了沉重打击。第一类是如纽约和伦敦这类有着大流量游客、来自全球的人口和密集的居住区的大型超级城市。另一类是是如武汉、底特律以及意大利北部的工业中心,它们与供应链紧密相连。还有如意大利、瑞士和法国的滑雪场或科罗拉多洛矶山脉的滑雪胜地等全球旅游地区。而在较小的社区中,新冠病毒的目标是疗养院和殡仪馆,以及如同海上小型密集城市一般的游轮。
谈论城市和病毒的时候不存在简单的、以一概全的解释。重要的是从可能加快或限制病毒传播的地方的特征中区分出不幸最先出现病毒传播的多发地点。城市之间有很多方面的不同——人口规模、年龄、教育水平、富裕程度、宗教信仰、人们的工作类型、社会资本水平等。以上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都可能影响城市对新冠病毒的易感程度。
人们常常认为早期的城市封锁和社会隔离措施——比如居家办公、学校停课以及就地隔离——能够帮助某些城市遏制大流行病蔓延。这些措施无疑在使感染人数曲线变平缓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很多亚洲高密度城市如新加坡、首尔、香港和东京可能容易遭受以后病毒爆发的袭击,但它们的确已经成功控制了疫情爆发。但是这些城市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特征使某些地方更易感或更不易感。
虽然这一流行病是全球性的,基于 Jed Kolko 、 Joe Cortright 和 Bill Bishop 等的研究,利用《纽约时报》开发的数据,我这里主要分析Covid-19在美国的地理分布情况。
在介绍我的研究之前,申明以下几点。疫情仍处于早期阶段,由于测试和其他因素的变化,病毒传播的相关数据仍然参差不齐。我们也还只能收集有限的城市样本,其中有些城市正处于疫情最严重的阶段,有的处于中期,还有更多可能还未受影响的城市。此外,由于本分析重点放在美国的数据上,所以可能会忽略全球其他城市的相关因素。
根据Kolko提供的截至4月1日按各县类型所统计的Covid-19病死率的数据(见下表):毫无疑问,大城市所属的县死亡率最高;从郊区到乡村地区的病死率排序也和密度高低相符。
大城市所属的县死亡率最高;从郊区到乡村地区的病死率排序也和密度高低相符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乡村地区可以幸免。根据《每日邮报》的Bill Bishop和 Tim Marena 的分析,尽管乡村的总体确诊率和死亡率都低得多,但事实上,新冠病毒正以和在城市中同样的速度在美国乡村传播。根据他们的分析,新冠病毒在部分乡村休闲地区造成了特别严重的打击。这些地方通常有着大规模的自然休闲设施——湖泊和海滨,美丽的乡村或滑雪场,它们吸引了许多富有的游客。这类地区包括科罗拉多州的鹰县和皮特金县,犹他州的萨米特县和爱达荷州的布莱恩县。据《华盛顿邮报》称,本周早些时候,位于爱达荷州滑雪带的核心地区伍德河谷有192例病例并有2例死亡。该地区总人口仅有2.2万,其确诊率比纽约市更高。
总体而言,根据Bishop和Marena的分析,乡村休闲县的新冠肺炎患病率是其他乡村县的2.5倍以上。
Kolko分析中提供了另外一张表。其显示了美国城市中Covid-19死亡率最高的地区。(虽然各地的确诊检验有区别,死亡数仍是反映Covid-19疫情影响的最合适标准。)
美国城市中Covid-19死亡率最高的地区
以上十个城市中有四个大型城市:新奥尔良、纽约、西雅图和底特律。但表中其余的城市并未重视密度对病毒传播的影响。在佐治亚州的小城市奥尔巴尼中,病毒就是通过两场葬礼传播的。
至于密度本身,Kolko的分析发现,密度和美国各县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显著相关。但密度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他的分析还发现,在人口老龄化、弱势群体占比较高、气候较寒冷潮湿的县,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更高。但需要注意,这一分析仅针对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更密集的城市在抑制疫情蔓延方面能取得更多成功。
但即使在美国,使城市更易传播病毒的也不是密度本身,而是人口密度的类型以及其对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因为即使在人口密集的地方,也能为人们提供单独的社会隔离的空间。简而言之,富裕的人口密集区和贫困的人口密集区有巨大区别:富裕城市的人们有地方隔离,可以远程工作,所有食物及其他需求都能递送上门;而在贫瘠的地区,人们不得不上街,去商店,和其他人一起挤公交车。
这种密度区别在纽约市的病毒地理分布中非常明显:受到Covid-19打击最严重的不是非常密集的曼哈顿,而是密度较小的外城区,如布朗克斯、皇后区以及密度更低的史坦顿岛。
密度越高, 传播病毒越快,一般发生在多户或多代家庭中、工厂中、前线的有密切身体接触的服务工作中或是公共场所。高密度也是1918年大流感在匹兹堡和费城的工业中心里的工人阶级社区肆虐的原因。
我们继续追踪病毒的传播时,除了密度外,还有很多其他值得我们进一步考虑的因素。两个明显的因素是人口年龄以及健康史,如吸烟、肥胖、糖尿病和心脏病。密切关注病毒在贫困和弱势群体社区的不公平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也希望关注不同工作种类之间的区别:能够进行远程工作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和在一线工作的诸如医护人员、派送员、杂货店员等容易感染上病毒的劳动力的比例。我们也可能发现,人们聚在一起做礼拜之类的频繁的宗教活动或多世代家庭占比高的地区也更利于病毒的传播。在美国这样的各州分立的国家,讨论政治取向的重要性是很有趣:蓝色州(支持民主党)及其城市在社会隔离方面往往比红色州(支持共和党)及其城市行动得快得多。
我们可能发现,想要在城市中鼓励的一些事情,比如紧密的社会联系和公民资本,会使城市更加脆弱。人口统计学家 Lyman Stone 在推特上称,“当一切都说清楚并采取了措施之后,我们会看到,新冠病毒对于有较高社会资本的人而言有特殊的致命性。”相对地,人们批评城市的一些方面(例如丁克、少子化以及有孩子的家庭较少)也可能有效保护了城市,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孩子有可能成为疾病传播的媒介。
这些因素中的一些也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旧金山作为仅次于纽约的美国第二密集的城市,在缓解疫情方面似乎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也许不仅是因为旧金山比其他地方更早地进行了封锁,虽然这确实有效。这也可能是由于儿童的人口占比较少,能居家远程办公的工作者占比更多,且是美国教育水平最高的地方之一。这一系列因素使旧金山比底特律、新奥尔良甚至纽约这些在社会阶层和人口统计线有显著差异的城市更能够抵抗病毒。
Covid-19大流行病对我们的地理和城市的全面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令人不安的是,新冠病毒似乎加剧了我们现有的经济、地理分界的某些关键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