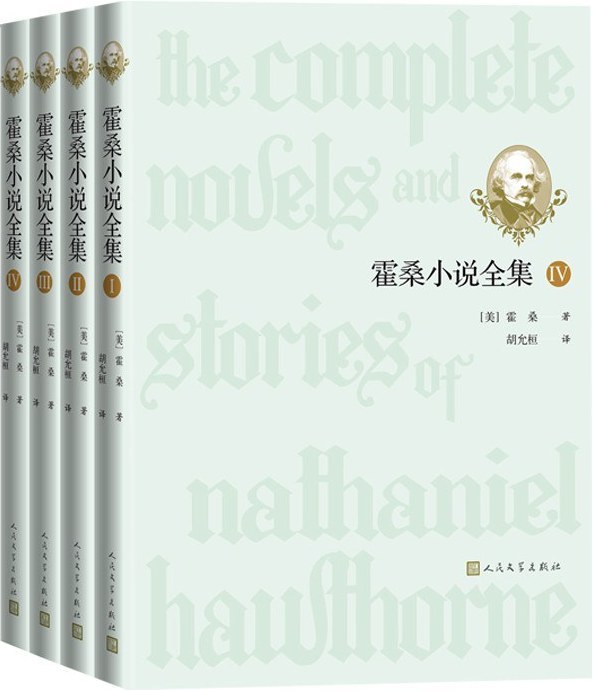
小说家霍桑(1804-1864)是美国“黑暗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以《红字》《七角楼房》《福谷传奇》和《玉石雕像》等四大罗曼司闻名于世。此外,霍桑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也卓有建树,有短篇“圣手”之美誉。他的短篇佳构多收录于《故事重述》(1837)、《古屋青苔》(1846)和《雪影》(1852)等三部故事集中,其中若干题材涉及巫术、变形以及万灵药水等超自然现象,无疑是对社会现实的扭曲反映。这类故事的主人公大多生性善良,不乏艺术天赋,但由于身处恶劣环境之中,往往难以逃脱悲剧性结局。同时代的小说家梅尔维尔曾评价霍桑隐居“古屋”(Old Manse)期间创作的短篇小说“笼罩在黑暗之中,因而分外黑暗”,并指明作家的本意并非神异其事,而是影射现实——从这个角度看,此类短篇皆可归为“寓言”。
《雪影》(The Snow-Image)取材于新英格兰普通家庭生活:家中两个孩子与雪花形成的雪孩一道在户外快乐玩耍,宽厚仁慈的父亲担心雪孩受冻,坚持将其带回家中炉前烘烤,雪孩立时化为一滩水渍。这是霍桑笔下最浅显的儿童寓言:作家一方面以清丽的笔触描绘自然景物,一方面讴歌人性之纯洁善良。然而,故事的结局却点明本文寓意所在:美国社会(及民众)最为推崇的务实精神与心灵世界格格不入——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天敌。由于缺乏艺术的想象力和感知力,他们往往在无意之中扼杀美和艺术。
《海德格尔医生的实验》(Dr. Heidegger’s Experiment)同样是一则寓言。故事中的医生邀请五位老友,前来品尝他最新的科学发明——一种能让人返老还童的青春泉水。在场的所有人都信誓旦旦,保证重获青春后将开始崭新的生活。可当他们喝下泉水、如愿重回青春岁月后,立刻又恢复了旧时的恶习本性。最后,众人在一番抢夺中失手打碎水壶,于是一场美梦宣告破碎。这一故事体现了霍桑短篇一贯的主题,即“人性恶”无处不在:它可能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被掩藏,然而一旦时机成熟,它便会故态复萌——永远也无法根除。
相比而言,《拉帕齐尼的女儿》(Rappaccini’s Daughter)则极具现实关怀。拉帕齐尼医生是一位科学家,毕生醉心于植物的毒性研究,以献身科学为志业。为了取得独步古今的科学成就,他选择以女儿作为实验对象——她自幼便与世隔绝,每日徘徊于携带毒株的百花园中,浑身沾满毒性。尽管她本人百毒莫侵,但她自身携带的病毒却足以令人致命。由此,她无法正常与人交往——试图亲近她的医科大学生最终被吓跑,她本人也因误服“解药”导致毒性发作而死(或说她因爱情幻灭而死于心碎)。故事里的医生寓意冷酷无情的科技力量:这种力量强大到足以改变大自然的规律,却无力挽回年轻可爱的生命。对人类而言,科技的疯狂发展到底是福是祸?作者的态度不言而喻。
《美的艺术家》(The Artist of the Beautiful)探讨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寓意极为深刻。故事男主沃伦达是一名钟表学徒,但后来沉醉于创造美的艺术品,遭师傅嫌弃,被逐出师门。师妹是他的梦中情人,对他一直不离不弃,最终却被迫嫁给另一位师兄——此人务实能干,深得师傅青睐,但其人性情愚钝,完全不能理解美为何物。师妹婚后不久即产下一子,家庭和睦,其乐融融,而沃伦达依然沉迷于艺术创造,被周围人视为走火入魔的“疯子艺术家”。在故事结尾,他携带迟到的结婚礼物——一只会飞的机械蝴蝶——来师妹家中拜访,众人皆夸赞这一艺术品精美绝伦、巧夺天工,但同时又惋惜它“似乎没什么用”。说话之间,机械蝴蝶被嬉闹的孩童损毁。沃伦达平静地与师妹一家告别,因为他深知:在美国这片贫瘠的土壤,追寻美的艺术家的确派不上任何用场。
小说中“粗野的手指”折断机械蝴蝶“翱翔的翅膀”这一意象本身便充满寓意,正如霍桑在另一部名篇《卓恩的木像》(Drowne’s Wooden Image)中感慨的那样:“谁会在一个美国佬机械师身上寻找现代的皮格马利翁(Pygmalion)!”从这个意义上看,本篇的主题既体现了美的艺术与世俗生活的分离,又反映出艺术与现实的冲突和隔绝。文中师傅一家及邻人对沃伦达的鄙夷不屑和冷嘲热讽充分证明:艺术/艺术家在实用主义大行其道的美国难以容身。根据王佐良先生在《照澜集》的看法,霍桑这类“寓言式的写法”,无疑极大地“扩充了短篇小说的领域”。
在上述“寓言式”写法的短篇小说中,发表于1852年的《羽毛冠》(Feathertop)尤发人深省。故事讲述一个由女巫创造并赋予生命的稻草人,在历经繁华虚荣的梦境后幡然悔悟,决定亲手了结自己的生命。本文故事情节并不复杂,语言也质朴明快,但由于其中人物形象及其寓意高度契合,小说由此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效果,在文学评论界备受赞誉。美国著名文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断言,《羽毛冠》“以不同凡响的力量,表现了一种与我们的世界相交的现实秩序,它既不完全和尘世相同,又和尘世相去不远,因此它或许是我们语言中一篇无与伦比之作”。
故事中的这个稻草人,是新英格兰最厉害的女巫里格比妈妈的作品。女巫本想做个普通稻草人,去吓吓玉米地里偷吃的乌鸦和麻雀,但那天早晨她心情十分愉快,于是决定做一个“绅士般的”稻草人。她用家中犄角旮旯残存的原料为他乔装打扮,感觉效果特别好,于是随手又给他戴上一顶她已故丈夫的假发,外加一顶插着一根羽毛的帽子。就这样,这个稻草人被命名为羽毛冠。
女巫以慈母般的眼光打量自己的杰作,越看越像真人。当她在自己的烟斗里装好烟草并点燃后,一个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何不让稻草人去见见世面?毕竟,“外面的世界,有许多跟稻草人一样脑袋空空如也的草包”——而他们通常都活得很好。
为了让稻草人成为真人,女巫让稻草人拼命吸烟——“抽烟,亲爱的。一直抽下去,你的生命就靠它”。稻草人拼命抽烟,于是渐渐具备人形:他的衣服开始变新,人也变得英俊迷人。随后,女巫又让他学习说话,经过一番努力后,稻草人竟说出“别怕,妈妈,我会像一名诚实的绅士一样混得很好”这样的蜜语甜言。一切准备就绪,女巫还给他配上一根闪闪发光的金顶手杖。稻草人告别女巫,走出屋子,雄赳赳地朝镇上走去。
一路上,几乎所有人都把稻草人当成“贵族”“美男子”,对他竭力奉承、赞美——除了镇上的一条狗和一个小男孩(像安徒生童话里的角色,后者一眼识破稻草人的“新装”)。稻草人前往女巫指明的目的地——镇上法官古金老爷家。原本盛气凌人的古金老爷,在稻草人说出一句女巫交代的暗语后,立马转变态度,变得笑容可掬,并吩咐自己的女儿宝莉走出闺房,好意款待稻草人。在与稻草人聊天的过程中,少女坠入情网,难以自持。直至她在穿衣镜中看到稻草人的真实模样,立刻被吓昏在地板上。与此同时,稻草人也从镜中看到了真实的自己——一个没有被施法术的稻草人。
稻草人羞愧难当。他一口气冲回女巫家里,悲凉地感慨:“我已经赢得宝莉的欢心,只要再吻上她的唇,我就会完全成为一个‘人’。可是我看到了自己,我空无一物,什么都不是,我不想再活下去了。”说完,他从口中拔出烟斗,掷向墙角,然后慢慢瘫倒在地——还原成墙角的一堆稻草、破衣、木棍,和一只南瓜。
从某种意义上说,《羽毛冠》中的稻草人可谓现实中美国人的隐喻。女巫用代表不同欧洲国家的边角材料和家中常见的农场物品制成了稻草人:他的身体是由扫帚柄、连枷、布丁棒、椅子的断臂、锄头柄、塞满稻草的饭袋和南瓜做成;他的衣服原料包括来自伦敦的梅子色大衣、天鹅绒马甲,和来自法国的猩红色马裤、丝袜、假发和三角帽——上述物品都极为破旧,分明一副贵族破落户的景象。“伦敦制造”的外套虽然有“刺绣遗迹”,但“遗憾的是它已经磨损并且褪色”,而猩红色的马裤即便“曾被法国路易斯堡的总督穿过”,但在交易给女巫之前却被赠送给一名“印度巫师”——属于廉价的二手货。镇上的人们看到“羽毛冠”华美的服饰,都在私下揣测“他是荷兰人、德国人、法国人,还是西班牙人”。可见,稻草人的构成暗示了它是欧洲遗产与美国土壤相结合的产物——二者共同创造出一个混合的“土著”身份。这名土著在女巫的命令和指引下(“在其他稻草人中抓住机会”),不无自豪地走向世界去创造属于他的财富和未来。
1781年,从法国移民美国的博物学家克雷夫科尔(Crèvecœur)在《什么是美国人?》一文中曾描述过这一混合身份:它对应着一个古老的神话,即“美国人”是“英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法国人、荷兰人、德国人和瑞典人”的大熔炉,这里“充满了无拘无束的工业精神,因为每个人都为自己工作”。根据克雷夫科尔的观察:“(美国)不像欧洲那样,由拥有一切的大领主们和一群一无所有的人组成。这里没有贵族家庭,没有宫廷,没有国王,没有主教,没有教会的统治,这里不存在少数人拥有隐形权力,不存在大型制造商雇用成千上万人,也不存在优雅精致的奢侈品。”因此,他的结论是,在美国广袤的土地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并不像在欧洲那样大”。
纳撒尼尔·霍桑
然而,在熟悉新英格兰和美国史的霍桑看来,克雷夫科尔的论断无异于一则笑话。尽管人人平等作为天赋人权被写入美国的法律条文,但事实上,从华盛顿国会到塞勒姆海关,霍桑触目所及,到处是尔虞我诈、恃强凌弱,哪里有平等可言?以寓言中的小镇为例,倘若稻草人没有女巫暗语的加持,镇上的法官古金老爷绝对不会高看他一眼——即便是从欧洲淘金归来的暴发户,也没有资格与当地的望族名流平起平坐。古金老爷如何发迹,作者并未交待,但既然女巫能以暗语相威胁,说明其中必定有“猫腻”,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同样,女巫相信稻草人完全具备“混社会”的资质,因为她不仅赐予他一张精致的南瓜脸,而且赋予他社会上追捧的贵族腔调和体面——于是命令稻草人去追求尊贵的古金老爷的宝贝女儿:“向前进!世界就在你的面前!”
在故事的结尾,女巫留下一段讽刺性独白:“天下有多少花花公子和江湖骗子,还不是跟你一样,都是些破破烂烂、无人惦记、一无用处的垃圾!可他们个个活得滋润,名声又好,从来就没认清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我可怜的稻草人偏就认清了自己,还为此送了自家的性命?”其实女巫明了,在这个遍布草包的世上,有尊严的稻草人并无容身之地:“我可以再给他一个机会,明天再送他出去。但算了!在这样一个空虚无情的世界里,他的感情太温柔易碎了。他太有良知,不愿意为自个儿而活。”
《羽毛冠》在霍桑短篇创作中占有独特地位。尽管故事背景设定为十七世纪女巫横行的新英格兰,但作者影射现实的“寓言”功能不言而喻。由于美国政坛臭名昭著的“政党分肥制”,在海关任职的霍桑被无端罢免,内心的愤慨可想而知——故事中面目可憎的古金老爷便是这类翻云覆雨的政坛大佬的化身。为养家糊口,霍桑被迫投身文学市场,但屡屡遭遇挫折:美国“庸众”像故事中的小镇居民,只注重外表华丽光鲜,根本无法辨别金玉其外的败类和真正的艺术天才,更不会像英国人崇奉莎士比亚一样崇奉这类天才。
这一切让霍桑感到无比悲哀。正如亨利·詹姆斯日后在《霍桑传》中所言,“欧陆的浪漫文学所凭依的源头活水,美国却一无所有:既没有悠久的历史,也没有民间传说。”因此,作家霍桑事实上“生活在一个简单、粗俗的社会之中”。用霍桑本人的话说,即美国是“一个没有阴影,没有古风,没有奥秘,没有刻画生动而又令人沮丧的不义之邦,只有光天化日之下,触目可见的一片繁荣气象”。这样的社会现实和“繁荣气象”显然不适合传统文学创作,于是作家只能转向寓言。
当然,霍桑的寓言并非全然原创:一方面,他受到本土作家影响,如他的康科德邻人、《小妇人》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她于1849年创作短篇故事集《花朵的寓言》),以及文学前辈华盛顿·欧文——在《睡谷传说》结尾,主人公伊卡博德醒来发现身旁“一只破碎的南瓜”,而伊卡博德本人也被描绘成“一个从玉米地里逃脱的稻草人”,而且无论走到哪里,他都随身携带一册清教神学家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所著的《新英格兰巫术史》。
另一方面,霍桑也受到欧陆浪漫主义文学尤其是德国浪漫派作家的启迪。爱伦·坡曾指控霍桑“剽窃”德国小说家蒂克(Ludwig Tieck)及法国作家大仲马,固然是空穴来风(霍桑在《海德格尔医生的实验》“序言”部分已力辨其诬),但霍桑若干小说(从立意到表现手法)与另一位德国浪漫派大师霍夫曼(E. T. A. Hoffmann)高度“雷同”,却是不争的事实。
以霍夫曼代表作之一《侏儒查赫斯》为例。此人原是人见人恶(心)的丑八怪(“后背弓得像个南瓜”),机缘巧合获赐女巫的法宝,在宫廷飞黄腾达,最后竟坐上了内阁大臣的交椅。借助这一侏儒形象,霍夫曼不仅揭露出当时社会的阴暗面,而且也描绘出德意志小公国里各阶层民众的生活状况:“那里是个庸人的圈子,四周的空气令人窒息。”——诚如批评家指出的那样,霍夫曼笔下的“寓言”并非凭空臆造,而是当时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这也是它引发霍桑强烈共鸣的主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和霍桑一样,同时代的马克思对《侏儒查赫斯》也情有独钟。流亡伦敦期间,马克思不仅时常对女儿们讲述这则寓言故事,而且曾推荐它为课外读物,或许正是因为其中富含天才的艺术想象和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借用笛卡尔《方法论》中的名言,即“世界是寓言”(Mundus est fabul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