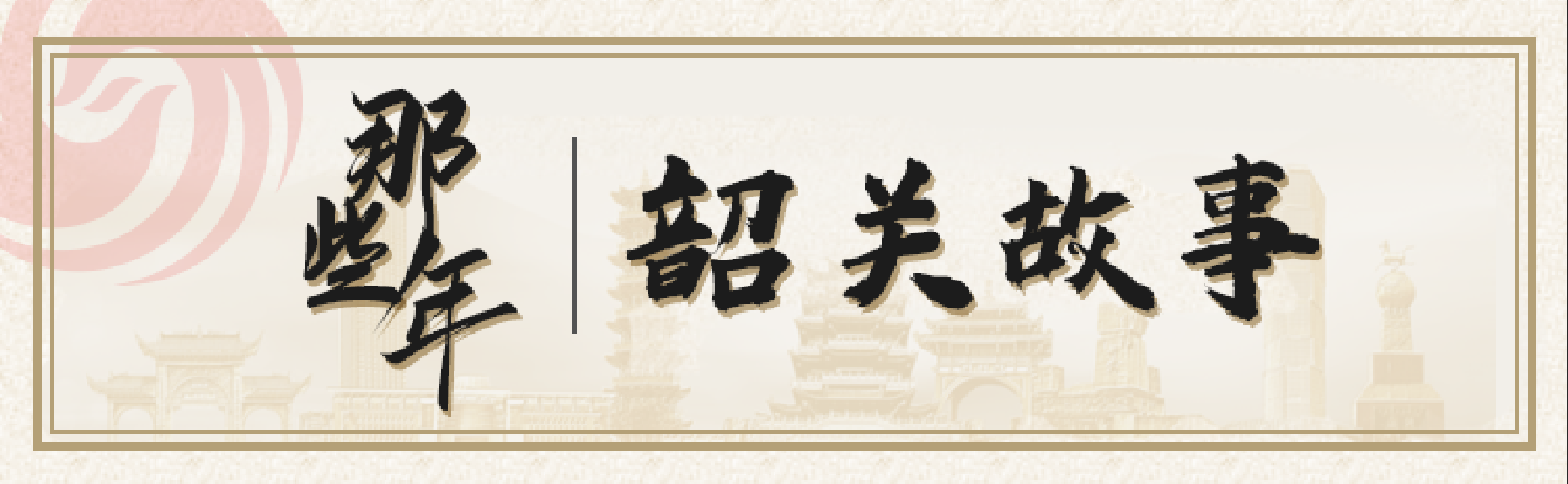
位于南岭南麓、武江上游的乐昌市坪石镇,是一个沿江水分布的狭长小镇,由于地处韶关市最北端,故有“广东北大门”之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粤北小镇偏安一隅,默默无闻,直到近年来,随着宜乐古道的发现,以及“三师”志愿者团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多位教授的寻访与深入调研,一大批抗战遗址在这里被发现,一段尘封多年的华南“学术抗战史”也终于从历史长河中被打捞起来。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广东紧急迁省会于粤北韶关,广东省教育厅随省政府迁至连县,以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为代表的许多粤港澳大、中学校先后迁至乐昌坪石和曲江大村(现为浈江大村)办学,直至抗战胜利。
这一烽火逆行的悲壮之举,保存了华南教育的根脉,在深沉的暗夜中,高擎起知识和科学的圣火。时至今日,其丰富的精神内核,依然照耀和影响着当代人,成为传承爱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助力人文湾区建设的活力源泉。
烽火逆行,保存教育火种
将时钟拨回战火纷飞的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日寇为从文化上摧毁中国抗战的意志和潜力,将诸多高校列为打击目标。彼时,偌大的中国,竟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随着平、津、沪、宁等地相继沦陷,中国高校大多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困境。为保存民族文脉,中国高校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迁徙,上演了抗日战争史上极为悲壮的一幕。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分三路在大亚湾登陆,广州告急,中山大学奉命紧急撤离。292名中山大学教职员工携图书、设备迁移至罗定。随后又辗转迁至广西龙州、云南澄江。随着战争形势的转变,1940年9月22日,时任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率领1700余名师生从澄江启程,经滇、黔、桂、湘、粤五省,纵横数千里,于1940年12月全部抵达位于粤北山区的小镇坪石,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岁月。
“迢迢远道,越悬崖,过山峡,经历了几千里的长征......”但“强健胜前”,“风雨不能侵蚀,憾击不能动摇”。透过中山大学亲历者的文字,我们能一窥迁移之路的艰难竭蹶与困难重重,更从中读出中山大学师生超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
中山大学的坎坷经历,只是华南高校在那个年代的一个缩影。同一时期,私立岭南大学、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东吴大学、仲恺农工学院,以及文理学院附中、培联中学、华英中学、华侨三中等30多所粤港澳大、中学校也纷纷内迁或建立于此。其中,大多数学校都经历了3迁乃至4迁,而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则先后迁徙 10 次,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曾说其是抗战中高校“迁校次数最多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大多数高校都选择整体迁往西南大后方,但华南这些学校在战局尚未明了的1940年,却选择逆行北上,彰显出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在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劲看来,此举向社会大众,更向日本侵略者展示出一种坚定的信念:中华民族不会屈服,抗战必胜。
国民教育是民族复兴的基本依托。华南诸校以烽火逆行的姿态,保存下华南教育的火种,让中华文脉得到延续,并培养起大量人才,仅中山大学在坪石的4年间,便培养学生近 2 万人,为抗战及新中国的发展输送了一大批栋梁之才。
历经磨难,不坠青云之志
坪石西北,武江之畔,沧桑的西京古道三星坪码头静静伫立着,尽管青苔已漫上石阶,周边荒草丛生,它依然坚挺地守在岸边。一如80多年前,守着奔波千里、满身疲惫的中山大学师生上岸。
这里正是中山大学师生在坪石开启烽火求学岁月的起点。由于抗战时期的特殊原因,中山大学各院校选址大多分散,有的甚至相距数十里:理学院设在坪石塘口村,法学院设在武阳司村后迁车田坝,师范学院设在管埠,文学院设在清洞村后迁铁岭,工学院设在三星坪村和对岸的新村,医学院设在乐昌县城,农学院设在湖南省宜章县栗源……三星坪和对岸的新村,还留有中山大学工学院的残垣断壁。坪石老街的广同会馆则是国立中山大学的研究院。
据记载,迁至坪石后,有家室的教师大多租住当地百姓的民宅。学校以寺庙祠堂当教室,土坯木板做桌椅,茅棚民居为校舍,石头木板架床铺。师生常常跋山涉水,往返穿梭于各村镇之间上课做实验,日常伙食也只有青菜、咸菜、辣椒,条件十分艰苦。
坪石中山大学 7 个校区的规划和 160 余栋校舍设计皆由该校建筑工程系教授虞炳烈独立完成。没有钢筋水泥混凝土,虞炳烈便让施工队因地制宜地利用当地出产的杉木、竹竿等建材,用杉树皮做屋顶,竹片钉起来做墙壁,以最低成本搭建起校舍。机械工程系还设有机械工场,专供各系学生实习之用。
吃住简陋、图书缺乏、实验仪器匮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也从未停止科学研究和创作的步伐,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提出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学术理论,出版发表了大量科研论著。
其中,邹仪新在1942 年发表了《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第二次日食观察报告》,详细报告了日食的相关情况;卢鹤绂发表了《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应用》,全面阐述了核裂变的实验发现及有关理论,并预言人类将有大规模利用原子能的可能性;王亚南1942 年开始撰写“高等经济学”讲稿,1946 年以《中国经济原论》为名出版,这是“中国最早一部尝试把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成功之作”......
文艺创作领域也百花齐放,黄友棣创作的《杜鹃花》谱曲,是抗战歌曲中的经典;马思聪 1944 年创作了《F 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部大型小提琴曲......
但凡有一方屋瓦栖身,便有朗朗书声响起。无论是逆境中坚持求学、追求真理的学生,还是治学严谨、德才兼备的老师,都是那个时代的华光,他们不仅留下了累累学术硕果,还将求知向学之风和开放、包容的教育理念传播开来,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武水流长,国士风骨永存
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西南联大遗址后曾说: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纵观华南教育史,不仅是一段烽火育才、读书报国的历史,也是一段以身许国、抗战救亡的历史。
聚集了众多华南高校的粤北地区,成为当时的教育圣地,开放的风气和良好的氛围,让无数新思想在这里激荡,点燃革命的星星之火。在保持和延续中国高等教育的同时,许多高校师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或积极响应当局号召参军,或踊跃服务于国家军需征调,或积极奔赴前方作战。如岭南大学的毛锦霞同学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中山大学的 200 多名师生加入东江纵队,参加抗日战争。
1945年1月21日,坪石被日军攻陷。中山大学建筑工程系卫梓松教授,因病未来得及随众撤退,落入敌手,日军欲利用他的声望,威逼利诱他出任坪石镇维持会会长,卫梓松以死明志,于 1945 年 3 月 3 日服下过量安眠药自尽,壮烈殉国.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被迫迁移的华南各学校终于得以重返故地,重建校园。4年后,新中国成立,不少身在国外,但曾在粤北执教或学习过的人,都因为对民族和国家的热爱,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或终身从事教育、培养人才,或在不同领域从事科学研究,为新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本立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他年轻时就读岭南大学,品学兼优。1950年,在爱国热忱的感召下,他便毅然放弃了出国机会,和同学一起北上长春东北科学研究所,投身光谱分析研究。
正是因为有一批批这样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投身新中国火热的建设之中,才能不断创造发展奇迹,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不断照进现实。
红色为底 谱写发展新篇
从中山大学天文台旧址,到新村不留亭,再到塘口村理学院物理系上课的古庙课堂......一处处旧址讲述坚如磐石的信仰信念,一件件文物彰显历久弥新的初心使命。
作为华南学术抗战史的见证,自2019年起,坪石镇多处遗址被重新保护修缮,连缀成“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这里正成为广大师生和众多游客缅怀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热点场所,为韶关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见证了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的峥嵘往昔,承载着粤港澳大湾区共同记忆和文化情感,已然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教育事业的“寻根之地”。在加强祖国统一、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湾区建设过程中,这段尘封已久的宝贵历史还将成为推动大湾区深化教育合作的历史机缘与全新契机。
昔人已逝,精神长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再次梳理、回顾这段华南教育历史,既是对革命先辈的缅怀,也是对坚守教育、笃志报国等精神的一种传承。激活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期待这些革命文物遗址不断绽放新光彩、为韶关发展谱写新的华彩乐章。
出品:凤凰网广东新闻中心
校编:陈婉霖
审核:韩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