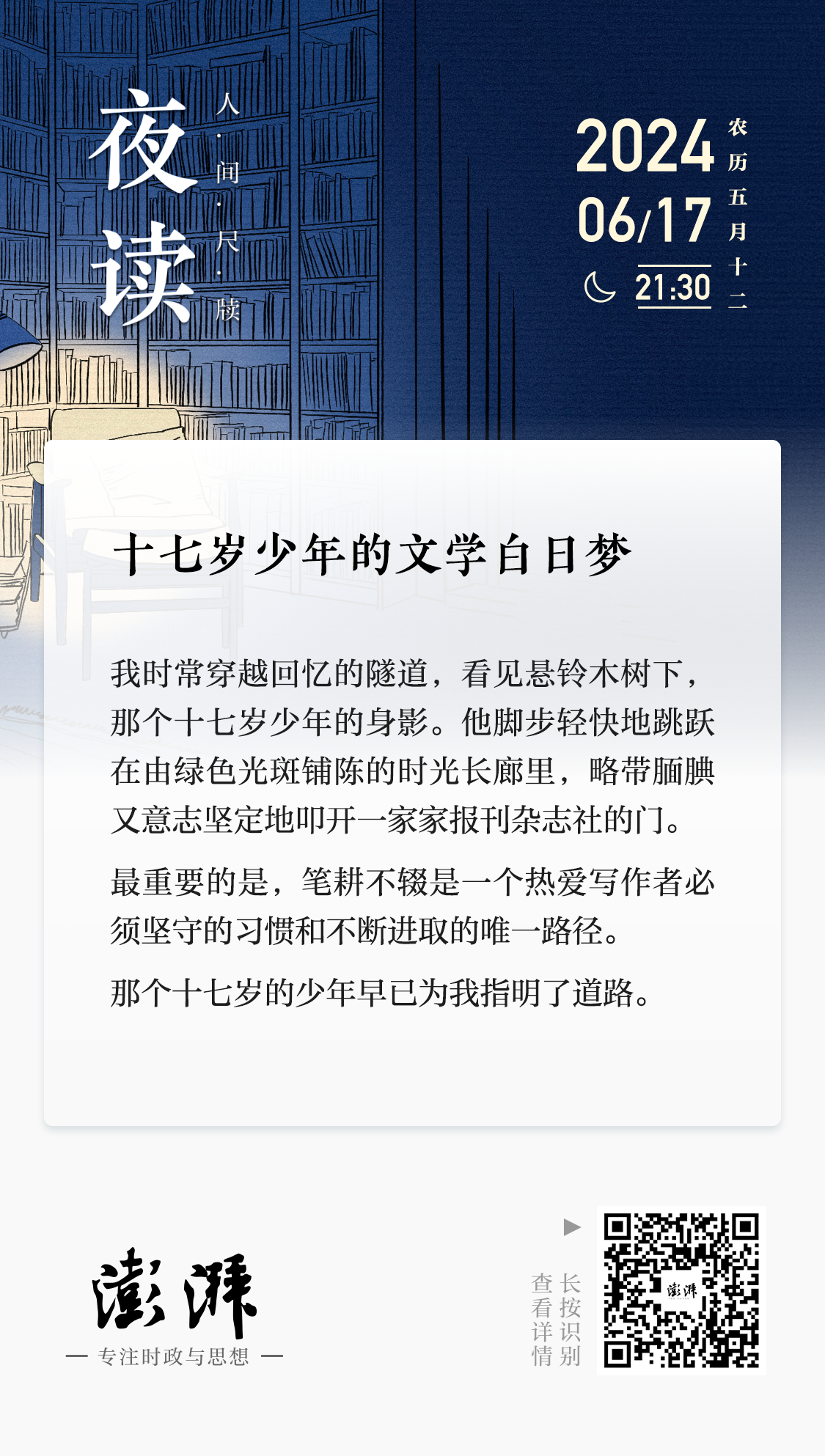上海的市中心有很多法国梧桐树。一到夏天,那些宽大的树冠就像张开的伞盖,遮挡了炙热而耀眼的阳光,微风透过树叶的缝隙,为城市送来一丝清凉。
我时常穿越回忆的隧道,看见稠密的悬铃木树下,那个十七岁少年的身影。他脚步轻快地跳跃在由绿色光斑铺陈的时光长廊里,手心攥着一本硬面抄,略带腼腆又意志坚定地叩开一家又一家报刊杂志社的门。
那是我在二十多年前做的文学白日梦。十七岁那年,我在《上海中学生报》上发表了处女作。几乎是同时,《中文自修》的编辑也向我约了一篇稿子。几年之后,我做大学社会实践,去《当代学生》编辑部实习,巧遇了当年编辑我稿子的两位伯乐,不禁感慨万千——她们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与帮助。用有些俗套的话说,“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我在文字上最初的那一点自信大抵是她们发掘的。
十八岁时,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地走进巨鹿路675号上海市作家协会,将一叠厚厚的稿纸毛遂自荐地递到《萌芽》编辑部。接待我的编辑老师说《萌芽》的投稿量巨大,一般是不回信作者的,来稿三月若无回复便可改作它投,但见我如此虔诚,不论这叠稿子里是否有文章留用,都会给我回一封信。那天我穿着白衬衫、牛仔裤,头发蓬松,戴金丝边框眼镜,倒真像个文学青年的模样。退稿和回信比我预想的来得快。编辑老师夸赞了我对文学创作的热情,当然重点在“但是”之后——我的作品离在《萌芽》上发表还有一段距离,须再接再厉。
我一头扎进图书馆,除了继续写小说、散文,也更有意识地研究目标杂志各栏目的文字风格和要求。我坚持平均一年给《萌芽》投两次稿,一次至少五篇文章。然后,它们像风筝断了线,像石子沉入大海,杳无音信。
但我并不在乎。“作品完成之后,它就与作者无关了。”我记得余华说过类似的话。他年轻的时候,一边做牙医,一边写小说,也不认识任何杂志编辑,只知道杂志的地址,就将稿件寄过去。遭遇退稿,就将信封翻过来,用胶水粘上另一个杂志的地址,将信再扔进邮筒。他说那个时期自己的手稿在各个城市间旅游,走过的城市比他后来去过的还多。直到《北京文学》的编辑打给他一个改变命运的电话,让他去北京改稿。
我也在期待贵人的出现,抑或说等待一个电话或来信。我没有广撒网,而是锲而不舍地把稿子往巨鹿路675号寄,终于在一年后再次收到了退稿。这次退稿并不完全,还附上了编辑老师的信笺,她说这叠来稿中有一篇文章情感表达真挚,形式也新颖,拟留用并于来年刊发。这成了我二十岁最好的生日礼物。在大学毕业前,我的投稿和编辑老师的来电日益频繁,几篇拙作得以陆续发表。
后来网络文学平台出现,每个人都可以自己经营博客、公众号,收获许多粉丝。我也因为工作关系,文学创作与投稿的频次肉眼可见地减少了,可自忖始终是有些文学追求的。十年前,我写完一部书稿,在微博上找心仪的出版社电子信箱,试着将样稿投递出去,最终促成了出版。
马尔克斯曾说,写作恐怕是这世上唯一越做越难做的行当。《百年孤独》的构思,他就足足花了十九年,“想好了,再坐下来写……一遍遍想,一遍遍琢磨。”当然,比写稿更痛苦的是投稿、退稿、再投稿——《百年孤独》这样的巨著也未能幸免。1950年代初,马尔克斯的处女作《枯枝败叶》被出版社退稿,写退稿信的是一位有名作家,他直接奉劝马尔克斯放弃小说。后来,《枯枝败叶》在好几个出版社之间流转,都没被采用。直到1955年,马尔克斯把它投到一家陌生的出版社,终于成功了。但最后,书出版了,出版商却蒸发了,马尔克斯没拿到稿酬,还倒贴了全部出版费用。
在我的投稿生涯中,虽然也饱尝挫折和失败,但幸运的是,遇到的多是乐于关爱后生的前辈们。文章发表、有所成就鼓舞人心,读者的青睐也是激励我不断前进的动力。最重要的是,笔耕不辍是一个热爱写作者必须坚守的习惯和不断进取的唯一路径。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记忆中那个十七岁的少年早已为我指明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