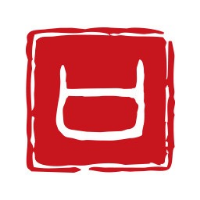大概在昨天,我还在心底非常羡慕人类中的那25%的“超级味觉者(supertasters)”,嫉妒程度,就和学渣仰望考上985的学霸不相上下,生而拥有更多的味蕾,简直让我这个资质平庸又爱吃的人太想拥有了。
而且“超级味觉者”这个称号,光是听起来就很厉害很专业啊,犹如吃喝界的超级英雄一般,天生带感!
但不幸的是,想成为“超级味觉者”,并没有一场相对公平的高考可言,而是完全依靠遗传和基因来决定的。
拥有超级味觉的人其实在我们身边并不少,25%的概率,平均五个人中就有一个嘛。陪着我们长大的蜡笔小新算一个,小新的味觉很有可能对于辣椒素和植物里的苦味格外敏感,只要知道今天晚上吃青椒,再没心没肺的野原新之助也开心不起来了。

那怎么测定自己是不是一个“超级味觉者”呢?
“超级味觉者”这个称呼是生理心理学家琳达·巴托舒克(Linda Bartoshuk)提出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味觉超级敏感的人。
最初的“超级味觉者”选拔标准,是按照我们舌头上味蕾的数量多少来测定的,你可以把蓝色的食用色素涂在舌头上,然后在一张白纸卡片上剪出一个 4mm直径的圆洞,把卡片放在舌头上数一下粉红色的凸起味蕾,如果在4mm×4mm的舌头上有超过30 个味蕾,你大概就是超级味觉者之一。
舌乳头和味蕾
另外,辣椒素,也是一个用于测试超级味觉者的好道具。味蕾与疼痛纤维是相连的,所以味蕾越多,痛觉感受器也越多。所以,味蕾细胞多的人很容易对辣椒素产生强烈疼痛反应。
除了味蕾的数量,成为“超级味觉者”的决定性因素还主要取决于TAS2R38基因的形态。
“味觉是负责将味道信息传递给我们的感觉,是由专门的器官产生的。”
布里亚-萨瓦兰《厨房里的哲学家》
说到TAS2R38基因的形态,我们就要从味蕾的工作方式说起,每一个味蕾是由50~150个味觉受体组成的,其中一个叫TAS2R的基因家族负责结合味觉受体和食物里的分子,再把味觉信号传递给大脑。
为我们传达苦味的受体基因是TAS2Rs,它们可以识别出几千种苦味物质。
而“超级味觉者”味蕾中的TAS2R基因发生了遗传变异,这个基因上的DNA序列的变化,导致味蕾产生的蛋白质不一样,所以“超级味觉者”会对蔬菜里的硫脲类化合物非常敏感,认为这种味道非常苦不堪言,甚至会感觉西蓝花苦的让人呕吐。
所以,你也可以用琳达·巴托舒克发明的丙基硫尿嘧啶(propylthiouracil)来确定自己是不是一个“超级味觉者”,丙基硫尿嘧啶是一种治疗甲状腺的药物,需要处方才能获得,大部分人只觉得它是没什么味道的纸味儿,如果你的觉得这种药特别苦,那恭喜你,你成功晋级为一名超级味觉者。
味蕾的密度和基因的元素,让天生爱吃的我无缘“超级味觉者”,只能面对味道的宿命论无可奈何,除了超级味觉者,世界上还有一半的人类属于“正常味觉者(normal tasters)”和25%的“味觉迟钝者(non-tasters)”。
在如今万物皆要政治正确的环境下,“超级味觉者”和“味觉迟钝者”也被改为高味觉者(hypertasters)和低味觉者(hypotasters),我倒觉得,超级和迟钝被替换为高和低让人觉得毫无诚意,不如改成“味觉亢奋者”和“味觉无感者”更安全些。
乔治·H.W.布什也是一个有名的“超级味觉者”,他的名言“我不喜欢西蓝花。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就不喜欢西蓝花,可妈妈总让我吃西蓝花,现在我是美国总统了,我再也不会吃西蓝花了。”就很好的表明了“超级味觉者”们的立场:我们不爱吃苦的、辣的、酸的,一切在自然界中看起来不那么安全的食物。
还好老布什的妻子芭芭拉很愿意帮他吃掉那部分西兰花
没错,“超级味觉者”其实是在进化过程中更有生存优势的,他们对含苦味(也就是毒性)的植物更为警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相对于男性,女性更容易成为超级品尝者,这也是由于女性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更多肩负了哺育后代的工作,而敏感的味蕾可以让她们对于有毒物质更为警觉,从而保护婴儿的安全。
2005年伦敦大学学院、杜克大学医学中心和德国人类营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共同发表的研究论文得出结论:人类进化出品尝苦味的能力,是为了检测植物中的毒素并避免食用它们。
所以说“超级味觉者”其实是人类对于危险大自然的一种防御机制,我们咀嚼和品尝,不仅是为了尝到美味,也是为了避免吃掉有毒的食物,所以我们在幼儿时期对于苦味最为敏感,保留了人类原始的警惕性。
但是一旦在长大后,发现了安全后,我们就会调节自我,从而在苦味的食物中也获得乐趣。当然,从悲哀的角度分析,也有可能是人类随着变老,味蕾的数量随之减少,远远不如婴儿时期那么敏感了,也愿意吃掉更多苦味食物。
长辈们往往愿意给小辈以健康的名义安利苦味蔬菜
大部分脊椎动物都拥有苦味受体的基因,越是杂食动物对苦味越为敏感,而纯肉食动物的苦味基因就比较少,因为不爱吃植物的它们很少能够遇到有毒物质。
我没有甜味受体,嘿嘿
不得不说植物真的很聪明,攻击力和躲避能力很低的它们,就必然要从味道的角度来对动物进行反操控,用苦味和毒素让动物远离自己。幸亏这些植物没有碰到蓝鲸,因为只需张开大嘴吞食浮游生物的蓝鲸根本不需要咀嚼和品尝,这些完全没有苦味受体的庞然大物完全不会受到味道的困扰(心太大了,中了毒也不知道)。
吃苦,对于蓝鲸来说,是不存在的
能吃苦的动物,也一定是被逼到绝路上了,日本猕猴对于柳树树皮里苦涩的水杨苷不敏感,这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毕竟树皮,是他们冬天唯一的食物。更有趣的是,柳树皮中还有一种化学物质,可以稀释血液、解热止痛,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阿司匹林的主要成分。
对,我还蛮能吃苦的
另外,“超级味觉者”还有一个隐形优势:他们很少会患上鼻窦感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耳鼻喉科专家诺姆·科恩发现,患有慢性鼻窦感染的病人几乎没有“超级味觉者”,因为超级味觉者的鼻子会对苦味的细菌性物质产生非常激烈的反应,从而阻止了鼻窦感染。
说了这么多“超级味觉者”的优势,我突然释然了。
我还是享受作为一个普通“正常味觉者”的乐趣,我喜欢吃蒜蓉西蓝花那种微苦的清爽感、潮汕人对苦瓜那种出神入化的应用、葡萄柚里迷人的苦味、咖啡和茶里苦的让人上瘾的感觉、辣椒素给口腔带来的轻微灼烧爽感和香气、还有IPA里的苦度,那种来自于啤酒花中的异α-酸或葎草酮的苦味更是让人神清气爽,更不用说越来越被宣传为健康食物的一众十字花科苦味食物了。
我想,“超级味觉者”们也必然无法享受重庆火锅咕嘟出来的欢乐,对他们来说难以忍受的灼烧感,而可以刺激我体内内啡肽的释放,俗话里的“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儿”就是源于内啡肽产生的愉悦和轻松。
做一个平平无奇的“正常味觉者”挺快乐的,毕竟,只要不是味盲就好。
参考资料:
《很高兴认识“我”》比尔·沙利文
《心理学与生活》菲利普·津巴多
《厨房里的哲学家》让·安泰尔姆·布里亚-萨瓦兰
《大美生命传奇》《环球科学》杂志社
《病者生存》沙龙·莫勒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