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白蛇传故事,目前有较充分的证据显示,可能是世界性蛇女故事的一个中国化版本。民间文学家丁乃通在其文章《高僧与蛇女——东西方“白蛇传”型故事比较研究》中对此做过详细的考证。丁乃通深入考察了白蛇传故事与欧亚拉弥亚(Lamia)故事的相似性,有理有据地反驳了“各自独立起源说”,以严谨扎实的分析得出了东西方两种故事“同出一源”的观点。丁乃通认为,它们来自同一个原型故事,这一原型故事大约产生于公元元年前几个世纪的印度北部或中亚地区,后来这一原型故事经宗教信徒之手,被改编成一个说教故事,这一宗教说教故事随后向西方和东方传播,成了后世欧洲的拉弥亚故事和中国的白蛇传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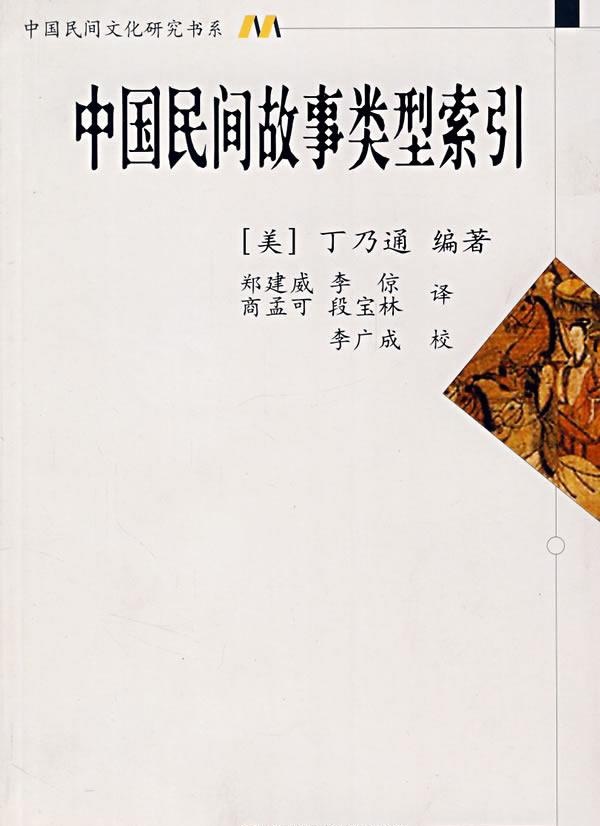
白蛇传故事如果最初真的来自域外,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将会饶有趣味——这一故事是何时传入中国的?如何一步步中国化的?其中国化历程经历了哪些阶段,形成了哪些中国特色?对这一系列问题,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全面回答。现仅针对蛇女故事可能的中国化所形成的一个本土特色进行探究,即白娘子为什么是“白”的。
对比欧亚诸多的拉弥亚故事,白蛇传故事的中国特色中最显著的莫过于白娘子之“白”。
白娘子之所以是“白”娘子,我们都知道,因为她是白蛇所变。但白娘子为什么是白蛇所变呢?在欧亚众多的蛇女故事中,仅有济慈的长诗Lamia中说是一条五彩斑斓的蛇(vermilion-spotted, golden, green, and blue),但到了中国后,为什么原本并不强调身躯颜色的蛇女变成了白蛇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梳理出白蛇传故事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化史,即白娘子是何时成为“白”娘子的。经过许多学者研究,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完整地描绘出白蛇传故事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化史了。
今天能发现的最早的蛇女故事,都集中在唐宋时期,大都收录在《夷坚志》和《太平广记》中。许多学者认为唐末《博异志》中的文言小说《李黄》是最早的蛇女故事。与《李黄》类似的蛇女故事,在南宋《夷坚志》中还有《历阳丽人》《孙知县妻》《杨戬二怪》《钱炎书生》《衡州司户妻》《济南王生》《姜五郎二女子》《净居岩蛟》《同州白蛇》,以及北宋《太平广记》中收录的《老蛟》《王真妻》。在这十二个蛇女故事中,蛇女原形为白蛇的有四个,即《李黄》《孙知县妻》《杨戬二怪》《同州白蛇》。如果再加上宋元话本《西湖三塔记》,今天能发现的白蛇传故事之前的蛇女故事中,“白蛇女”故事至少有上述五个。
也就是说,算上《西湖三塔记》,在我们已知的十三个蛇女故事中,点明蛇身颜色的“白蛇女”故事有五个。这占了相当不小的比例,很大程度上已经说明了蛇女故事在早期就已开始了本土化变异,尤其是第一个蛇女故事《李黄》也正是“白蛇女”故事。那么蛇女为什么会变白呢?白色对蛇女妖的身份建构和故事内涵有何新的发明?
不少学者认为白蛇或白娘子之“白”,意味着纯洁忠贞、善良、吉祥神圣等,寄托了普通百姓的心声。的确,自清代中叶以来流传的白蛇传故事,其中的白娘子形象给人的印象是相当正面的。但纵观蛇女故事的整个演化史,在白蛇传故事的第一个定本——冯梦龙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之前,上述我们所列举的那五个“白蛇女”故事中,没有一个“白蛇女”可以称得上忠贞纯洁,或者性格良善。事实上,在已知十三个蛇女故事中,大部分蛇女都存在着一种共性,即“好淫”——主动寻求与人间男子交合。这虽然或许不乏良善动机,但与传统上的纯洁忠贞、吉祥神圣等风马牛不相及。
有鉴于此,在回答白娘子为什么是“白”娘子这一问题时,谢兴尧以“白蛇好淫”为由给出了答案。而丁乃通则认为“白蛇在民间文学中被认为法力最大,而且根据中国民间迷信,这种畸形怪物会有异乎寻常的神力”。白蛇(可能在蛇类中)法力最大或神力非凡,故较易幻化为人,从而易与人类男子产生情爱纠葛。但丁乃通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白蛇被认为法力最大或有异乎寻常的神力。
笔者认为,白蛇之“白”或白蛇被认为法力最大,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佛教文学中的龙蛇叙事。梳理佛教经典《大藏经》所涉及的龙蛇故事,我们会发现其中提到龙蛇颜色的,白龙或白蛇的数量明显较多。佛教徒熟知的佛陀“钵伏毒龙”故事,在西域石窟的佛教壁画中被绘成了“钵伏白蛇”图像。在深受佛教影响的《太平广记》中,提及龙蛇颜色的故事占比最高的就是白龙或白蛇故事。据研究,《太平广记》的龙故事中言明龙身颜色的有36篇,涉及青白赤黑黄五种颜色,但白龙故事有12篇,占比最高,在四卷蛇故事中,白蛇出现的次数也最多,达10次。另外,在宋代笔记小说的蛇故事中,白蛇出现的次数相比于其他颜色的蛇也最多。
丁乃通提示的民间文学一线,其背后的信仰逻辑,或可追溯到中国早期信仰中的白色动物崇拜和“物老成精”“物老变白”的信仰。
周秦以降的不少古代典籍中,记载了大量白色动物出现的祥瑞征兆。据统计,周秦以来的古籍如《尚书》《楚辞》《史记》《汉书》等,记载的白色祥瑞动物至少涉及三类,飞禽类如白鸠、白雀、白乌、白鹘、白燕、白鹤、白雁,走兽类如白兔、白狐、白狼、白麟、白麞、白鹿,水生两栖类如白鱼、白龙、白虬、白龟、白螭。这些动物的出现都被书写者视为祥瑞之兆,反映出了视白色动物为精灵的崇拜观念。既然白色动物多被视为精灵,其相比于非白色的同类自然应更具灵性,体现在后世的志怪小说中,或许就逐渐变成了“法力最大”或“有异乎寻常的神力”。
关于“物老成精”“物老变白”的思想,东汉王充的《论衡》中有言:“夫物之老者,其精为人;亦有未老,性能变化,象人之形。”王充的此一论说源于秦汉以来的民间信仰。魏晋时代,玄学及鬼怪之学盛行,葛洪继承了王充之说。葛洪《抱朴子》有言:“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抱朴子》中还有大量“物老变白”信仰的描述,如“千岁之鹤……色纯白而脑尽成丹”“虎及鹿兔,皆寿千岁,寿满五百岁者,其毛色白……鼠寿三百岁,满百岁皆色白”“千岁蝙蝠,色白如雪……又千岁燕,其窠户北向,其色多白而尾掘”。这种“物老变白”的描述,也正符合先秦以降传说中的仙境动物多为白色的想象,如《列子·汤问》记载,“渤海之东……其中有五山焉……其上禽兽皆纯缟”,《史记·封禅书》中描述蓬莱仙山,言“其物禽兽尽白”,《汉武帝内传》中言西王母的车驾多用白色动物如白虎、白麟、白鹤等驱乘。
“物老变白”以及仙境动物多为白色的想象,加上“物老成精”的信仰,或许为白蛇精怪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为“白蛇女”故事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干宝《搜神记》中记载:“千岁之雉,入海为蜃;百年之雀,入海为蛤;千岁龟鼋,能与人语;千岁之狐,起为美女;千岁之蛇,断而复续;百年之鼠,而能相卜。”这里虽然没有言明蛇能变美女,但“物老成精”思维下的“狐变美女”逻辑在后世的志怪小说里显然被继承。既然狐狸能变成美女,蛇又为何不可呢?于是“蛇女”的出现似乎在情理之中。虽然目前有较充分的证据显示蛇女故事可能是外来的,但外来型故事要想在本土生根发芽,也需要适合的“土壤”和环境,“物老成精”“物老变白”以及仙境动物多为白色的信仰或许正是其“土壤”和环境。
总之,蛇女故事如果是在唐宋时期(或之前)自域外而来,那么原先并无特异颜色的蛇女,其转变成“白蛇女”、进而演变成著名的白娘子的原因,很可能正是上述复杂信仰语境综合作用的结果。白娘子或白蛇之“白”,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特色,是世界范围内蛇女故事的中国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