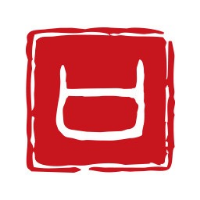客居北京两年多,我在家做炒饭的次数寥寥,一来是深知自己的低碳水饮食计划在油亮喷香的炒饭面前不堪一击,二来是总觉得炒饭只有暮色围拢的流动热炒摊上出品的才有筋骨,扭动的火舌,翻飞的米饭,黄黄稠稠的路灯下,老板手里的鸡蛋义无反顾地朝着滚烫的锅沿撞了过去,有点悲壮,场面混乱,但这是炒饭的精髓。
这种热炒摊在北京随处可见,大多昼伏夜出,有的驻守在人流如潮的地铁口,有的等候在令人惴惴不安的僻静小路上。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地铁口的热炒摊老板总是很善于招徕客人,每逢晚归人从地铁里鱼贯而出,一声声响亮的“炒饭炒面炒粉干”就迎面往人耳朵里钻。相比之下,躲进黑暗小巷子的热炒摊老板要寡言少语得多,要么木讷地守在锅前,要么坐在板凳上闷头玩手机,很少主动揽客,若是有人上前,他们也能手脚麻利的做出一份扎实生动的炒面或者炒饭。
我家楼下的老李就属于后者。
刚搬进小区没多久,我就买过老李的炒饭。一到晚上,他的热炒摊和卖炸串、卖煎饼、卖麻辣烫的三轮车们便聚集成一个微型流动夜市,把小区背面的停车场点亮。许是停车场太空旷,即便小贩们倾巢出动也显得寥落,大家在这片空地上各据一方,没有生意的时候总是各自沉默。老李的热炒摊很显眼,在停产场的中间,照明灯比别人的都要亮,他站在灯后,一张微微浮肿的脸被照的煞白,远远看过去有点骇人。
去年十月,秋老虎和冷空气还在北京城里拉锯,白天前者占了上风,一到傍晚,瑟瑟的冷风就变得跋扈。街上行人穿薄衫穿毛衫的都有,老李松垮垮的白色短袖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我走到老李热炒摊跟前的时候,他正专注于对付锅里的炒面,握着锅把儿的左臂结实有劲,手腕一紧,铁锅前后抽动,大半锅面条就连翻几个跟头。
老李并不热衷与人攀谈,往往客人在他这里下了单,就跑到别的流动车去吃点炸串和麻辣烫,所以老李的热炒摊看起来总是无人问津,却又总是火苗纷飞热气腾腾。
我得知老李是皖北人,是跟他买过七八次炒饭之后了。那会儿因为通州的大火,东五环外的合租房经受了严格的盘查和强拆,一时间人心惶惶,无数白天光鲜亮丽的上班族被打回了北漂的原型,我也没能幸免。北京的十一月凉风彻骨,加上找房子的燃眉之急,那天我去买炒饭的时候忍不住跟朋友抱怨,兴许是言语中藏不住的乡音,老李主动问我“你是安徽哪儿的人?”。
那天晚上,有关老李的事儿像是没封严实的木桶里徐徐缓缓渗出的水,汇聚成流,撒落在北京深秋冷硬的路面上。
老李是三年前来的北京,带爱人来看病,孩子留在家里由老人照看。老李和爱人刚到北京就住在了靠近通州的地方,地偏人少,房租便宜,合租房里一个不足10平米的隔断,那会儿不到1000块每个月。老李说到房租,连叹了好几口气,懊悔当时着急安顿下来,也没多去几家中介看看,说不定有更便宜的。我和朋友有些讶异,不知道怎么宽慰他,一时间大家相顾无言。老李又抿起了嘴唇,一言不发地用锅铲搅散刚刚打进锅里的鸡蛋。
老李的炒饭,不讲究先炒蛋还是先炒饭,每次油热爆香葱蒜末之后就放入米饭,米饭事先处理成松散的状态,放在一个大号的透明塑料袋里,面条米线河粉也是同样安置。热炒摊上的火极旺,米饭入锅翻炒几下,很快就热气哄哄。此时老李会用锅铲把米饭推到一边,留出一块空地给鸡蛋。
老李磕鸡蛋的手法干脆利落,但又似乎有些大力,鸡蛋总是在锅边撞个头破血流,破碎的蛋壳挂在凹凸不平的锅壁,被窜起的火舌舔的噼啪响。
热炒摊上的炒饭多是千篇一律的琥珀色,加了酱油,鸡蛋的嫩黄和米饭的雪白都被掩盖,一份炒饭挤在四四方方的塑料盒里,混混沌沌。老李不喜欢在炒饭里加酱油,除非有客人特意嘱咐,否则他递过来的炒饭永远都是油润清亮的,鸡蛋和米饭各自分离,但又因泛着浓淡不同的黄色融为一体。老李说他喜欢“看起来明明白白的炒饭”,又说“为什么她的病就是看不明白”。
老李的爱人得的是精神方面的疾病,在老家医治了两年,不见起色才来的北京。老李提到爱人,说得最多的词就是“性格好”。我大约知道他说的“性格好”是什么意思,小城市没有大城市一日千里的生活节奏,久居在一个地方,人们的生活圈子多多少少会有重叠的部分,哪怕是一星半点的关联,人和人相处起来都熟络得很快。
老李和爱人在老家开了一家烧烤店,女主人热衷与人闲聊,直率的性子招徕了不少回头客,男主人不善言辞,就包揽了店里需要出体力的杂活儿。女主人跟朋友闲聊的时候喜欢咪点小酒,不挑牌子,白的啤的都行,碰到言语投机的人,也会喝的脸红脖子粗,客人结账的时候,她又脑筋清明,把账算得明明白白。
老家的烧烤店规模不大,被老李夫妻经营得有声有色,直到老李察觉爱人的举止有异,有条不紊的生活节奏才被打破。
一天夜里烧烤店打烊后,老李的爱人提议想遛弯走回家,老李旋即答应,转身把电动车锁在烧烤店里。回家的路上,老李的爱人表现出少有的沉默,嘴里不时跑出七弯八拐的曲调,老李没有多想,回家之后洗漱如常,倒头睡到天亮。
接连几日,老李的爱人都寡言少语,嘴里的小调儿虽然听不着了,但是开始在路边捡垃圾往家带,有时候是饮料瓶,有时候是粗细不一的树枝。老李说他爱人捡垃圾的时候像着了疯魔,怎么拉都拉不住,骂也没用,只顾死死盯着地上的垃圾,对老李的愤怒置若罔闻,老李一松手,她就扑过去把垃圾捡起来用衣服兜在怀里。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老李连拉带拽地把爱人带到医院。医生的诊断还没出来,街坊邻居间就传出一些故弄玄虚的说法,最后传到老李耳朵里的是,他爱人碰到“脏东西”了。老李不信这些歪门邪道,心里气不过,嘴上却也顾不上辩驳,眼下最重要的事就是谨遵医嘱,让爱人接受治疗。
医生给出的答复是“喝酒喝坏了脑子”,需要住院观察。老李觉得这个说法不着边际,跟医生争执了起来,第二天他辗转到另一家医院,同样的检查在爱人的身上又做了一遍,得到的答复和之前一模一样。
老李的爱人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多。白天他守在医院,傍晚还要回到烧烤店。生活的温情好像一去不返,烧烤的生意也每况愈下。
爱人住院的这段时间,不止一次有熟人来劝老李试试“偏方”,来的人说得神乎其神,不惜举出身边亲友的事例证明自己没有胡言乱语。老李看着躺在病床上只会咿咿呀呀的爱人,决心一试。
这种拜鬼求神的“救命偏方”,我小时候听家里的老人说过,至于具体如何操作,谁来操作,我一概不知。老李对寻求“偏方”的过程也是含糊其辞,只告诉我“去了,去了两次”“没用,大师也治不好”。回忆的沉渣一股脑涌上来,犹如炒饭时锅里腾起的热气,蒙住了老李眼里的光。
后来,老李问亲戚借了一笔钱,抱着孤注一掷的心态来到北京。老李刚到这儿就找了份工作,物流仓库的搬运工。工作劳形,生活苦心,好在公司给员工缴纳五险一金,能帮老李分担压力。
热炒摊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做的,有过开烧烤店的经验,炒面炒饭对于老李来说得心应手。这几年,老李的热炒摊也曾出现在人流如潮的地铁口和天桥下,由于频繁遭到红袖标的驱赶,他索性在离家不远的小区找了块儿僻静地,虽然黑暗大于光亮,但大部分时间都不用提心吊胆了。
后来,我在附近找到了房子,嘴馋想破碳水戒的时候还是会跑到老李那儿买炒饭,老李的热炒摊前依旧一副无人问津的样子,唯一不同的是,十二月的北京空气冰冷得像铁皮,老李穿了一件厚厚的棉衣站在明晃晃的照明灯后面,臃肿得有些滑稽。等炒饭的时候,我问起老李爱人的情况,他总是先叹一口气,再说“挺好的”,也不知道是在宽慰我还是宽慰自己。
今年过完年回来,我再也没见过老李的热炒摊,但是一到傍晚,停车场上仍会聚集卖各种小吃的三轮车。有天晚上,我疯狂想吃炒饭,跑到地铁口的热炒摊买了一份。拎回家一看,米饭和鸡蛋在盒子里挤挤挨挨,是比琥珀更加颓废的颜色,用老李的话说就是“看起来不够明白”,一如这座城市里的大多数人,囫囵消化生活的混沌,终了不知何去何从。
文:头头
设计:小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