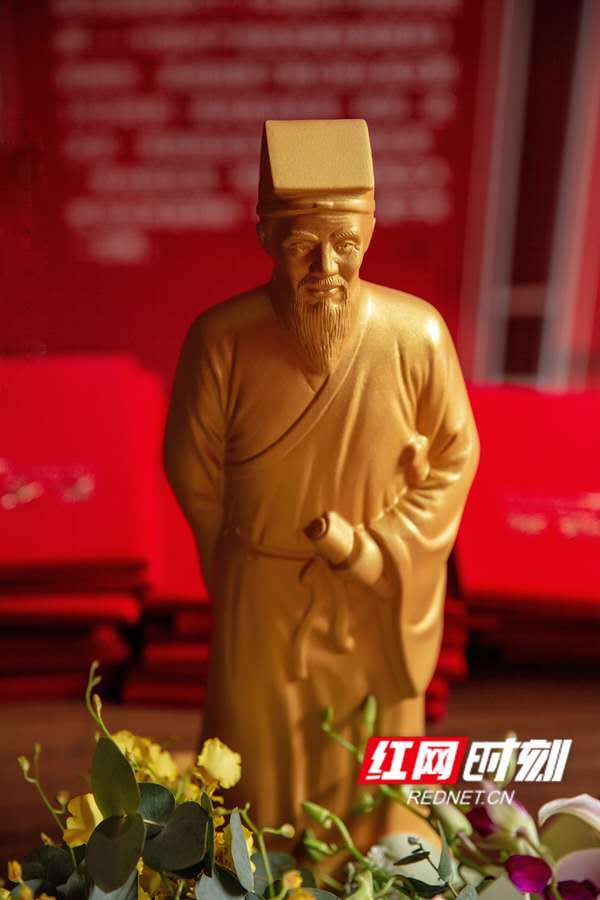
[内容摘要]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规定城邦本身的规模不宜太大,否则不能很好地维系自身的统一。但是在 469B—471C 这几页文本中,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以一种漫不经心的“跑题”式谈话,给出了一段著名的关于“希腊人不打希腊人”的论述与主张,呈现出一幅良善有序的希腊共同体景象和超越城邦视野的全新思想氛围。为什么在柏拉图看来,一个“治理得好的城邦”,似乎由内而外、自近而远,竟然最后一定要超越城邦,走向了对“希腊”这一文明共同体的守护?这一叙述既突破了单纯城邦政治的狭隘视野,又不同于后世关于“普遍主义”帝国的思想逻辑,而是基于某种“情感”的自然转渡,是对亲属与友谊共同体的不断扩充。
[关键词] 柏拉图;苏格拉底;理想国;夷夏之辨;规模
古典哲人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共同体的想象,以“城邦(polis)”为最高形态。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明确指出,“城邦”是人类政治共同体最后的终点与目的,因为它能达到自足自洽的程度,显示在共同生活中自然所趋向的最完全和最高的善。(1) 由此以下,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对城邦政治的推崇源远流长,认为它是人类的自然,构成人类生存的最佳尺度与视野,超越城邦规模的“帝国”和“文明”形态,则往往被认为是不稳定和“不自然”的。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甚至还规定城邦本身的规模也不宜太大,否则不能很好地维系自身的统一。(2) 超越“城邦”尺度的广大区域与人口的统一与治理问题,对他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469B—471C 这几页文本中,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以一种漫不经心的“跑题”式谈话,给出了一段著名的关于“希腊人不打希腊人”的论述与主张,呈现出一幅良善有序的希腊共同体景象和超越城邦视野的全新思想氛围。
本文以春秋“夷夏之辨”为辞来类比并分析柏拉图的这段主张,先是指出它是柏拉图所谓“治理得好的城邦”的诸特征之一,有其确定含义和前后一致性;进而追问:为什么在柏拉图看来,一个“治理得好的城邦”,似乎由内而外、自近而远,竟然最后一定要超越城邦,走向对“希腊”这一文明共同体的守护?它的叙述既突破了单纯城邦政治的狭隘视野,又不同于后世关于“普遍主义”帝国的思想逻辑,而是基于某种“情感”的自然转渡,是对亲属与友谊共同体的不断扩充。在谈话的机锋交错中,这一谈话看起来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要回避“理想国的实现条件”这个主题而采取的迂回拖延,同时也是为“教化”格劳孔而采取的一种修辞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这一表面不经意的“插入内容”却是在提醒我们注意,面对当时和后世纷争不断的悲剧性政治现实,需要人们超越城邦,贯彻“自近者始”这一哲学式的“劝勉”。但柏拉图这一劝勉的真正回响,或许并不在后来列国争伐不息的整个西方历史与政治实践中,毋宁说当我们从中文思想语境审视这一哲学劝勉时,会发现它更接近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中国之为“中国”的政治教义之所在。
1
好城邦的特征:希腊人不打希腊人
《理想国》469B—471C 的内容一般来说要么让人费解,要么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以致后世“造论”并不多,虽然对熟悉文本的读者来说,它众所周知。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突然谈论起希腊各城邦之间的关系,并且他是从城邦中如何对待战士与烈士的话题,突然跳转到“我们的战士将如何对待他们的敌人?”(3) 这一设问的。在格劳孔尚且不明所以的追问下,苏格拉底借机说出可称为“希腊人不打希腊人”的这一大段主张。话题的跳转突如其来却又自然而然,苏格拉底指出,我们的战士:
当他们任何人在战场上英勇牺牲……我们将会去向那位天神打听,我们应该如何埋葬这些如同神灵、如同天神一般的人,应该采用什么特殊形式,根据他的答复,我们将如此照办……此后,如同对待神灵一样,我们将会如此敬奉和崇拜他们的墓地……这又如何?我们的战士将如何对待他们的敌人?……首先,在奴役战俘方面,你是否认为,希腊人应当奴役希腊人的城邦,或者他们应当尽量不让这事发生,并且使宽恕希腊民族这一做法成为自己的传统,以防遭外族人的奴役?(468e—469c)
我们让自己的战士备极哀荣、享受敬奉和崇拜,那么我们是否也不应奴役希腊其他城邦的战俘呢?从这个问题出发,苏格拉底提出希腊城邦、希腊人之间不要互相奴役,应让宽恕希腊民族成为我们的传统,以一致对外;要避免对战败者搜尸取财这种贪婪陋习,要允许敌方运走尸体;战利品更不能拿去敬献给希腊人的神庙,否则会亵渎神灵;不能分割希腊人的土地、烧毁他们的房屋,而至多是夺走其一年的收成作为惩罚。归根结底,要区分希腊人之间的“内讧 (στάσις)”,和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的“战争 (πόλεμος)”。因为希腊人自己之间应是亲属,而外邦人则是外人;亲属朋友之间的对抗只表明希腊民族得了病、发生动乱,但与外邦人之间交战时,双方则是“自然的”敌人;内讧发生,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罪行,他们应该靠和谈而不是战争解决分歧;应该共同热爱希腊人的信仰。
对此,当格劳孔指出这或许只是一个“远为文明的理想”时,苏格拉底则立即指明,目前我们在言谈中创立的这个城邦,它的城民就是这样“既高尚又文明”的,这个城邦将会禀持上述这些义理,恪守希腊人的内外之分,对于希腊人:
他们会友好地开导对方,而不是用奴役或毁灭的方法惩罚对方,他们是训导者,而不是敌人……他们就不会希望去蹂躏对方的土地,因为对方中绝大数人是他们的朋友,也不会捣毁对方的房屋,而只是把争端持续到这么一个限度,当那些制造分歧的人在无辜受难的人们的逼迫下不得不接受惩罚。(471B)
但苏格拉底滔滔不绝地谈论这一突兀的内容,最后被格劳孔有些不耐烦地打断:
就让我们如此定了,这两条以及前面制定的那些,同样都很好。然而,我觉得,苏格拉底,如果某人让你如此谈论下去,你就怎么也不会记得你曾暂时把那个问题搁在一边来讨论所有这些东西,那个问题是,这一城邦政体是否能实现并且凭什么方式实现?(471C)
格劳孔的“不耐烦”暗示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这一大段关于希腊人“内外”之别的“发挥”似乎有些跑题了,我们本来是在筹划和描述一个城邦自身的“政治”,怎么就谈起全希腊来了呢?因此他要将滔滔不绝的苏格拉底拉回正题:在言谈中建立起这个理想城邦的模型之后,现在该谈谈其实现的途径了。
然而,这一不耐烦的“打断”,却不也正加强着一种引人注目的效果么——“跑题”本身及其被“打断”,借助文本叙述中表面的断裂恰恰在吸引着读者的注意。
往前回溯文本或许可以确定这一段内容所处的语境。第五卷开头,本来苏格拉底已经在“言辞”中带领大家完成了理想城邦的基本建构,却在众人的一致要求下,必须要解释一下他前面提及的“妇女儿童公有”问题,于是苏格拉底声称要冒险带大家经历几个“浪潮”:妇女与男子一起参与执政、做护卫者,这是第一个浪潮;妇女儿童公有,这是第二个浪潮。讲完之后,在 462A 处苏格拉底停下来做了个解释,表明这两个浪潮虽然的确一个比一个更惊世骇俗,但“与城邦其余部分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正义而设计的,是“好城邦”的特征。除此之外,好城邦还有其他特征,即下文谈及的所有公民的团结:国家不分裂,看起来最像一个人,荣辱与共、彼此一体,生活中友爱平等,死后备极哀荣,百姓慎终追远。如此之后,才如上所述转入了“希腊人不打希腊人”的主题。
因此从整体语境来看,苏格拉底是在“治理得好的城邦”的意义上,引出了“希腊人不打希腊人”的主张:一个治理得好的城邦,首先内部团结如一人,然后似乎循着由内而外、自近而远的路径,走向了对“希腊”这一文明共同体的守护。这是“好城邦”的特征之一。
对于这样一种主张,我们在中文思想语境中并不陌生。“攘夷”与“自近者始”大抵是《春秋》“夷夏”“内外”之辨的应有之义。春秋笔法,内外有别,因此“侵、伐、战、围、入、灭、取邑”之例各有所分,“王者无敌,内不言战,言战乃败矣”,或者“战不言伐,围不言战,入不言围,灭不言入,书其重者也”(4),这些义例也堪为佐证。此外,春秋大义中,灭人之国、绝人之世,乃是大恶;而反身以存诚、强恕以求仁,治天下先以其国、再诸夏、再夷狄,则是正途。
由此观之,“辩论之风”(394D)似乎把所有言谈中的“建国者们”带到了一个更遥远的维度。“《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5)在类比的意义上,苏格拉底在言辞中建立的城邦成了正天下之始的“其国”,希腊各城邦则堪为“诸夏”,“诸夏”合起来又称“中国”;“内诸夏而攘夷狄”则成为苏格拉底所传达给格劳孔的“大义”之所在。
倘若“自近者始”与“攘夷”可以拿来首先概述苏格拉底这里表述的直接意蕴,那么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除了在“应然”的层面理解这一“夷夏之辨”的内涵,还要在对话语境的回溯分析中,理解自近者始、由己及人的扩充是如何可能的;“攘夷”的逻辑和必要性又是如何被阐述的。唯此才能回答,为什么一个治理得好的城邦必然走向“夷夏之辨”所确立的王者之治。
2
由己及人:非“普遍主义”的扩展
最初建立在自然需求和简单分工之上的农人与工匠的共同体,迫于战争的威胁而需要护卫者,护卫者必须对城邦公民温和、对敌人勇敢,培养这种“文质彬彬”的德性需要“音乐陶冶心灵、体育训练身体”;为了守护在教育中形成的政制(πολιτεία)、守护城邦的风俗与律法,还要从护卫者中选拔统治者。而为了防止护卫者和统治者的腐败,就要促成统治者的个人利益和城邦公共利益的一致。为此,在最严格的正义城邦中,干脆就取消了护卫者们的个人财产和家庭,建立集体生活、供给制,以至于他们的“爱欲”也必须纳入城邦总体的安排之下,不得有家庭,妇女、儿童公有。
在这样的城邦中,所有人都成了平等的“兄弟姐妹”,城邦不仅是“血缘”共同体,也是“友谊”共同体。然后,当苏格拉底提出“希腊人不打希腊人”时,看起来是将这一共同体的外延扩大了:
这不是一个关于人道或博爱的规范,而是一个严格的爱国主义规范。它显示了“给我们的朋友以好处,给我们的敌人以伤害”这一关于正义的定义。而我们的朋友即是我们自己的团体、族群、部落或等级的成员。(6)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在此于是并不是一个基于某种“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论述,而是基于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的种族区分;表面的友谊共同体,以及基于亲属共同体的“自然”状况:“血缘关系定义了我们的部族,而友谊被限制于这同一群人之间……自然使得普遍主义成为不可能。”(7)
这种基于血缘与友谊的认同,在人群中意味着有“亲疏远近”之别,这样的思想在希腊的语境中,首先就与斯多亚派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不同。作为普遍主义的第一个形态,斯多亚派关于“世界城邦”与“世界公民”的设想,超越了民族认同和城邦政治,转而诉诸自然法、宇宙理性、普遍公理,主张在世界城邦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公民,服从同一种普遍的法律。这一世界城邦的设想,后来据说落实在第一个“世界性帝国”即罗马帝国这里,斯多亚派哲学也因此能一度成为罗马的官方哲学。
但丁(Dante Alighieri)正是基于斯多亚派的这种世界公理和人类的普遍目的,提出了其“世界帝国”的概念,歌颂罗马帝国在诸邦争夺中脱颖而出,成为这一世界公理的承担者,只有这样一个一统的政权及其世界君主,才能处理全世界的争议、维持正义。他说:
面对这些事实,我们无疑是可以肯定,大自然注定了世界某一地区的一个民族来一统天下,否则,大自然就会有所欠缺,而那是不可能的……罗马人征服全球,是凭借公理而取得世界统治权的。(8)
“世界帝国”凭借公理取得全世界的统治权,但丁为罗马帝国的崛起作了一个极其理性演绎的合法性论述,似乎由此阐发出了一种基于“普遍主义”的天命之国的概念:罗马民族是高贵的民族,经受了考验,因而受到神意的眷顾、承担天命,成为人类的核心,要为人类全体谋求利益与和平。有论者遂指出,斯多亚的“这种世界主义,体现帝国世界的统治要求,在长达 800 年的希腊化文明和罗马文明中,都是主导的政治伦理精神”。(9)
那么,《理想国》中这段转瞬即逝的苏格拉底主张,尽管建基在亲属与友谊的表象之上,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说,它是先知般地、不经意地、粗略地表达了这样一种以“普遍主义”为根据的希腊帝国的梦想呢?而后来世界历史终于迎来光辉灿烂的“普遍主义”,它主导和照亮了希腊罗马大地呢?
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处的希腊现实中,城邦之间的纷争从未停息。尽管希腊城邦的确会因宗教、共同敌人等原因结成各种各样的联盟,(10) 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常态是摩擦和战争。因与波斯人的战争而兴起的提洛(Delos)同盟也不过维持了 50 多年。而“从公元前 5 世纪初至公元前338 年,在 164 年中,雅典几乎有 120 年处于战争状态,也就是 3 年里有 2 年多在打仗,它从未经历过 10 年以上的和平时期”。(11) 苏格拉底身后,马其顿征服所带来的短暂统一也因亚历山大王的去世而迅速瓦解,进入松散的泛希腊化时期。所以,如果抛开普遍主义“世界帝国”的概念不论,我们是否还可以温和地倾向于以为,无论如何,苏格拉底的主张不过是针对这种混乱现状,在此借机隐约地表达了一种大希腊的理想秩序而已?
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在此没有做冗长的表述,更没有像但丁那样反复通过“三段论”的推理形式来严格论证,只是在话题的跳转中“不经意”地做了过渡,“点到为止”地呈现了这样一种关于希腊人内部秩序的设想与样态。所以我们若以“苏格拉底论希腊帝国”这样的“主题性”标签来叩问文本,就很难整理出一个明确论述。不过,苏格拉底谈话的随意性,却同时非常明确地表明,他没有像斯多亚派或但丁那样,先提出普遍的“世界公理”,然后论证一个尘世中的承担者;当然更不会沿着这条普遍主义路线,像后来的康德那样,将世界永久和平的主张奠基在一个内在的普遍的历史目的论之上。
在此,柏拉图的这一“写作方式”本身,再度体现出“出其不意”的修辞效果。也即是说,那种看起来是“不经意”的“插入”与“跑题”,之所以又显得如此“自然而然”,让我们一路侃侃而谈就愉快过渡到对整个希腊的“关怀”,不正呈现出苏格拉底的主张与那些普遍主义论述有着最重要的区别么:苏格拉底“内其国”以言事,那个言辞中建立的理想城邦及其“既高尚又文明”的公民,从亲属与友谊共同体出发,进一步去提倡和维护希腊秩序,内“中国”而外夷狄,仅仅是一种自然的情感过渡:
对于友谊的规定,其最深刻的原因在于,我们最爱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孩子,而借助扩展(byextension),我们将我们自己视作由种群(ethnic stock)所界定……自然在我们的存在方式中根深蒂固地植入了一种倾向,即偏好那些产生我们(generated us)和继而由我们所产生的人。由此观之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对于苏格拉底及其听众来说就是一种分离(separation)的原理,而非一种一致性(unification)原理。(12)
我们的战士是我们的令人尊敬的朋友、亲属,我们希腊人之间也是朋友和亲属,尽管每一城邦的律法和风俗可以不尽相同。我们应像对待这一城邦的朋友一样对待其他希腊人,他们的尸体我们不能侮辱,他们的城邦我们不能蹂躏。这种自然的过渡,仅仅基于亲属之情与朋友之义的扩展,而非基于某种普遍主义的目的论和宏大叙事,我们希腊人要保护自己,我们共同的敌人是野蛮人。
对比一下《伊利亚特》中普里阿摩斯国王赎回赫克托尔遗体的相关情节,或许可以更加突显这里的“非普遍主义”特征。盛怒的阿喀琉斯为朋友复仇而杀死了特洛伊的英雄赫克托尔,并且侮辱他的尸体、拒绝埋藏他,亦即拒绝给他的敌人以应有的尊重。特洛伊的普里阿摩斯国王来到阿喀琉斯的营帐,双膝跪地抱住阿喀琉斯,吻着“那双使他的许多儿子丧命的手”祈求道:
神样的阿喀琉斯,想想你的父亲……阿喀琉斯,你要敬畏神明,想想你的父亲,我比他更可怜。(13)
“想想你的父亲”,普里阿摩斯以“父亲”作比,想激起阿喀琉斯将心比心的“怜悯”,但
这叙述中更重要的理由是:“你要敬畏神明!”因为无论是战争还是灾祸,在荷马的故事中都是出自神安排的命运。
作为回答,阿喀琉斯说:“老人家,不要再这样刺激我,我已经有意释放赫克托尔,海中老人的女儿,我的生身母亲,作为宙斯的信使来过。”(14) 神的信使曾经来过,让普里阿摩斯赎回儿子的尸体,已经是在众神的安排下成为必然和命令。(15) 因此,在这段允许敌方把死者运走的故事叙述中,第一句话诉诸的是“怜悯”与“恻隐”之心,虽然看起来是通过对恻隐之心的扩充来引起阿喀琉斯出于同情而归还尸体,但最终的促动因素却是为了不冒犯众神。这与苏格拉底有着根本的不同。
3
“回避”与“教化”:苏格拉底式对话
所以,同样是涉及对敌人尸体的处理,苏格拉底的说辞没有诉诸众神安排的命运,也没有诉诸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普遍主义。而是就在与格劳孔的娓娓对谈中,趁其不注意,从亲属与友谊的温情共同体出发,诉诸朋友与敌人的自然区别,开始谈论起“夷夏之辨”,一直等到格劳孔发现“跑题”才罢休。
既如此,再回到文本的原初语境,问题仍然是,为什么一个治理得好的城邦必然会走向这一“泛希腊”主义的道路呢?或者确切地说,为什么既没有众神在场,也没有理性目的论,但这个“内其国”城邦的公民却可以将这种休戚与共的共同体认同转渡到整个希腊呢?这一插入或跑题得以发生之处,正是整段叙事的关键环节或者说“神奇时刻(magic moment)”。
在不经意间,自然而然地,仅仅似乎借助于情感的转渡,我们理想的城邦,那个发端于亲属与友谊共同体的城邦,担负起在希腊民族中“合诸侯以攘夷狄”的重任;为了促进全希腊的团结,它还必须规定战争中的“礼仪”:战争只是以惩罚来告诫,绝不是灭国取邑。如此宏大的主题竟然是以不经意的方式在“跑题”中点出的,这种插科打诨一般、转瞬即逝的“夷夏之辨”真的值得我们反复思忖么?
《理想国》的著名注疏者阿兰 • 布鲁姆对这一段内容的解释就显得非常简短而仓促,只有一段文字,他首先以“回避”为名义指出苏格拉底是在运用某种论辩技巧:
在讨论了女人和孩子的共有及其益处之后,苏格拉底和格劳孔转向这一政制的可能性问题。但苏格拉底似乎渴望回避这一问题,他把讨论转向了他们业已建成的城邦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它将进行战争的方式。(16)
无独有偶,克吕格(Gerhard Krüger)的《理想国导读》也这样解释道:
苏格拉底一直有意避而不谈这个“奇谈怪论”……当第三个,也是“最大最厉害”的浪头打过来时,他突然首先集中精力讨论起正确的战争方式,尤其希腊世界内部的战争问题了。然后他才鼓足勇气,带着对巨大的哄笑之浪富有嘲讽意味的担忧,说出必须由哲人来统治这个中心主题。(17)
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为了回避讨论“理想国实现之可能性”这一问题,而故意拖延或者转移了话题?然而,顺着这一逻辑,至多我们只能说柏拉图的戏剧性笔法只是在此卖了一个“关子”,暂时岔开谈话以渲染一下气氛、激起格劳孔等人进一步追问的欲望,因为毕竟苏格拉底很快还是回到了理想城邦的“实现条件”这一不可能绕开的话题上,同时格劳孔也早就表现得急不可耐(471C—472D),这样对话才有了引人入胜的效果。这种伪装的“回避”,只是为了激起矛盾、渲染气氛,引起格劳孔和读者的兴趣,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一直善于此道,它是苏格拉底式对话的风格,他一直在掌控着对话的进程、一直在变着法儿吸引着年轻人的强烈注意。
此外,即使作为对话人物的苏格拉底为了“回避”、拖延真正的问题,而转移到了“希腊人不打希腊人”这个话题上,可是作为创作者的柏拉图难道不清楚这是一种暂时的离开?我们从文本整体情节来看,这一段插入叙述当然只能是柏拉图的一种有意安排,不过是他的又一个写作“阴谋”。“回避”本身作为柏拉图显白的手法,应该还有别的隐微意图,所以我们不能只从形式上去理解这段内容。在“回避”这个解释路径上,柏拉图研究和注疏家弗里德兰德(Friedläder)给出了更丰富的补充:(18)
希腊人之间是“天然的朋友”,所以他们之间不可能存在着“战争”,只可能有存在着“争吵”或“内讧”。因此,通过这种“友谊”,统一的希腊民族出现了,而我们的国家共同体也正是靠同一种“友谊”而团结在一起的,这就是说,最终希腊民族是一个规模扩大了的城邦。这个思想非常严肃,非常重要,而此时此刻的柏拉图……要把他的消息——徒劳地!——传达给全希腊。柏拉图恰恰在这个地方插入这个告诫,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依然是再次隐藏真正的目标,把它往后推……就是躲避那个我们急切想听到回答的问题,就是……“这种国家究竟能否实现,怎样才能实现”的问题。
弗里德兰德虽然最终也认为,这插入的一段是为了躲避“这种国家究竟能否实现”的问题,但他敏锐地指出在此柏拉图是插入了一个要传达给全希腊的“告诫”,即希腊民族是一个整体,它是通过—正如我们上文所述 —“友谊”这种媒介而悄然实现的,并且这是非常“严肃”和“重要”的思想。当然,在他看来,柏拉图只能以这种看似不经意的方式“徒劳地!”传达出这一对希腊人的告诫。至于为什么“严肃而重要”,又为什么“徒劳”,他没有过多展开阐释。说它“严肃而重要”,或许正因为,它是一种罕见的超越城邦视野的关于希腊共同体的思想,即“希腊民族是一个规模扩大了的城邦”,而柏拉图又是在前后极为隐微的叙述方式中,以非常富有思想启迪的方式呈现出来。说它“徒劳”,或许因为希腊的现实以及往后的历史,都没有听从柏拉图在这里传达的消息。
但是还是有人听到了某种“严肃而重要”的消息。在阿兰 • 布鲁姆仅有的那段阐释性文字中,附带还有另一解释,它是从“教化”的目的来理解柏拉图的这一安排的:
城邦内部的变化引起城邦间关系性质的变化。在这一讨论中,虽然苏格拉底为格劳孔充满爱欲的和好战的脾性提供了得自战争的满足,但大体的意图,是为了缓和战争,并使其人性化。为达此目的,苏格拉底提出一种对野蛮人充满敌意的泛希腊政策。(19)
即是说,为了满足好战、爱荣誉的格劳孔,苏格拉底加入了城邦对外战争的描述;但又为了正确地引导格劳孔的爱欲,他顺从格劳孔的“习俗性认知”的限制,在区分野蛮与文明的前提下,让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像一个大家庭,只有针对野蛮人的战争才被给予肯定。这条叙述线索,这一表面的“回避”,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教化格劳孔这样的年轻人,把他们从“与热爱一个人自己的东西相关的情感延伸到全体人类”(20),从个人到城邦到希腊、到全人类,这是一条会扩展延伸的情感道路。正如前文指出的,一种基于情感的自然过渡,并且扩充为可以关怀全体人类的大慈大仁。
“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21),格劳孔好勇过人,苏格拉底则因材以教,发掘其恻隐之心,以求约之以礼义,并且阿得曼托斯以及所有的柏拉图的现代读者们——那些自负而好斗的灵魂,都可能因沉浸于这段内容而获得情感升华。所以,以“教化”为目的的说法当然成立,对文本解读的立义也很高明。
然而问题的关键似乎仍然在于那个“神奇时刻”,即这种情感扩充何以可能?或者说何以“令人信服”?“城邦内部的变化引起城邦间关系性质的变化”这一仓促闪现的点评之语,究竟道出了什么本质上的、道理上的关联?若不能深入探究这一问题,仅仅指出这种情感升华式的“教化”与自然而然的“转渡”,那么在格劳孔转身沉思之际,是否会觉得这只是靠不住的以情感为基础的道德说教,终究不能获得打动心灵的“理性力量”?只是因为格劳孔此时太急切地想知道那个关于“这一政制如何实现”的问题,他才无暇深究:为什么一个治理得好的城邦必然走向对文明共同体的守护?
4
新秩序的视野:“中国”之为“中国”
“回避”与“教化”之论,对这一段插入的“希腊人不打希腊人”的文本安排的解释,仍然不能满足我们的追问: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所作的这番谈话中关于“希腊共同体”秩序的想象,仅仅出于自然的情感(亲情与友爱)及其扩充,如果不是出于其他种种利益的考量与现实主义的因果联系,怎么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一个治理得好的城邦必然会走向对文明共同体的守护呢?
我们一直在反复追问这一问题,想要一种铁板钉钉的必然性答案,因为似乎觉得情感“转渡”与“扩充”甚至只是一种温情的修辞、个人的体验,或者至少说没有理性的必然逻辑那般牢靠。我们究竟想要一种怎么样的可靠性论述呢?
在列奥 • 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叙述中,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社会是生活在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斯宾诺莎所开创的政治哲学“古今之变”之后的视野中,“自我保存”被上升为首要的个人生存理性与国家理性。国家本身被要求去除道德性,因此,同样是要讨论一种城邦“政制”,例如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和托马斯 • 莫尔的《乌托邦》等等,都只是在讨论“自我保存”所引起的相互战争时,才涉及与其他城邦的关系问题,而与所谓由近及远式的情感“扩充”、关怀人类的“教化”丝毫不相干。
在以马基雅维利为标志的所谓政治哲学“古今之变”中,古典政治的“城邦”视野,蜕变成了近代“民族国家”的主权视野,但其中一以贯之的局限性仍然在于,以此很难理解和想象,也很难构筑起来,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在“希腊人不打希腊人”的主张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城邦与城邦之间和谐的“礼乐秩序”。在近代政治哲学的语境下,基于“自我保存”的国家理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对我们而言,不过是“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自然状态的扩大版。在列国竞争的逻辑中,道德的虚幻性、权力的重要性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始终构成我们理解国家之间关系的基石。
于是,“希腊人不打希腊人”“一个治理得好的城邦必然会走向对文明共同体的守护?”我们至多只能基于冷酷的“政治现实主义”,从利益算计的角度,去这样理解:一个国家治理得好,就会变得更强大,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与不断扩大的利益诉求,就会不断走向扩张,从而成为地区性共同体的守护者。这才是我们容易接受的令人信服的逻辑,某种和平有序的国际关系,只能是霸权及其平衡的结果。而为了论述霸权的合理性,自我中心主义的权力逻辑往往却披上了“普遍主义”的外衣,把特定国家的愿望等同于普世愿望,建构了一种凌驾一切之上的虚伪哲学。
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在漫不经心的“跑题”中,基于“民吾同胞”式的自然情感,一个治理得好的城邦,由近及远、不断扩充,实现“希腊人不打希腊人”,守护文明共同体。我们从“教化”的角度来看,它似乎是在劝勉那些强悍而自私的灵魂,从亲情与友爱这种直接的、合乎自然的情感事实出发,不断“延伸到全体人类”,直至可以通达“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然而不仅如此,除了情感的转渡与扩充,苏格拉底的“希腊”同样有着某种现实的结构,即诸城邦面临共同的威胁:野蛮人。在《理想国》其他各卷文本中,着眼于城邦内部秩序与外部威胁时,野蛮人并未被考虑进来。城邦对外的战争仅仅是因为城邦“发烧了”,人们的需求不断增长,因而引起相互扩张和斗争。唯独在“希腊人不打希腊人”这一段,野蛮人作为希腊共同的敌人被提出来。面对这一共同威胁,“希腊”共同体才清晰浮现,需要各城邦联合起来,构筑内外有别的秩序。一个治理得好的城邦,不仅是智慧和正义的城邦,也是强大的城邦,因此它既会领悟这一形势,也有能力担当这一义务。《理想国》在言辞中建立的这个理想城邦,恰恰就是治理得最好的城邦,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最终将“夷夏之辨”必然地带到它的视野中来。
一个治理得好的城邦必然会走向对文明共同体的守护。这样一种“希腊人不打希腊人”的主张,及其实现次第,既不同于狭隘排他式的城邦视野,也不同于“普遍主义”目的论,更不同于利益算计式的“政治现实主义”。它首先是在“夷夏之辨”的视野下承认有“希腊”这一共同体及其义务,因此不同于单纯的城邦竞争、唯我独尊;它建基于自然情感的扩充与维护共同体的理性自觉,因此不同于普遍主义目的论与天命之国的优越论;它首先为的是共同体的好处,而不同于为一己之私去争夺霸权,去搞“分而治之”、零和博弈。
因此,当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主张“希腊人不打希腊人”时,他似乎构建出了一种新的理想的“中国”观念,一幅和谐有序的共同体图景。而实现它则需要“从近者始”,先正其国其民。先做一个治理得好的城邦,然后可以也必然会走向匡正天下;所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22)
在希腊和西方历史上列国竞争的悲剧性政治现实中,柏拉图的这一未能实现的主张,读起来更像是回响悠远的哲学式劝勉;但却更接近中文语境下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之为“中国”的政治教义之所在。在全人类面临共同的全球威胁、日益凝结为命运的共同体时,“中国”之为“中国”的教义和教化,超越城邦与主权国家的相互竞争,包含着新秩序的可能性。
本文注释
(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3a,中译文参考吴寿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
(2) 柏拉图:《理想国》423B,中译文参考王扬译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年。
(3) 柏拉图:《理想国》469C。
(4) 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曾亦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240 页。
(5)“《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春秋公羊传 • 成 公十五年》,见《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463 页。
(6) Stanley Rosen: Plato’s Republic, A Study, New York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96.
(7) Stanley Rosen: Plato’s Republic, A Study, p.196.
(8)〔意〕但丁:《论世界帝国》,朱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42—43 页。
(9) 姚介厚:“斯多亚派的自然法与世界主义思想”,《社会科学战线》,2010 年第 5 期,第 30 页。
(10) 例如古老的“德尔斐近邻联盟”,既是出于维持共同的宗教信仰、神庙管理,也是出于共同防御的需要。见〔法〕克琳娜 • 库蕾《古希腊的交流》,邓丽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51—152 页。
(11)〔法〕克琳娜 • 库蕾:《古希腊的交流》,第 155 页。
(12) Stanley Rosen: Plato’s Republic, A Study, pp.196-197.
(13)〔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年,第 570—571 页,即卷 24,486、503 行。
(14)〔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第 573 页,即卷 24,561—562 行。
(15)〔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第 552—554 页,关于如何处理赫克托尔的遗体,众神有争执,宙斯力排众议,安排了让普里 阿摩斯赎取儿子尸体这一策略。
(16)〔美〕阿兰 • 布鲁姆:《人应该怎样生活》,刘晨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年,第 125 页。(17)〔美〕克里格、〔德〕弗里德兰德、〔德〕沃格林:《〈王制〉要义——柏拉图注疏集》,张映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年,第 13 页。
(18) 同上,第 124 页。
(19)〔美〕阿兰 • 布鲁姆:《人应该怎样生活》,第 125 页。
(20) 同上。
(21) 语见《论语 • 先进》,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128 页。
(22)《春秋公羊传 • 成公十五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何休注云: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 乃正夷狄,以渐治之。见《春秋公羊传注疏》,第 463 页。
作者:唐杰,重庆大学经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副教授
本文系《东方学刊》总第8期“政治”栏目文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