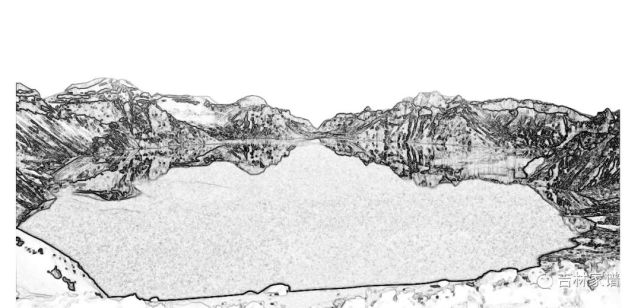
满族文风渐盛
作者富察宝仁 吉林家谱
满族是一个古朴骁勇又善于学习、努力进取的东北少数民族。满族的正规文化教育,起始于后金时期,后逐渐发展并建立了有别于京师(北京地区)旗学的东北盛京“旗学”和吉、黑两地的“满学”。东北地区满、蒙、汉八旗的官旗学、满学及官义学、蒙学、宗学、觉罗学、翻译学等,为关东满族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先决条件和物质基础。
清前期,偏远的东北地区是清政府发配流人之地。这些流人多达十几万,其中有大批中原文人儒士,他们的到来不但携带来大批经典书籍,还被延请或开设私塾教授满汉八旗官兵子弟,从而,对东北地区满族文化及满汉文化的融合、繁荣兴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东北地区地处华夏边域,数千年来远离锦绣繁荣的中原文化,尤其是这里
聚居的山林渔猎民族生产力低下,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文化极不发达。直到明朝末年,满族的先人女真人,以及赫哲、鄂伦春、索伦、瓦尔喀、飞牙喀、库雅拉等同属满—通古斯语族的东北诸多少数民族,尚无本民族的文字。
努尔哈赤举兵兼并女真诸部,联络蒙古、反明立国后,命巴什克额德尼和
噶盖创制了满文。清定鼎北京之后,在盛京、吉林、黑龙江关东三将军辖地,陆续建立了一些八旗官学、义学及满汉族学堂、蒙古学堂,历经二百余年,对满族等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偏远的东北满族地区逐渐地出现了文化繁荣的景象。
清初之时,东北地区尚未建立八旗官学,只有一些知晓文化重要性的八旗
高官,才会延师授课教育自己的子弟。宁古塔将军巴海就曾聘请流人吴兆骞“为书记,兼课其二子,长名额生,次名尹生”。巴海给自己儿子制订的学习内容是“昼则读书,晚则骑射……依次而射,射中者得箭”。可谓是关东满族最早的“国语骑射”教育,被流配到宁古塔的文人杨越、陈敬尹,也曾被聘请“授满汉子弟书”“教之以礼仪”。大批汉族流人的到来,使得东北尤其是吉、黑两地的私学教育得到了发展。这些汉族文人学儒也得到了满族官员和百姓的尊崇,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安珠瑚、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都十分“雅重文士”,对他们“待以殊礼”。《宁古塔纪略》载:
宁古塔满洲,呼有爵而流者,曰哈番,哈番者,汉言官也,而遇监生、生
员亦以哈番呼之,盖俗原以文人为贵。
满族人正直淳朴、宽厚善良,素来尊重长者、敬重文人学士,清代汉人方拱乾著《绝域纪略》载:
“八旗之居宁古塔者,多良而醇,率不轻与汉人交。见士大夫出,骑必
下,行必让道,老不荷戈者,则拜而伏,过始起。”
满族重视教育由来已久,金代时便创制了女真文字教子弟以习,并沿用了
二三百年。后金(清)太祖努尔哈赤不但自己精通蒙汉文字,还命人创制了满文,并将浙江绍兴府的儒者龚正六延请到家,尊为师傅极其厚待,命其教授自己几个儿子读书。努尔哈赤的这些儿子都知书达理又能征惯战,全皆因努尔哈赤对其进行文化教育的结果。
天命六年(1621),后金与明朝的战斗节节胜利,相继攻下了辽河以东广大地区。如此战火纷飞之时,努尔哈赤却还想着如何教育八旗子弟,培养文武兼备的开疆治国的人才。这年七月他下令,命在各八旗之中设学堂,教授“国语骑射”,并选在文化方面颇有才华的巴克什钟堆、博布黑、萨哈连、吴巴泰、雅兴噶、阔具、扎海、洪岱等8人为八旗师傅,专心教育,不参与战事。努尔哈赤郑重而言:“对在你们之下的徒弟和入学的儿童们,能认真读书,使之通文理即是功。”此可谓满洲八旗官学之始。由于此时战事频繁,故教育事业进展缓慢。
天聪元年(1627),太宗皇太极即位之后,也很重视文武两手治理国家,制定了“以武功戮祸乱,以文教佐太平”的治国大策。皇太极即位之后的第三年,便施行了两大兴文教之举。一是在盛京修造文庙,以“崇文重道”。这一举措,标志着皇太极接受了儒家思想,以此来表达儒家思想是国家社稷“肇万年有道之长也”。二是开科取士。这是后金(清)政权第一次开科,参加应试的有满、蒙、汉各族学子,且不拘一格选材取士,甚至连“包衣阿哈”(家奴)也可应试,“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以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拔出”,共录取200余人。此举大批的满汉族儒人学子受到提拔重用,极大地提高了后金(清)政权官员的文化素质。
天聪元年开科后,大批汉族文人入仕后金政权,皇太极也受到了很大震
撼:“八旗子弟不读书,‘未尝学问,不明理义’,怎作国家社稷的栋梁之材?”他觉得对八旗子弟进行文化教育,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大事,于是在天聪五年(1631)颁布读书令,旨谕:
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
满族乃白山黑水间的渔猎民族,素来有重武功而轻文事的传统习俗,故许
多贝勒、王公并不重视,阳奉阴违而行。皇太极决心以强制手段推行八旗子弟的文化教育。《清太宗实录》载有皇太极怒斥诸贝勒大臣之“读书谕令”:
朕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所以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
实有赖焉。闻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者……如有不愿教子读
书者,自行奏启。若尔等溺爱如此,朕亦不令尔等披甲出征,听尔任意
自适。
此读书谕令甚有意思,明廷将领贪生怕死皆不愿披甲出征,而后金这些满
洲八旗贝勒王公,披甲出征、厮杀、作战是各个争先恐后。一是,骁勇好斗的弓马骑射的民族传统所致。二是,后金政权有效的奖励措施,战胜得的财物全部论 功 行 赏 。1618年,努尔哈赤率二万八旗兵征明得胜,将所获之 30 余万人畜财物全部奖赏给诸旗兵将。
后金(清)升官晋爵也很公道,视军功大小而晋。皇太极以“不教子读书”,便“不令尔披甲出征”来挟制。若不披甲出征作战,何来军功,怎分得财物?没有军功又怎会升官晋爵。如此一来,皇太极的“读书令”,很顺利地落实了下去。
皇太极的读书令落实是落实了,但许多贝勒大臣敷衍了事,将读书认作是
极苦且无用之事,并不令子弟认真读书。汉臣胡贡明针对此状况上疏道:“当于八家各立官学,凡有子弟者,都要入学读书,使之无退缩之辞。”《天聪朝臣奏议》载胡贡明之疏道:
好师傅,方教得出好子弟,当将一国秀才,及新旧有才而不曾作秀才的人,敕命一二有才学的不拘新旧之官,从公严考,取其有才学可为子弟训导的,更查其德行可为子弟样子的,置教官学……小则教其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大则教其子、臣、弟、友、礼、义、廉、耻之道。诱掖奖功,日渐月磨,二三年必将人人知书达理,郁郁乎而成文明之邦矣。
这个汉族大臣胡贡明还奏请皇太极颁旨,应尊师重教,他说:对教学师傅
应“顺设养廉之典,供以衣食,使其无内顾之忧。尊以礼貌,使其有教授之诚。崇以名分,使其有拘束之严”。胡贡明之疏十分详细具体,深受皇太极的重视依奏而行,故而他的读书谕旨得以更好地落实。
皇太极虽然力推满族臣民文化教育,但始终不忘“国语(满语)骑射”为清
王朝立国之本。天聪八年(1634)四月,皇太极谕令:“朕闻国家承天创业,各有制度不相沿袭,未有弃其国语,反习他国之语者。事不忘初,是以能垂之久远,永世弗替也。”他告诫众臣“清语为国家根本”,又强调“我国家以骑射为业”,应“时时不忘骑射”。
满族是渔猎为生的山林民族,十分重视习武骑射,早在五六千年前,满族
先人肃慎人便以“楛矢石砮”入贡而闻名中原。满族先人靺鞨人建渤海国,女真人建金国,均是以弓马骑射武功所成。满族长久以来便有俚俗:家中生男孩便在门上挂一小柳枝弓箭,俗称“公子箭”,以标识此家又诞生了一个小男孩,并有祈祝此子日后成为一个弓马骑射巴图鲁(勇士)的美好祝愿。狩猎骑射,是满族先辈几千年山林生活形成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国语(满语),是满族重要的文化特质,所以这“国语骑射”自努尔哈赤、皇太极时起,至清末都是清政府对东北地区的满族人进行教育的宗旨。
清政权定鼎北京之后,在东北的盛京和吉林、黑龙江三地区,建立了两种
文化教育宗旨有别的八旗官学。盛京地区建立的八旗官学、八旗义学、宗学与觉罗学,有别于京师北京城的旗学,强调的是满汉文并重,但实际上是鼓励满族人学习汉文,以培养清政府亟须的通晓满汉文的人才。
盛京的旗学,是满八旗学班教读满书,习弓马步箭;汉八旗学班教习满汉
书,习弓马骑射。盛京旗学突出的是学满书、学弓马,以“国语骑射”为重。吉、黑两地的八旗官学和义学教学宗旨,与盛京旗学又有所别,只习满书、弓马骑射,故而称之“满学”,因其系国家官办故又称“满官学”。
清代,东北地区的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地,因八旗官办的旗学、满学数量有限,学生名额有限,满足不了满、蒙、汉八旗子弟的求学,故各地区又增设了许多八旗捐建、国家公助的八旗义学。盛京城为了解决爱新觉罗宗室、觉罗这些皇亲国戚子弟的文化教育,还专门设立宗室官学、觉罗官学。吉林城为解决众多巴尔虎等蒙古八旗子弟的求学,特建了蒙古官学。为更多地培养满汉文翻译人才,特建了东北地区最早的专业翻译学校,即吉林翻译官学。自康熙三十年(1691)盛京城建八旗官学始,至清末止,二百余年的时间里,东北地区的满、汉、蒙古八旗子弟的八旗官学、义学等各校毕业生,至少有20万人以上,从加快了东北地区文化的发展。
从东北八旗官学走出来的能文能武、骑射优异的八旗子弟从基层做起,后来许多人做到了中高级军政官员,率领满、汉、蒙古八旗劲旅,在东北抗击沙俄和日本的武装侵略,在西北、新疆反击沙俄的侵略和平剿勾结沙俄卖国的准噶尔、阿睦尔撒纳等叛乱,在京津地区抗击美英法俄等八国联军的进攻,在这些守土卫国浴血奋战中,八旗兵都是清王朝的精锐劲旅之师。当然,在平息捻军、黑旗军、大刀会、红枪会、白莲教乃至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军的战斗中,从东北调来的满蒙汉八旗兵,也是清王朝的主力
部队。因为这些八旗兵受到了“武功戮祸乱、文教佐太平”的儒家传统教育,只知忠君报国,根本不知晓农民起义对历史前进的推动作用。
八旗官学、义学在东北广大地区的普及,不但使满族受到了正规教育,也
使后加入的赫哲、鄂伦春、索伦、锡伯、瓦尔喀、库雅拉等许多操满—通古斯语的伊彻(新)满洲人,第一次受到了文化教育,得以“广布教化,多方训迪”。使得这些早年只知弓马骑射渔猎,粗犷豪放无拘无束的民族,“大非昔比,礼貌言谈,亦几于满汉无异矣”。使这些满洲共同体的新成员,成为知礼节、懂教化的八旗新满洲,他们驻防在东北广大地区,成为御敌守土捍卫边疆的重要力量。
盛京八旗官学、义学重满语文教育,吉、黑两地八旗官学、义学只进行满语文教育,维系了满族的语言文字,较好地保护了满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俚俗。清政权入关之后,“从龙入关”的百万满族人迅速地被锦绣中原的汉族俚俗、语言文字所同化,渐染汉俚汉习。正像乾隆皇帝所言:八旗子弟“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俗”。此乾隆朝距满族入关仅百年之时,但关内许多满族人已不会说满语,更不要说满文了。
此时,关外的满族因施行封闭的“国语骑射”国策,所以人们讲的是满语,用的是满文,甚至许多汉军八旗人和数十万中原流人流民也在使用满语满文。
清代,嘉庆年间的西清所著《黑龙江外纪》中,记载了一些有关满语满文的轶事,人们可以从中窥豹一斑。
当时,吉、黑两地的时宪书(历书),是由清廷的钦天监颁发的满文版,由官员请领,第二年春在各地赠阅或买卖。当时也有汉文时宪书,而且到货时间也早,“然,土人(满族人)惟以清文(满文)为重”。由此可知,因文化教育的普及,清中期时东北地区满文已经在大量流行使用。西清在《黑龙江外记》中说:
余见土人家清文一帙,叙奇三上书,始末甚悉。且言奇三将上书,请
于其母,母曰:“救一部出汤火,即死,不辱汝父,吾何恨!”此文疑即奇三作,亦达呼儿巨擘也。
此文虽短却从中可以知晓许多陈年旧事。达呼儿即打虎儿,即今之达斡
尔族。达斡尔族的一首领奇三,用清文(满文)上书朝廷(或黑龙江将军),说明当时满文在达呼儿等伊彻满洲(新满洲)中普遍使用。虽然奇三上书之事不清楚,但其为救部族而敢赴汤蹈火不畏死的精神,实乃令人敬佩。其母亦明大义、识大体,为救族人出苦难宁可儿子赴死的操行,亦可为妇人之楷模。
西清在《黑龙江外纪》中,还记载了自己所见的满文词曲,“满洲曲,类古乐府”。他讲“长篇短句,意皆类是,然多拍手以歌”。满语“阿穆巴摩萨齐斐图们阿尼牙德伊集密”,译言为“伐大木,烧亿万春也”;“阿穆巴博商阿斐阿卜开克什德班集密”,译言为“巨室成,荷天恩也”等,确实有中原汉古乐府之美韵。
西清乃清重臣大学士鄂尔泰的曾孙,祖上“从龙入关”世居北京,他从北京
调到黑龙江为官,故以京城人的眼光把当地驻防的陈满洲及新满洲的赫哲、索伦、鄂伦春、达呼儿、锡伯、瓦尔喀等族人,都视为“土人”,而忘记了自己的先人当年也是关东的土人。西清所见所闻,黑龙江各驻防城的新、陈满洲及蒙、汉八旗官兵的公务文牍、日常生活及歌词唱曲,使用的都是满语满文。其实也是如此,《吉林外纪》讲:
吉林地域本乃“满洲故里,蒙古、汉军错屯而居,亦皆习为国语(满语)”。
《黑龙江志稿》讲:
黑龙江地区“满蒙汉八旗,并水师营丁、官屯庄丁,二百年来向读清书(满文书)。”
清代的一些前朝逸闻,也从侧面讲述着东北广大地域的各族人们通用满语满文之旧事。
乾隆二十九年(1764),因新疆地区地广人稀难以抵御沙俄的入侵,清政府从盛京地区抽调满洲锡伯族官兵一千余人,连同家属计三千余众,西迁至新疆伊犁地区屯垦戍边。他们的后人即今天的新疆锡伯族,由于地域偏远民族语言文字保护得很好,至今仍在讲满语使用满文。
清代,东北地区的八旗官员,因不懂汉语汉文而无法高升迁补,汉人因通晓满汉语言文字而升官、经商发财的,都是极平常的事。乾隆九年(1744),盛京工部满主事一职空缺,吏部便拟以宁古塔驿站官萨哈那升补。
萨哈那因不晓汉文难以胜任,权衡之后奏称:“吾不识汉字,情愿在本处效命。”因满语满文在东北地区广泛流行使用,为了生活、办事方便,许多汉八旗人及流放至此的汉族流人都会满语满文。
汉八旗官员会满语满文很容易升迁自不待言,许多流配于东北苦寒之地的汉族流人,因通满语文字得以任职升官,经商成为巨富大贾者也不是少数。
《黑龙江志稿》载,一流人叫陈昭令,因“精通满汉文理”,被任命为官庄的拨什库。流人陈敬尹、周长卿曾颠沛流离生活无状,后来努力学习满语满文,“贫而通满语,则代人贾(经商)”被人称为“掌柜”,一年可以得三四十金。
清朝的康、雍、乾、嘉时期,东北地区出现了满族文化的繁荣,除了清政府在此建立了许多八旗官学、义学、宗学、觉罗学、翻译学等学堂之外,几十万汉八旗民众及流配至此的汉族文人学士,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早在后金之时,皇太极为培养能文能武的人才下了读书令,命八旗子弟读
书学文。可当时满文创制刚成,主要用来发布政令、记录档案,还设有用满文编制的教材。皇太极决定用汉人的经典文献为教材。于是,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旨谕:设立文馆,并命巴克什达海及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满族文人学士急速翻译汉文典籍。
满洲文人达海不愧为巴克什(文化有成就者),但英年早逝,38岁便病死。他病死之前,组织满汉文人学士,译完了《素书》《三略》《万宝全书》《刑部会典》等巨著,尚未完成的还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演义》《大乘经》等传世经典。这些汉传统文化经典被翻译成满文后,作为教材流行了二百余年,在东北广大地区广泛地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西清于嘉庆年间在《黑龙江外纪》中写道:
土人无问何部翻译,《通鉴纲目》《三国志》(案,此乃翻清文《三国演
义》,国初盛行,非陈承祚书。原注),类能强记,剽为议论,而不知读翻译四书五经。
满族八旗子弟读这些汉文化经典之著,非像汉族学子从读四书五经为始,
但终归是学习了汉文典籍接受了中原汉文化,从而打破了以长城山海关为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已维系二千余年的“华夷之辨”。正如清初到宁古塔省亲的汉人杨宾所诗:
谁道车书是一家,关门依旧隔中华。
已看文字经重译,更裂军繻过五花。
清朝前期,吉林、黑龙江等东北地区是发配汉族流人的重要地区,因此有
大批中原汉人被流放至此。康熙朝,吉林、宁古塔等地已是“迁以众多,聚五方之人杂处”。这些流人中有大批文人学子,甚至还有一些江南名儒,他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汉文化,还潜移默化地推动了东北地区尤其是吉、黑两地文化教育的繁荣发展。
清顺治、康熙年间,流配到吉、黑地区的汉族流民,据不完全统计有几十万之众,其中仅吕留良案,被发配到黑龙江地区的就有 500多人。还有许多人是因科场案、通海案及各种文字狱案而被牵连的文人学子,其中较为著名的便有吴兆骞、钱威、钱志熙、方拱乾、杨樾、王雨亭、张缙彥、方登峰等数百人。这些人家境大多都很富裕,他们被流配关外时,因读书之所好携带了大批汉文图书典籍。杨宾在《柳边纪略》中载道:
宁古塔书籍最少,惟余父(杨樾)有《五经》《史记》《汉书》《李太白全集》《历代古文选》《昭明文选》。周长卿有《杜工部诗》《字汇》《盛京通志》。呀思哈阿妈有纪事本末。车尔汉阿妈有《大学衍义》《纲鉴》《皇明通纪纂》。
杨宾在蛮荒之地宁古塔,见到其父及流人文者有大量书籍并不足为奇,称
奇地是一些满洲人也有些汉文书籍。嘉庆年,从京城而来的满族官员西清,也很惊奇在堪称蛮荒的黑龙江地区发现了许多汉文书籍,他在《黑龙江外纪》中讲:
尝见土人(当地满洲人)家中有内版《尔雅》《盛京通志》《八旗通志》
《词林典故》、写本《春秋左氏传》、汲古阁《五代史》、古香斋《渊类鉴函》、坊刻《通鉴纲目》《史记》《汉书评林》……
其实,当时将汉文书带到关外最多的还应数吴兆骞,乃“赁牛车,载所携书万卷”,简直就是带来一个小图书馆。这些流人携带而来的书籍,犹如苦寒的关东大地吹来了缕缕春风,对汉文化的传播和东北地区满族文化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东北地区的满族人淳朴粗犷不识文字,故对汉族文人十分尊敬。正如汉人杨宾所言:“流人之中,尊显而儒雅者,与将军辈等夷交,年老者,且弟视将军辈,况下此者乎!”流人中之许多大儒,都有被巴海、萨布素、安珠瑚、那启泰等吉、黑两地将军延请为子弟教书的经历。
西清在《黑龙江外纪》中,曾记述了一则趣闻。内地江苏常州人士龚兴瓒,携家口被流配至齐齐哈尔城。其妾生有一男孩叫宝宝,甚是聪慧好学,九岁时便以博学名冠全城。据讲,这小宝宝对《四书》《五经》中的《易经》研究得最为透彻。齐齐哈尔乃黑龙江将军驻防之城,将军那启泰闻听有此神童,便命人将其请到将军府,与他请教“《易》之大义”。
那小宝宝问那启泰道:“乾为天,为父;地为坤,为母。父母一而已。我乃一爹而二娘,然则,地固可多于天欤?”
将军无从以对。
小宝宝慢道:“在常州为江南地,黑龙江为塞北地,地虽多,其实一也!”
身为黑龙江广大地域的将军,朝廷的一品大员,可谓万人之上的高官,竟
恭恭敬敬地请九岁的孩童讲《易经》,可见满族人对汉族文化人士的尊崇。
清代,流放到东北地区的文人学士,写了许多记述关东风物、满族民风俚
俗的纪实文献,《柳边纪略》《宁古塔纪略》《宁古塔山水纪》《秋笳集》《研堂见闻杂记》《黑龙江述略》《绝域纪略》《龙沙纪略》等甚多,通过诗文记述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史资料,也促进了东北满族地区文化的发展。
在这些汉族流人的笔下,早年那“性直朴,习礼让,务农敦本,以国语骑射为先,兵挽八力,枪有准头,骁勇闻天下”的新、陈满洲人,因清政府官学、义学、满汉学等学堂及文庙的广泛建立,开始逐渐知书达礼,甚至还出现了满族秀才等文人学士。在汉族流人文人学儒无声的助推之下,东北地区的满族逐渐展现了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