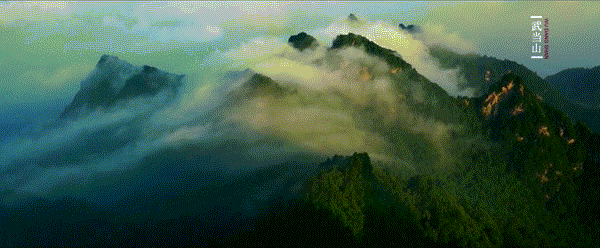有的人想“修仙”,有的人想逃离现实生活,有的人想回归生活的节律感……
这些问题,并非上一趟武当山做义工就可以解决的。
到武当山道观当义工,你要准备一份简历。
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和健康证明,这是最基本的,余下的你可以自由发挥:
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分数,微信公众平台运营的熟练程度,跑800米所用的时长,认识简谱或五线谱,会洗菜和切菜,心态稳定到即使登上1612米的天柱峰也不会恐高,等等。
或者干脆什么都不点缀,道长会根据特长一栏的空白,“因地制宜”地分配给你技术含量要求不高的工作——去紫霄宫或太和宫的某一片区域扫地。
△紫霄宫 / 图虫创意
和武当山道教协会紫霄宫管委会主任王芳道长通过QQ联系上、定好上山日期以后,你需要买一张火车票或者飞机票,准备足够的衣服和驱虫药水。
秋冬季还要多准备一些热水袋——武当山有着与海拔匹配的寒冷。
而道观因易燃的木质结构,属于特级防火单位,取暖设备难以令适应暖气的城市人满意,甚至你的Kindle和电脑都会被冻得开机困难。
△紫霄宫 / 图虫创意
跟看重学历的企业单位或者看重经验的NGO(非营利组织)不同,道观录取义工的标准是“随缘”。
因此大多数申请者最终都能顺利踏入义工宿舍,除非床位已满——那只能说明你实在无缘。
“来一起开启修仙之路啊”
1月24日,因为新冠病毒肺炎的暴发,位于疫情重点地区的武当山封山,十堰封城。去年10月来武当山大岳太和宫做义工的行李因此滞留。
在豆瓣和B站上持续更新“武当山修仙日常”的行李,经过6个月的适应,已经将在道观的作息稳定下来:用道家养生早餐冰糖水煮苹果开启一天,偶尔侍奉观内灵兽(流浪猫);
研习笛、箫、树叶等多款民间乐器,制止众多逃票、在观内烧纸、乱丢硬币许愿的游客“作妖”,参与冬季特有的“冰雪奇缘”铲雪活动,还能免费领取铁锹一把,无限次体验在风雪中御锹滑行。
△武当山的修仙日常 / 微博截图
去年,人类学专业毕业的行李辞去做了5年的出版社编辑工作,在北京的胡同开了一个“快闪式”小卖部,用短短几个月时间从令他感到迷失的工作状态回归柴米油盐的生活。
作为一个喜欢观察不同群体、时常切换生活模式的人,行李从朋友谢九那里听说了武当山招募义工的信息,在他看来,这是想象之外的一种身份。
同时,在国内众多招收义工的道教场所之中,相对于其他背景繁杂、难以分辨专业与否的道观,武当山招募信息更公开透明,流程和管理也更正规、安全。
△紫霄宫招募义工的官方微博 / 微博截图
一开始,行李憧憬这样一座幽密的“人间净土”式道观:与世隔绝,道长们仙风道骨,在苍松古刹里静听晨钟暮鼓,闲看云聚云散;日子清淡如水,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
他甚至幻想会不会有高人教他掐诀念咒,或碰上奇幻际遇。
就连武当山太玄紫霄宫官方微博也在2020年武当山道教学院招生简章的宣传语中写道:“来一起开启修仙之路啊。”
由于武当道观的被动曝光量大多来自武侠、玄幻作品,而主动曝光又相对低调,这种源于武侠小说和影视的斑斓想象,成了部分上山做义工的人的“误会”。
有些义工去紫霄宫(紫霄宫是武当山道观行政中心,也是招募义工的主要场所)体验,有一种免费旅游的心态。
武当山是5A级风景名胜区,道观里包食宿,斋堂的素食三餐还算丰盛,有免费的公共浴室和卫生间供使用,除了日用品要自己购买,基本可以承包所有生活需求。
愈热情的人有时愈容易放弃。
随兴而至的太极功夫爱好者、看过金庸或梁羽生小说有“修真”想法的中二年轻人,以及从事教师、医生等体面工作的人来到这里,觉得每天扫地干体力活儿很委屈,同时又要受观里规矩的制约,就会提前下山。
“像回到了农村老家,很乡土”
提到“千层楼阁空中起,万叠云山足下环”的武当道观,会默认它拥有落后于山下的生活节奏:网络不够稳定,硬件设施不够宜人,需要种菜挑水自给自足,没有过度社交。
用义工姑娘芋圆的话来说,“像回到了农村老家,很乡土”。
芋圆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大四学生,喜好古风文化。很久以前,她读过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书中讲述了作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亲身探访隐居在终南山等地的中国现代隐士的故事。
因此,芋圆想象中武当山的道士们也过着“隐士”般的生活。
△在山岩间隐隐约约 / 图虫创意
从雾霾阴沉的北京跨越1000多公里的地理距离来到武当道观后,眼前的情景却让她深感熟悉:台阶上的凉席晒着药材,黝黑的道长坐在低矮的板凳上聊天,阳光灿烂,粮食曝晒,像回到了乡下老家。
义工的生活每天都遵循着相似的节奏,日复一日。
早上六七点起床,和道长们一同上唱腔优美但听不太懂的早课,上午和下午分别进行3个小时的劳动:有时是扫地,把道观里的落叶、灰尘扫在一起;
有时是清理垃圾,可能会在某个香炉底掏出某个游客虔心上供的猕猴桃;有时负责值殿,引导游客们安全进出并合乎礼仪地跨越门槛;有时是采摘药材(比如黄精),或者给午饭用的100斤萝卜擦丝。
△义工的活其实并不轻松 / 微博截图
“上山下乡”的农活重复了几天,过惯了丰盛日子的芋圆觉得太无聊。
她在制作纪录片《白日梦想家》时被工作伙伴指责“不懂真正的纯粹是什么”,因而赌气上山,抱着“逃离原有生活”和“想看真正纯粹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目的而来。
她问道长为什么要安排自己做这些事,对方回答:“把你内心的事情扫一扫,还能增强体力。”
忽然有了大量闲暇时间,芋圆“闲得发慌”,还是选择把时间托付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上山两天后,她在手机上重新下载了VOA英语App,一边除草,一边听有关特朗普的新闻——在远离城市的陌生环境里,仍要寻找一些熟悉的事来做。
从较低的工作强度和宽松的监督制度上来说,义工劳动更像一种户外健身和放松。逐渐适应以后,芋圆发现,农活带来的美的感受大于它带来的疲劳。
在大殿工作时,她能注意到阳光微弱的偏移,周师兄吹笛子和高师兄伴唱的声音会时不时飘进来。
“生活变得非常简单”
最初跟行李提到武当山义工招募信息的谢九,也持有和芋圆一样“逃离原有生活”的想法,在去年5月到紫霄宫做了一个月义工。
2014年,“全真道士梁兴扬”成为微博网红,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大众对道教的刻板印象,引发社会对该群体的关注。
和行李一样也是人类学专业出身的谢九,从那时开始关注国内的道教组织,“在当代,这样一个非常有历史的组织会以什么形式存在?我实在是有点好奇”。
△这位博主打破了大家对道士的印象 / 微博截图
去年,负责一个“费心费力”的品牌公关项目的谢九因为工作特别辛苦,自觉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早上起不来床,晚上睡不着觉,时间上的丰俭不再由人。
在无尽的事务让她难以招架的时候,她思考究竟能不能找到一种生活方式,让自己更关注生活的“节律”,“我希望自己(至少)有好的生活表象,不想混混沌沌”。
当时,她关注的紫霄宫官方微博每天都发清晨日出的照片,让她觉得山上的生活是有秩序、有要求的。“比如早上6点你就是要起床,就是要去做事情。”
尽管市面上有很多治愈效果明确的禅修班,但在她看来,短期内人为干预的课程不太可能达到某种目的。
“比如我去山里走一趟就升仙了?不可能嘛。”
到武当山道观做义工,谢九想亲身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不只是截取其中的一个显著片段,而是接受它完整的面目,“不是一种我刻意营造的实验室般的小环境,而是本身真实存在的一种生活状态”。
做义工后,一度在工作里承受多方压力的谢九感到“生活变得非常简单”。
平时的生活里,除去用手机主动获取的信息,光是所处的主导环境和主导力量分配给每个人的信息就已经饱和了,也会发生大量社交活动,“面对社会这个庞大的信息体,我处于被大量信息规训的状态”。
而紫霄宫给予谢九的信息量,只有她平时生活的20%—30%。
△武当山风景 / 图虫创意
每天清早起床洗漱,谢九会听到位于紫霄宫大殿右侧那面大鼓传来“咚咚咚”三通鼓声,意味着早课即将开始。
穿好衣服出来,她会看到毫无遮挡的天空、朝霞、险峻的山脉,有些道长会很自然地搬起自己的腿,放在栏杆上压腿——她感受到了久违的生活节律和秩序感。
扫地,也成了她每天投入、专心、视为使命的工作。“扫地能让你知道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故事。”谢九说。
游客没来之前她已经拿起了扫把,因此头一天晚上刮的风,被风刮来缠在树枝上的风筝,野鸟打架后留下的几根羽毛,松鼠留下的粪便,等等,这些发生在昨夜的故事都被她率先得知。重要的是,在井然有序之下,她重获一种有余力关心生活细节的闲暇。
△紫霄宫的鱼,也是自由自在 / 图虫创意
除了信息量显著减少,在工作里常要和人打交道的谢九体察到了另一重“简单”:社交压力简直为零。
这里有更多的空间让她可以用想要的表情生活。
以前她负责一个项目时,脸上要调动丰富的表情以应对各方关系,“社会生活不允许你没有表情啊”。但在道观里,面无表情就是被允许的,想笑的时候可以笑,不想笑的时候不用笑。
△紫霄宫前的道士们 / 图虫创意
这里的道长和义工们不会勉强自己社交,即使冷如冰山也无妨,形成了比较自我的状态。
受此感染,曾经在田野调查里喜欢抓着每个对象问一大堆问题的谢九也减少了好奇心和窥探欲,更专注于自身——对于那个每天到山顶独自练功的外国男人,她一个字也没问过。
“道长们照此生活,
义工们只是短暂经过”
尽管大家每天都一起上早晚课,一起劳动,芋圆坦言:“义工跟道长们的生活始终隔着距离,我只是体验了其中的一部分生活。”
山上忌讳问道长们从哪里来的问题,因此不能进一步了解他们;芋圆看到他们认真上经文课的样子很棒,但因为并不感兴趣,她自己不会去上课,“我只是选择性地接受有关道教的东西,体验到的道观生活是很浅的”。
道长们常常会练琴、练剑、练习如何使用拂尘,晚上的书法课会研究《周易》《道德经》,义工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一起学习。
“但即使我们跟道长们一起聊cosplay,聊微博热点,聊二次元,做差不多的事情,也只是短暂的过客。他们是真心向道,以此为业。”
相对新道徒来说,义工的招募要求并不严格,要的只是对道教文化感兴趣、有闲暇时间的社会人士。因为心向修行,道长们更能从根本上长久地实行这种简单朴素的生活。
在短暂的道观居民角色扮演里,芋圆发现表面上自己和大家的生活节奏趋于一致,可是世界观和圈子完全不同:“我和同住的义工同样都喜欢看一个综艺,我们对这件事的思考方式相似,可为什么她会相信用一个打坐的姿势就能得到身心的升华呢?”
△道观的生活/行李
这座道观的现代化进程里,掺杂着住在这里的人彼此矛盾的生活观,仿佛时空错置,既现代又复古。
作为接待大量游客的风景区,山上电网全通,缆车解放脚力,物资与山下无异。
宫观管委会里的管事道长也会被称为主任、副主任,开微博、豆瓣账号,玩抖音和《王者荣耀》,在App上预订机票飞往新加坡交流道法。在今年的“太和宫小型春晚”上,还有人演唱了《渴望》和《好人一生平安》。
但同时,他们仍然采草药治病,在陋室里节食苦修,用经书或神话解释自然现象,八九点就上床休息,不像城市人那样热衷熬夜。
看到在殿前玩日漫cosplay的年轻人,道长们也会好奇地问道:“他们在拍《霹雳布袋戏》吗?”——那是上世纪80年代播出的一部台湾木偶剧。
△其他道观的一位道士 / 图虫创意
随着上山的人越来越多,来道观体验当义工会不会更普遍?
谢九认为这不会成为一个流行化的选择,“因为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而是取决于道长们。对于这样的机构,是想变成一个尽可能开放交流的场所,还是更看重有限度的传播,可能不是完全取决于公众意愿的”。
上山给她带来的变化是:走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看到落叶她会突然有想扫一扫的冲动。
因为道长们的热心而退过一次回京火车票的行李,目前的身份还是“李小道”。
最近因为常常需要铲雪以及疫情封山期间物资紧缺,“每当一铁锹铲下去,都觉得像奶油蛋糕,越看越饿”。
△“李小道”镜头中像奶油蛋糕的武当雪 / 微博截图
6个月过去,在B站上传的“武当山修仙日常”视频里,面对窗子漏风、房顶漏水的宿舍,他仍会调侃一句,这是风水很好的房间,顺便极为“入戏”地跟关注他的朋友们发一声问候:“祝大家生活愉快,逍遥自在!”
他仍然舍不得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