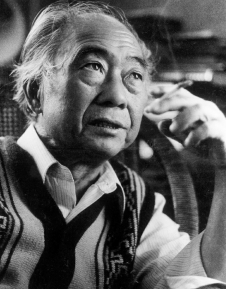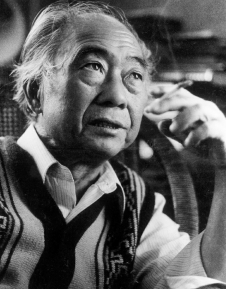
晚年的汪曾祺。 资料图
汪曾祺国画《端午》。 资料图 要是这些梦想都成真了,那他还是一流的文人书画家,他写有一套“有学术价值”的《中国马铃薯图谱》,编选过一册文坛高手云集的美食美文汇编《知味集》,写了一系列有关美国社会现状的文章《美国家书》,完成了一本具有文人视角的学术著作《中国烹饪史》,研究汉代的历史并写成了一部极有现代感的历史长篇小说《汉武帝》 朱航满 前不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汪曾祺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收集了他的全部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戏剧、散文、谈艺、诗歌、杂著、书信,等等,展示了汪曾祺作为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学家的全面才能。 读《全集》,有一个深深的感受,就是其一生的文字,大多处于较高水准,无论是早年的练笔之作,还是晚年的应酬之作,甚至是在一些书画上的题跋,乃至是书信和文书材料,都展示出其充满灵气的文学才华,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极为少见的。当代文学史上,有不少鼎鼎大名的作家,具有文学史价值,但其文学阅读的价值却是大打折扣的,甚至随着时间的流失,越来越小。汪曾祺恰恰相反。 字画皆高妙
在文学的才能之外,汪曾祺最被文人津津乐道的,可能是他在书画方面的造诣。《全集》没有能够征集和编撰出版《书画卷》,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虽然出版社随全集赠送了汪曾祺的一幅作于1984年的花鸟作品复制品,还有一份书法作品的藏书票,也在书前印制了几幅书画代表作品,但不能充分展示汪曾祺在书画方面的才艺。
其实,目前汪曾祺在书画方面的作品,已经有了一些成果,诸如由其子女自行印制的《汪曾祺书画集》,还有故宫出版社编选的《汪曾祺书画》,以及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在纪念汪曾祺去世20周年征集的汪曾祺书画作品集。特别是后者,还与我略有关系。某次与一位作家出版社的朋友聊起汪曾祺,他说正在参与征集和编撰汪先生的书画作品,问我有无藏品。我无缘得藏汪先生的书画作品,倒是知道有位朋友收藏了汪先生一幅书法作品,且经我帮助由汪先生的子女鉴定后得以购藏,最终将其收入此书画集。
汪曾祺的书画作品目前已经成为收藏界热衷的藏品。汪曾祺的书画应该算是文人字画,这个汪曾祺自己也是清楚的,但其在字画的意境、构思和趣味上,却绝对是高妙的,也是一般的书画家所无法具备的。汪曾祺的画作之上,常有题跋,多系绝妙的即兴文字,堪称上好的小品。
1984年3月20日,为翻译家巫宁坤作仙人掌画并题词,如下:“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美。宁坤属画,须有昆明特点,为作此图。一九八四年三月廿日,是日大风,不能出户,曾祺记。”
巫宁坤和汪曾祺是西南联大的同学,巫宁坤时在外文系,汪曾祺则在中文系,都曾师从沈从文。在历经近半个世纪的磨难之后,汪曾祺以这种文人的方式赠答,可谓极具雅兴。赠送巫宁坤的这幅作品,显然属于汪曾祺的书画精品。汪曾祺晚年作了不少书画应酬之作,但也多有灵光乍现的美妙之处。很多文人都把收藏汪曾祺的书画作品作为一种荣幸。
《知味集》背后的美食“朋友圈”
书画之外,汪曾祺还有两个最为鲜明的生活爱好,一个是美食,另一个则是旅游。源于这两个爱好,汪曾祺写过不少的散文,其中主要文章都收录在他后来的散文集《旅食集》之中,这册文集后来又加以增订,以《旅食与文化》为名出版,后者汪曾祺已经写好了序言,但终未能见到其出版。汪曾祺关于美食的文字,都收录在了他的全集之中,可谓洋洋大观了。
令人遗憾的是,汪曾祺生前编选过一册饮食有关的《知味集》,却不见于《全集》。也许按照编者的设想,《全集》只收录汪曾祺的作品,选编的作品则一概不收录。这在《全集》的编选中有先例,但也并不完全如此。
《知味集》由汪曾祺亲自撰写《征稿小启》,可谓广发英雄帖,一时征得文人谈美食文章多篇。1990年此书在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时,汪曾祺又撰写了长篇美文《后记》,对于这本由他独立主编的著作颇为满意,他在开篇中就这样写道:“这本书还是值得看看的。里面的文章,风格各异,有的人书俱老,有的文采翩翩,都可读。”
《知味集》收录了当时文坛作家的谈美食文章48篇,其中除了汪曾祺自己文章《五味》和《萝卜》之外,还包括有李一氓的《征途食事》、王蒙的《吃的5W》、铁凝的《面包祭》、陈建功的《“涮庐”闲话》、高洪波的《吃谈》、王世襄的《鱼我所欲也》、林斤澜的《豆腐》、陆文夫的《吃喝之外》、黄宗江的《美食随笔》、舒婷的《美食天地》、秦牧的《梧州豆浆》、刘绍棠的《打糊饼》、邓友梅的《饮食文化意识流》、苏叔阳的《吃的拉杂谈》、吴祖光的《腐乳·窝头汤》等,真可谓名家云集与名篇荟萃。
这本《知味集》不仅是汪曾祺唯一独立主编的一册著作,展示了他在美食方面的趣味与观念,更为重要的是,这本谈“吃”的文集,也从侧面展示了汪曾祺的文坛交际和独特“朋友圈”。我们无法具体探究当时他是怎样逐一约稿的,可能有些文章会选自公开出版物的谈吃文章,但这种选择一定是具有倾向性的,而更多的应系约稿获取的文章,展示了他当时在文坛交际方面的情况,这应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除了独立编选《知味集》之外,汪曾祺还与邵燕祥一起编选过一册《美国的月亮》,在此《全集》中也未见踪影。
《美国的月亮》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12月出版,收录在冯牧和袁鹰主编的一套“中国作家看世界丛书”之中。在此书的署名上,汪曾祺排名第一。但据汪曾祺自述,此书主要由老友邵燕祥编选。这样的事情,汪曾祺也干过一些,我们不能不分彼此,一概收录,那就成了作品杂烩了。诸如汪曾祺曾任《沈从文全集》的编委,并出席了发布会,但究竟为全集的编选作出了多少具体的事情,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和探究。
无论如何,《美国的月亮》一书的编选,至少说明汪曾祺对于美国这个话题是感兴趣的。汪曾祺曾受华裔作家聂华苓的邀请,去美国中部的爱荷华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项目,回来后他曾就在美国的观感,写过几篇散文,皆可观。而在美国期间,汪曾祺还曾有一个写作计划,就是写一系列的《美国家书》,后来这个系列没有继续。在全集的《书信卷》中,汪曾祺在美国致信妻子施松卿,透露了他回国后将有一个写作《美国家书》的计划。此前,他已经就其将美国的见闻向施写了21封篇幅较长的书信。
未实现的写作计划
以上这些遗憾,对于出版《全集》实际上也算不上什么特别的遗憾,《全集》还是可以再编撰的,具体选还是不选,也是可以继续探讨的。但对于汪曾祺来说,他生前的几个创作计划未能实现,真可谓人间未尽才,这才是真正的遗憾。
此次读《全集》的《书信卷》,发觉汪曾祺除了《美国家书》未能实现以外,还曾有两个写作计划没有实现,一是计划写一本《中国烹饪史》,另一个则是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汉武帝》。如果这两个计划完全实现了,我们对于汪曾祺的评价以及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又会是另外一说。1973年2月1日,汪曾祺曾写信给他的好友朱德熙,谈他对《文物》杂志刊印朱德熙发言的一点意见。其中主要是关于古代人吃食的事情,显示了汪曾祺在这方面的造诣。信末处,他淡淡地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很想在退休之后,搞一本《中国烹饪史》,因为这实在很有意思,而我又还颇有些实践,但这只是一时的浮想耳。”从这封信来看,汪曾祺很可能已经有一些初步的准备和思考了,而他也是此作很好的人选,但最终没能付诸于实际。
长篇小说《汉武帝》未能最终写成,可能是汪曾祺创作生涯中最大的遗憾。汪曾祺为创作这本长篇小说,已经采取了具体行动。从目前披露的信件来看,汪曾祺在1981年到1985年之间,曾计划写作小说《汉武帝》,但最终没有完成。
1981年6月7日在写给好友朱德熙的信件中,他提及打算写一个中篇历史小说《汉武帝》的初稿;1983年9月8日在给陆建华的信中,则计划在1984年动工写作长篇小说《汉武帝》,并说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稿,“他们来要我写长篇,我因写戏故,曾翻阅过有关汉武帝的材料,觉得这是一个性格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人物,我对他很感兴趣,就随意说了一句:‘现实题材的长篇我没有,要写除非写汉武帝。’不想他们当了真,累来催促。这个所谓‘长篇’的希望是很缥缈的。几位师友都劝我别写,说很难写。但我姑且试之。不成,就算了。这样,明年我大概还不能走动,将钻进故纸堆里。”在1983年的一封信中,汪曾祺甚至披露,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将长篇小说《汉武帝》列入了1985年的发稿计划。
最终,汪曾祺的长篇小说计划未能实现。
1984年6月13日在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江达飞的信中,提到他还在为小说做准备,“目前只能翻来覆去地读《汉书》”。 1984年8月16日给陆建华的信中,写到了小说的进展,“《汉武帝》尚未着手。很难。《汉书》《史记》许多词句,看看也就过去了,认起真来,却看不懂。比如,汉武帝的佞臣韩嫣、李延年,‘与上同卧起’,我就不能断定他们是不是和武帝搞同性恋,而这一点在小说里又非写不可。诸如此类,十分麻烦。今年内一定要先搞出有关司马迁的部分,题曰《宫刑》(这“宫刑”就很麻烦,成年人的生殖器怎样割掉的,我就弄不清楚)。”
显然,汪曾祺对于这部小说动了真格,下了功夫。有趣的是,1984年9月,他还给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写过一封求教信,专门请教与宫刑有关的6个很具体的问题,并得到了答复。到了1985年6月5日,他在给宋志强的一封信中写道:“《汉武帝》还未动笔,很难。”此后,就未在见他再提及此事了。经过一番努力,汪曾祺终于放弃了写作长篇小说的梦想。
“很奇怪的作品”
对于汪曾祺来说,还有一个遗憾,也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如果说《中国烹饪史》和长篇小说《汉武帝》的未曾实现是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而他的一本《中国马铃薯图谱》则算是一部真正的佚著了。
在1987年2月6日写成的一篇散文《马铃薯》中,汪曾祺写道:“我曾经画过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这是我一生中的一部很奇怪的作品。图谱原来是打算出版的,因故未能实现。原稿旧存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文化大革命’中毁了,可惜!”
1958年,汪曾祺因被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1960年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一时没有地方可以去,便留在了这个研究所打杂。研究所当时要画一套马铃薯图谱,因为汪曾祺有绘画的功底,也或许因为总要找一些事情来做,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汪曾祺。
在1990年写成的一篇散文《沙岭子》中,汪曾祺又旧事重提,谈到他曾在这个时期还参加过张家口地区的农业展览会的美术工作,画过“许多的动物、植物、水产、农林牧副渔,什么都有”,甚至还颇为自得地写道:“我画过一套颇有学术价值的画册:《中国马铃薯图谱》,另外还画过‘一套口蘑图谱,钢笔画’。”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版《汪曾祺全集》,历经8年的努力,已经是接近完美了。实际上读了《汪曾祺全集》后,才发现在这个全集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不同于以往文人脸谱化的汪曾祺,这恰恰是读全集的好处之一。或许是太喜欢这个作家了,有时在读汪曾祺的全集之后,会颇感一些不足,甚至有些异想天开起来。因为我们试着可以去想想,假如汪曾祺的各种书画作品、编选的文集都编选进来,他的佚著也奇迹般地找了回来,而那些未曾实现的作品也都实现了,或者发现了他尝试写下来还未来得及出版的长篇小说手稿,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要是这些梦想都成真了,那时我们读了《汪曾祺全集》,是否还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汪曾祺:他是不可替代的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诗人、评论家,他还是一流的文人书画家,他写有一套“有学术价值”的《中国马铃薯图谱》,编选过一册文坛高手云集的美食美文汇编《知味集》,写了一系列有关美国社会现状的文章《美国家书》,完成了一本具有文人视角的学术著作《中国烹饪史》,研究汉代的历史并写成了一部极有现代感的历史长篇小说《汉武帝》,如此等等。呵呵,那该是怎样的一个汪曾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