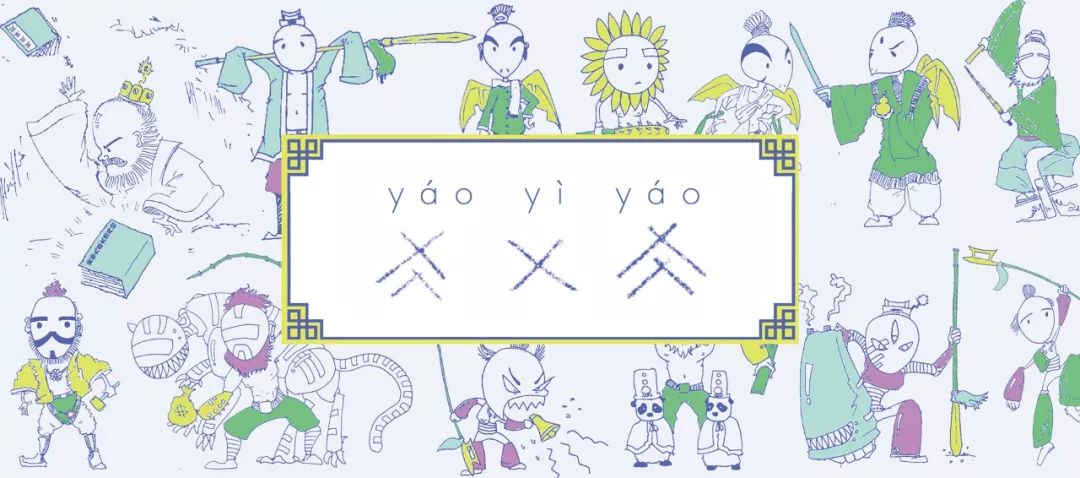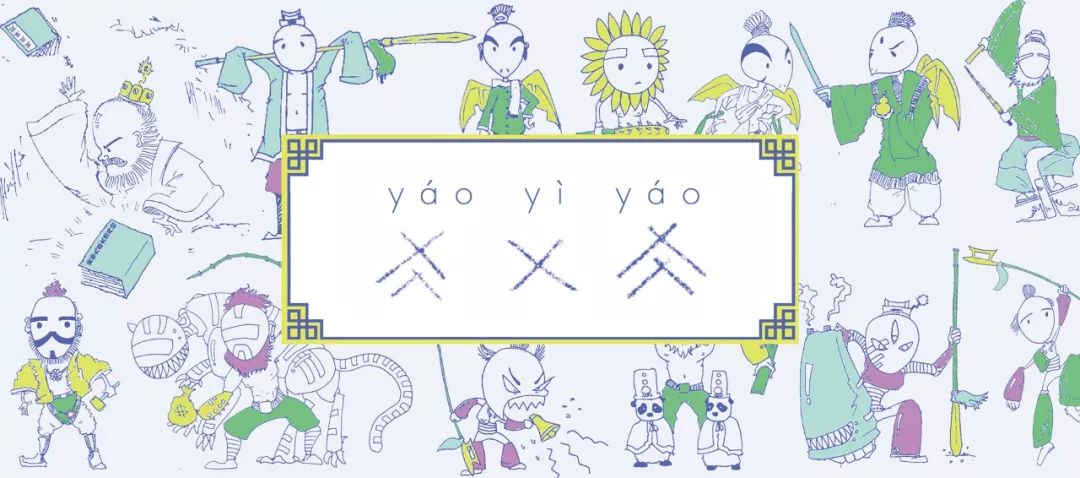
在神仙们过年会怎么发朋友圈?里面,我原本准备了这么一条,结果不小心没挂出来……
除了签名卖书、代言游戏跟永不出现的大电影之外,六学还是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也算证明了自己不是一个莫比乌斯环,比如据说小朋友们感兴趣的:“孙悟空到底有几个妖精女朋友”。
六老师对这种问题给出的答案过于不详细了,所以我们不揣冒昧替他解答一下,不过需要提前声明,即使我们没有答对——虽然可能性非常之低——我们也并不为此向全国人民谢罪。
《西游记》里边,孙悟空倒是不曾如有些影视作品般谈过恋爱,但是若因此就把美猴王视作见了女色一身正气的样板戏人物却也是大错特错了。
悟空从来不是个道学面孔,恰如偷桃盗宝之事做了不少那样,偶尔与异性虚与委蛇一番,也并不介怀。
比如大家都熟悉的“三借芭蕉扇”故事,悟空就变成牛魔王与铁扇公主亲密了一番——虽然书里面说“不敢破荤,只吃几个果子”。
“酒至数巡,罗刹觉有半酣,色情微动,就和孙大圣挨挨擦擦,搭搭拈拈,携着手,俏语温存,并着肩,低声俯就。将一杯酒,你喝一口,我喝一口,却又哺果。大圣假意虚情,相陪相笑,没奈何,也与他相倚相偎。果然是——
钓诗钩,扫愁帚,破除万事无过酒。男儿立节放襟怀,女子忘情开笑口。面赤似夭桃,身摇如嫩柳。絮絮叨叨话语多,捻捻掐掐风情有。时见掠云鬟,又见轮尖手。几番常把脚儿跷,数次每将衣袖抖。粉项自然低,蛮腰渐觉扭。合欢言语不曾丢,酥胸半露松金钮。醉来真个玉山颓,饧眼摩娑几弄丑。”
所以说,就算肉不敢吃,为了取经大业,调戏一下别人老婆也是无可厚非的。
出于种种原因考虑,在《西游记》里面我们看不到更多的此类剧情,但是却不代表类似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第四十二回“第四十二回 大圣殷勤拜南海 观音慈善缚红孩”里面,观音菩萨亲自道破了玄机:
“菩萨坐定道:‘悟空,我这瓶中甘露水浆,比那龙王的私雨不同,能灭那妖精的三昧火。待要与你拿了去,你却拿不动;待要着善财龙女与你同去,你却又不是好心,专一只会骗人。你见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那有工夫又来寻你?你须是留些什么东西作当。’”
如果光是骗个净瓶,显然与“见我这龙女貌美”无关,那么即便是菩萨打趣,也大概说明孙悟空不但可能见色起意,甚至还是个老手。以至于菩萨不能靠念大悲咒防住悟空,还得亲自出马走一遭。
我们都很清楚,通常说的“四大名著”中,除了《红楼梦》之外,都有史书、笔记、话本、戏剧的来源(当然,《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的关系是更复杂的话题,不表)。所以孙悟空的女朋友问题,要到我们最熟悉的《西游记》之外去寻。
在元代就有杂剧版《西游记》,说实话元曲在如今的影响力比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差的太远了,但在古代却远非如此。而这个版本里面,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孙悟空的更多细节。
先看西天取经的孙悟空刚出场时是如何自我介绍的:
“一自开天辟地,两仪便有吾身,曾教三界费精神,四方神道怕,五岳鬼兵嗔,六合乾坤混扰,七冥北斗难分,八方世界有谁尊,九天难捕我,十万总魔君。
小圣弟兄、姊妹五人,大姊骊山老母,二妹巫枝祗圣母,大兄齐天大圣,小圣通天大圣,三弟耍耍三郎。喜时攀藤揽葛,怒时搅海翻江。金鼎国女子我为妻,玉皇殿琼浆咱得饮。我盗了太上老君炼就金丹,九转炼得铜筋铁骨,火眼金睛,鍮石屁眼,摆锡鸡巴。我偷得王母仙桃百颗,仙衣一套,与夫人穿着。今日作庆仙衣会也。”
所以,这个取经的孙悟空是“通天大圣”,“齐天大圣”的弟弟,而从老君处偷金丹、王母处偷蟠桃这个设定,在当年也已经有了。至于“鍮石”跟“摆锡”,其实也就是黄铜以及水银和锡的混合,这位大圣您练得还真是彻底……
图为中山靖王墓出土的铜祖,就不解释了。
此外要注意的是,他还偷了“仙衣一套”,是为了给老婆穿。而他这位夫人也是有来历的:“妾身火轮金鼎国王之女,被通天大圣摄在花果山中紫云罗洞里”。当然,现实中虽然不存在这个国度,我们也不好说这里是不是以“火轮”跟“金鼎”来暗喻修炼。
不过,我们大抵可以说,纵然考证不出妖精女朋友,但孙悟空确实是有老婆的,老婆还是抢来的。
此外,如果做一个更广泛的考察,孙悟空形象的来源虽然存在复杂的争议,但至少难以断言与中国古代南方的猴神信仰无关。
而在传统的笔记故事中,猴类精怪往往与掳掠女子一事联系起来,《喻世明言》第二十卷里面,就曾经记载了猴族“齐天大圣”劫夺他人之妻,被紫阳真人打入酆都天牢问罪的故事。
虽然《西游记》里面不曾用过这个桥段,却也难说是不是将之移花接木给了八戒,又或者是用在黄袍怪跟百花羞公主身上,当然还有紫阳真人那件著名的衣服。据此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观音菩萨对悟空的作风问题那么不放心了……
这些故事也就或明或暗地进入了孙悟空故事的叙事传统之中,虽然今日已经少为人知,但以自己的所知甚少去断言他人的荒谬,本身也就是荒谬的。
文化与艺术形象的变迁或许只需要几十年就能迎来彻底的颠覆,就好像《西游记》原著与相去甚远的86版电视剧或者《大闹天宫》。如果说《西游记》不是什么,那它也显然不是打怪降妖,更不是造反有理。
当然,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身的审美趣味与解释原则,也并非不应为经典和传统的老少咸宜做一些努力。
但与此同时,任何在传播中试图简单化和普遍化的东西,也都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真实,无论传播何种内容。如果忽略了这一点,仅仅拿出粉饰过和扁平化了的所谓美好,与文化和传承又能有多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