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叶刀》曾发表报告称,2007年至2020年,中国不孕发病率从12%上升到18%,每年开展的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周期数超过100万次,每年超过30万例试管婴儿诞生。为了促进生育率的回升,要求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的呼声越来越大。近日,国家医保局提出,逐步将辅助生育技术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澎湃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医学人类学硕士戴媛媛长期致力于研究辅助生殖。北京某生殖中心附近的家庭旅馆是她的主要田野点。在家庭旅馆,她见到了大量从外地来北京“做试管”的女性。同住并参与观察的过程中,她以其人类学视角发现,在主流社会聚焦女性在试管历程中遭受的身心痛苦外,女性在试管之路上还充斥着其他故事,这些故事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女性在现代医学技术凝视下被 “客体化”的刻板叙事。
戴媛媛(第二作者)与其硕士导师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赖立里副教授合作的论文《多重身体 :辅助生殖技术实践的人类学观察》发表于《妇女研究论丛》2022年第6期。
澎湃研究所策划《试管之路》系列文章,理论部分基于上述研究,但更侧重研究背后的个体,更关注异地就医做试管女性的故事,在孤独的就医旅途中,她们如何用自身策略与姐妹情谊在简陋却温馨的小旅馆中追逐生育梦想。专题共四篇,这是第一篇《决定的做出》。
2020年的夏天,丹丹从河北县城的老家到达北京,在一家生殖中心旁的家庭旅馆住了下来,打算做第三代试管婴儿。
“试管婴儿”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英文简称IVF-ET)的俗称,指的是将精子和卵子分别从男女体内取出,在培养皿内受精并培养成早期胚胎,再转移到子宫内,着床并发育成胎儿,直至分娩的技术。“试管婴儿”,连同促排卵、精子和卵子冷冻、代孕等各种衍生技术统称为辅助生殖技术。女性们在日常生活中用“做试管”来指代整个诊疗流程。
根据技术上的细微区别,目前有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试管婴儿,分别适用于不同原因的不孕症。第一代适用于输卵管不通畅、排卵障碍等女性不孕问题,第二代适用于精子活性低、无精症等男性不育问题,第三代适用于男女双方或一方存在遗传性疾病或染色体异常的情况。
与我在家庭旅馆认识的大部分做试管的女性不同,丹丹已经有了一个5岁的女儿。她不但能“自己怀”,而且还是“易孕体质”,女儿就是她自然怀孕所生。但在生女儿前后,她曾流产4次。为了保住肚子里的胎儿,丹丹曾用尽各种办法,比如接连数月躺着不动,静卧保胎;为自己每日注射保胎针剂;甚至初一、十五斋戒,求神拜佛,但对她的复发性流产都无济于事。
流产的原因来自丹丹老公。他的染色体存在异常,13、14号染色体罗氏易位,可致近70%的流产概率,而第三代试管的治疗,能够在胚胎植入前进行遗传学诊断(英文简称PGD),筛选不携带致病基因的胚胎移植。自丹丹24岁第一次怀孕,到检查出流产的真正原因,过去了整整6年。丹丹二十多岁的后半程,用她的话说,“光生孩子了,啥也没干”。
在生育率持续低迷的当下,像丹丹和她老公这样有生育障碍的育龄夫妇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2021年5月,北大三院的乔杰团队在《柳叶刀》发表的报告称,2007年至2020年,全国不孕发病率从12%上升到18%,每年开展的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周期数超过100万次,每年超过30万例试管婴儿诞生。而为了促进生育率的回升,要求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的呼声越来越大。一些省份已将其政策落地,成了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积极信号。近日,针对建议将不孕不育治疗纳入免费医疗的提案,国家医保局给出答复,逐步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但对患有不孕不育的夫妇,尤其是不孕女性来说,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减轻经济负担只是第一步。
将污名化为斗志
我曾问丹丹,不孕不育的问题出在老公身上,但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她在背负这份罪责,会不会感到委屈和不公,老公又是否表达过愧疚?丹丹的回答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她说,在检查出老公染色体有问题后,老公的自尊心很受挫,他对医学检查表示怀疑,他觉得自己“那方面”没什么问题,而且他们已经生出了一个健康的孩子。所以他不甘心就这样做试管,想“再试一次”。
他们再试了一次。这次,丹丹又怀孕了,也又流产了。为了维护老公脆弱的自尊,丹丹又一次遭受了流产的刮宫之苦。
丹丹老公说的“那方面”指的是性能力。在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中,男性不育常与阳痿和阉割的想象联系在一起,当男性不育,妻子往往帮忙隐瞒。而当不孕方是女性时,有研究表明,女性更容易遭受来自亲密伴侣的暴力。新闻曾报道,2020年11月,山东德州曾发生过女子因不孕而被婆家虐待致死。
除了直接的暴力外,更多不孕女性受到的是来自社会的多重且隐性的污名攻击。有对其女性身份的贬低,没有孩子的女人往往被认为是失败的,母职的缺失被看作是女性身份的不完整;或是婚姻关系的威胁,古语有“无子三年,去妻”;更有人格上的污名,例如一些地方用“不下蛋的母鸡”称呼不孕女性,甚至会指责女性不孕是因为“生活作风不检点”“打胎太多”,或是做了坏事“遭到报应”。
有些不孕女性在遭受污名后激发出了做试管的斗志。来自河南农村的阿颖已经经历过一次试管失败,她怀着背水一战的决心再次来做试管,因为试管的成败事关她做人的尊严。她说:“成了,回去就是皇后。不成,回去就是奴隶”。她公公曾不止一次说过:“你要是有个孩子,我们全家跪着伺候你”。阿颖做试管的姿态,像个忍辱负重的巾帼女将。
女性将不孕的污名转化为做试管的斗志背后,是整个社会文化在加强不平等的生殖性别分工,甚至医疗程序设置和学术研究亦在其中参与。
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嘉苓曾对台湾的生育历史进行考察,她发现台湾早期的门诊不孕检查流程“穷尽女而后男”, 将不孕门诊设于妇产科,将男性检查报告列于女性病历之下,强化了生殖“重女轻男”的性别分工。即便现在科室设置已经有变,但依旧是女性承担着主要的生殖劳动,生殖的性别分工依然不平等。
同样地,在学术研究上,关于辅助生殖技术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女性的身体。而对男性生殖角色关注的欠缺,令男性在生殖领域,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二性”。在性别范畴,涉及男性的研究也多局限在“男性气质”这个概念框架下。对于男性不育研究的遗漏,使得性别概念过于窄化。
一个生殖与性紧密联系的文化创造了一个语境,即男性害怕承认自己的不育,而女性也通常会秘密地掩盖丈夫的不育,这被认为是身为妻子的责任。虽然男性不育也会遭到侮辱,但不同于女性的是,他们会得到保护,免于公众的嘲笑。古老的文化创造出对男性不育的掩盖语境,而这种语境也不断延续并强化着古老的父权文化,即女性的身体才是不育的场所。
选择治疗,为何是试管?
不孕不育存在着一个医疗化(medicalization)的历史过程。不同于其他疾病,“不孕症”一般不会有明显的身体疼痛或给正常生活造成障碍,“非自愿无子”(involuntary childlessness)是对不孕症去医疗化的表述。在许多国家,收养和过继都是“非自愿无子”伴侣实现生育权的制度方案。辅助生殖技术诞生之后,不孕不育可以通过医疗而非社会性的手段去解决,让人们对生物性血亲,也就是俗称的血缘关系的追求得以强化。
如若采用医疗手段解决“非自愿无子”的问题,目前的主要治疗路径有三种:常规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及辅助生殖技术治疗。
常规药物治疗适用于患病情况较为轻微,男女双方都没有发现器质性异常的夫妇,主要采取促排卵药物治疗和中药调理。手术治疗适用于男女单方或双方出现器质性异常,如男方精索静脉曲张,或者女方宫腔粘连等问题。而对于药物及手术治疗均无法解决的不孕不育问题,辅助生殖技术治疗被认为是其最终手段。国家卫健委的资料和国际辅助生殖权威杂志《生殖生物学与内分泌学》(Reproductive Biology and Endocrinology)均指出,有超过20%的不孕夫妻,必须借助辅助生殖技术才能解决生育问题。
在讲述不孕不育治疗经历时,女性常常将做试管之前的其他治疗视为“走了很多弯路”,但其实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仅在40%左右。所以,为什么试管婴儿技术被认为是“最有效”或“最终”的治疗手段?
来自陕西农村的月月一侧输卵管堵塞,另一侧有积水,在做试管前曾喝过一年中药。在她的讲述中,喝中药是比做试管痛苦百倍的事。药方里面有蝎子、蛇、还有土王八,她熬药的时候都不敢看。而且中药采用的口服方式往往让人能够直观感受到药物令人不悦的苦味,她说:“吃饭喝水都是药味,吃饭都想吐,感觉自己要中毒了”。这样的视觉和味觉冲击加重了她对药物的身体感受,当没有成效之时,就会产生更大的挫败感。
相比之下,现代医学成像技术让细微的人体细胞也变得可见,且有量化的数据检验和显示结果,及时评估成效,大大提升了医疗科技的权威形象。辅助生殖技术根据生理周期精细化安排的就诊流程,也让做试管的女性产生了在一步一步往前推进、“距离成功又近了一步”的感受。即便移植后的胚胎没有着床,她们也不会觉得一切努力付诸东流。这种随医疗过程推进的步骤与感受,被她们用语言形象化,并成为加固成功的信念:已经配成的胚胎被描述为“孩子”,去医院移植胚胎叫“接娃回家”,再次开始一次试管周期的感受是“已经有一个东西在那儿了”,而不是“从零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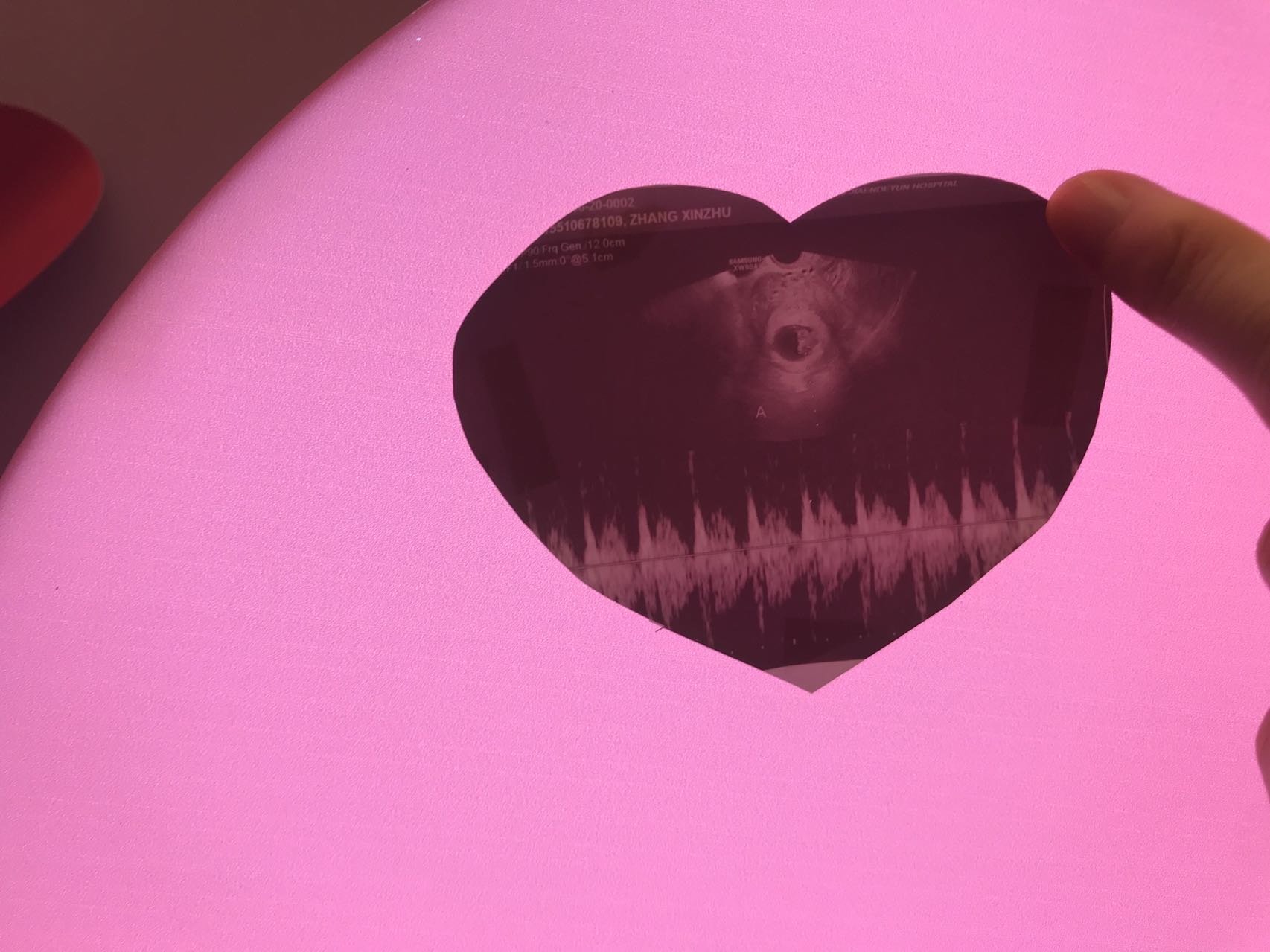
某私立生殖中心心愿墙上B超胎心图。澎湃研究所研究员 戴媛媛 摄
但是,辅助生殖技术也遭受了很多批评,其中之一便是加剧了性别不平等。美国人类学家玛西亚·英霍恩(Marcia Inhorn)通过她在埃及的民族志研究发现,第二代试管通过显微镜将“虚弱无力”的精子直接注射到卵母细胞内,以治疗男性不育,这个技术被很多文化认为是对男性阳刚之气的修复。一些年长男性可以通过二代试管提高生育力,而女性的生育能力对年龄高度敏感,所以就给了一些老年男性堂而皇之与妻子离婚的理由。在生育时间的框架下,性别不平等的状况拉大了。
总而言之,辅助生殖技术是性别化的技术,无论是第一代、第二代或是第三代试管,最终都是女性在承担大部分的治疗流程,女性付出的时间、精力和情绪成本,女性所实施的身体劳作,都远远多于男性。
做试管的钱谁来出?
辅助生殖技术费用高昂。目前在国内,每个试管婴儿周期的价格多在3万-4万元之间,同时,很多人并不能一次成功,需要两次或以上的治疗次数,费用加起来可能超过10万元。此外,对于异地就医的家庭而言,往返两地的交通费、食宿费用等也是相当大的一笔花费,不少家庭因为花费太高而不得不放弃。
我曾听闻一位来自甘肃首次试管失败的女孩在离开前说“等攒够了钱再来”。在我做辅助生殖研究的几年来,也见证过一对山西果农夫妇每年中秋节前后,拿着卖苹果的钱来做试管。我曾问一个旅馆老板,一年中的旺季是什么时候时,她说“收完麦子之后”。这古老的生产节律与当代前沿科技周期的暗合,让我产生了“压缩的现代性”之感。
高昂的试管费用,让钱由谁出,成为了做试管决定的一个重要环节。阿颖穿着一双有些挤脚的鞋子,在医院和旅馆之间来回奔波,脚被磨出了水泡。我陪她去附近商场买鞋子,看到价格之后,她放弃了。她告诉我,因为不孕的原因在她身上,这次做试管的钱需要她自己承担。
阿颖一侧输卵管堵塞,另一侧通而不畅,“有很多弯弯绕绕”。第一次试管失败后,她的婆家便不肯出钱再给她做试管,而为了看不孕多年没有固定工作的她没有足够的积蓄,只好求助娘家。阿颖卡里用来做试管的三万块钱是她父亲在工地受伤所得的工伤赔偿,父亲腿上打着石膏,现在还躺在家里养伤。
阿颖绝非个案,已有研究显示,不孕女性的经济状况往往会因不孕受到损害。当然,更多的案例还是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试管费用,但这“共同承担”中,辅助生殖技术在男性和女性身上不同的实施方式,加强了生产和再生产的性别分工。我在田野调查时经常看到的,往往是女性一人奔波在求子的路上,她们动辄在家庭旅馆住上一个月,很多人为了做试管辞掉了工作。按照她们的解释,缺席了的丈夫留在老家负责赚钱,如果丈夫也来陪同做试管,那么就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了。
女性通常也会用“男女身体构造不同”来合理化不平等的性别分工,以宽慰自己。然而,正如波伏娃那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生殖也并非天然存在这样的性别分工,生殖从来都是一个社会事项,只有打破生殖与身体生物性的因果链条,对生殖的社会想象力才能被重新打开。
结语
在众多中国家庭的试管之路上,做出试管治疗的决定是第一步,而做决定的过程,并非普通的“有病就医”那么简单。可以说,做试管并非是一个决定,而往往是女性对自己的身份和身体下的一个决心,甚至会昂扬起斗志。但其背后,折射的是不孕女性易遭受社会污名的文化语境,和文化上将女性视为生殖责任的主体的偏见。
这种性别意识也贯穿了做试管决定的整个过程。当女性要承担大部分的不孕治疗过程时,治疗焦虑也集中在了女性身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不孕女性对试管婴儿的青睐,做试管的步骤明确,步步伴随着回应,常常带给女性在辅助生殖过程中阶段性的安慰。最后,试管高昂的费用,令谁出钱成为又一个性别分工的场域,就像一些女性会因为不孕的原因在己而负担试管的治疗费用。
最后,我们仍应反思,当走在做试管漫漫长路上的女性,又一次被置身于无论是社会还是科研的聚光灯下,这是否再次严重阻碍了我们对男性生殖角色和责任的理解?关注女性在生殖过程中性别分工的同时,强调这些流程中男性的参与,以及生殖与男性的关联,也许这个决定的做出就不会那么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