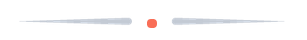编者按:《中国艺术》(Chinese Art)是西方早期研究中国艺术的重要文献,1958年在纽约出版,上下两卷。作者William Willetts(魏礼泽)(汉学家、西方艺术史家)从中国的地理特色着手,系统梳理了玉器、青铜器、漆器、丝绸、雕塑、陶瓷、绘画、书法、建筑等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他坚持客观描述作品的方法,“并不对所讨论器物给予美学价值论断,而是让器物自己说话”。
“让器物自己说话”,与观复博物馆“以物证史”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我们选择翻译此书的原因。此次我们邀请到美国CCR(Chinese Cultural Relics《文物》英文版)翻译大奖获得者对此书进行正式专业的翻译,译者也是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国际索引数据库)和AATA(国际艺术品保护文献摘要)收录的美国出版期刊Chinese CulturalRelics的翻译团队成员。
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此次翻译将存疑处一一译出,其后附有译者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本书,在绚烂璀璨的器物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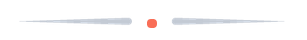
图60的石碑特别有趣。菩提双树矗立,构成了这个大型光晕的边界,拱顶向上,构成繁复的花叶纹顶盖。背景之中,嵌着飞天手持珠宝花环的形象。
图60
释迦牟尼和多宝如来的塔通常由yaksa拿着,装饰以花彩,构成这一设计的全部。光线穿过不规则且大小不一的孔洞,照在主要的坐像人物或站像人物上,人物位于树下。这一场景具有一种生动的戏剧化特质;人物像在舞台上一样,给人以真实感,这是三维空间带来的第二期最伟大的感受。
第三期
到了第二期末尾,中国雕塑已几乎完全摆脱了笈多艺术的风格。图30的阿弥托佛巨型雕像已经与同期的印度作品完全不一样,虽然前者直接继承于笈多艺术模型,比如图59的北齐佛像。第三期对印度标准风格的拒斥开始了。这一复兴与唐代的开始并非同时。而是7世纪70-80年代萌芽的,兴盛了将近100年。到了世纪末,创造的洪流开始消散。并没有新的风格或主题的介入;模仿变得笨拙,工艺也变粗糙。我们就此结束对7世纪末期的中国雕塑的讨论。
有几个纪年时间可以帮助我们定位中国本土取得的成就。铭文消失后的数十年,一件铭文纪年为641年的著名石碑记录了一些龙门古老洞窟的修复和翻新。645年,玄奘回到中国,带来了7座笈多图像。3年后,随之而来的是Wang Hsuan-tze这位皇帝特使,这是访问笈多宫廷的四次中的最后一次,并带来了菩提迦耶的著名弥勒佛像的副本。龙门石窟最大洞窟和最伟大的塑像就是阿弥托佛像,开凿于672-675年。造像活动在武则天时期达到了高峰(684-705年),这时长安的Kuang-chai寺建造了重要的Chi-pao花园。原属于这座建筑的残迹现在有些保留了下来,对于风格相近的其他物件的断代提供了宝贵线索。
这一时期对于人形的兴趣前所未见。中国雕塑这一时期似乎暂时地或者完全地屈从于笈多成熟风格的诱惑。晚期笈多图像保存下来的不多,但留存下来的一些雕塑残件和石刻寺庙的壁画残片已经足以说明当时(6-7世纪)这些作品对于外国工匠的吸引力和带来的惊叹有多么大。唐代的雕塑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第二期已经发端的趋势,对开脸的自然写实处理,衣服处理成刻线花饰,像打湿的褶皱边紧贴于裸体之上,圆雕人物似乎有动态。
往期文章链接:
处女翻译·432《中国艺术》(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