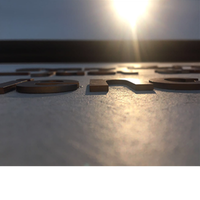今天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数据,考古学家发掘唐代东都洛阳宫城的崇庆门遗址,发现两条平行车辙,辙距约为1.4米,在崇庆门相对的宣政门,发现的辙距约为1.2米,而此前在洛阳永通门,还找到过辙距为1.25米的轨迹。
这么一算起来,当时马车车厢的空间并不是很大,即便是轮距1.4米的马车,比起今天的A级车还会要窄一些,至于轮距1.2米的马车就更小了,也就够一个人舒舒服服地坐在里头,多添个人都嫌挤。
皇帝当然可以坐很大的“辂(lù)车”,唐代皇家工匠的造车水平极高,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大驾玉辂,唐高宗时造,至今进御。自唐至今,凡三至泰山登封,其他巡幸,莫记其数,至今完壮,乘之安若山岳,以措杯水其上而不摇。庆历中,尝别造玉辂,极天下良工为之,乘之动摇不安,竞废不用。元丰中,复造一辂,尤极工巧,未经进御,方陈于大庭,车屋适坏,遂压而碎,只用唐辂。其稳利坚久,历世不能窥其法。世传有神物护之,若行诸辂之后,则隐然有声。
意思是唐高宗时期打造的一号专车,工艺精湛,质量极好,几百年间不停使用都没见坏,宋代的工匠都仿造不出来,于是北宋皇帝出行,都乐意坐这辆老爷车。
有意思的是,古人想到的评估行车舒适度的方法和今人如出一辙,都是倒杯水搁在车身上,看是不是会洒出来。
唐高宗若是知道这事儿,兴许会一脸鄙视,因为他嫌车子又闷又颠,往来出行,能坐轿子的,绝不乘车。估计也是因为他对车辆极端挑剔,才会逼着将作监的大师们造出这样的神作。
至于普通人就没这么舒适了,车和马都是正经的消耗品,细细盘算起来,拉车的马本来就不便宜,配套的车、车身装饰、马料、马厩,乃至马夫、车夫,都是钱,所以能乘车出行的,也只有高级别的官员。韩愈坐着高大的马车去拜访李贺,李贺专门写了一篇《高轩过》,标题里头隐藏的信息,就反映了这种社会等级。低级官员可能以骑马为主,白居易做官之后,养了两匹马,还乐滋滋地写进诗歌里,这种感受和今人买了新车是一样的。
诗人杜甫年轻时候很是逍遥过一阵,因为他父亲是官员,家中财富可以供他骑马到处游乐,公子哥儿杜甫想必不会选择低矮的蒙古马,更有可能骑着体型较大的河曲马,这样才能显身份,何况他是骑马去飞鹰走狗打猎的:
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
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鶬,
在开元盛世中长大的杜甫肯定对马很了解,他写过一篇《沙苑行》:
君不见左辅白沙如白水,缭以周墙百馀里。
龙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称献于此。
苑中騋牝三千匹,丰草青青寒不死。
食之豪健西域无,每岁攻驹冠边鄙。
王有虎臣司苑门,入门天厩皆云屯。
骕骦一骨独当御,春秋二时归至尊。
至尊内外马盈亿,伏枥在坰空大存。
逸群绝足信殊杰,倜傥权奇难具论。
累累塠阜藏奔突,往往坡陀纵超越。
角壮翻同麋鹿游,浮深簸荡鼋鼍窟。
泉出巨鱼长比人,丹砂作尾黄金鳞。
岂知异物同精气,虽未成龙亦有神。
几乎把马夸到天上去了。这种对马的痴迷,也是唐代诗人的一个特点,此前南朝的门阀世家子弟,娇弱不堪,甚至有听到马鸣而惊悸不已的。而往后到了南宋,士人们崇尚坐轿子,对待马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骑马这样的剧烈运动,一般人接受不了,自然也就被排除在诗文之外了。
杜甫在长安做了很多年京漂,后来钱花光了,出行只能骑驴,他写道:
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
平明跨驴出,不知适谁门。
个中滋味,大概和今天人们开个三蹦子上街感觉是差不多的。
南人乘船,北人乘车。杜甫晚年流离南方,从蜀地到湖南,大多时候都是乘船,其实以平稳程度而言,乘船大概是最舒服的,唯一不靠谱的是天气,杜甫最后死于湘江孤舟之上,也许是钟情于骏马的他不曾想象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