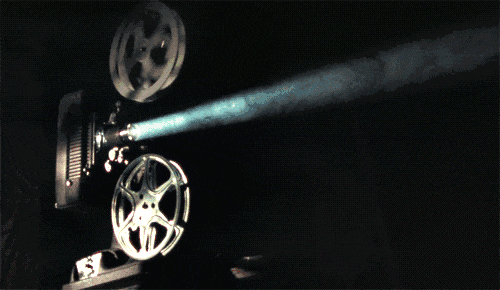在人间诸种愁苦里,或许“寂寞”已是最好最淡的一种。身边无伴,苦,但若身边有伴,说不定更苦。
书.

博尔赫斯《阿莱夫》
(以下这篇是王朔文集2007年版总序(有删减)。王朔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无知而不去冒充有知,在于他承认自己的低俗而不去假装什么崇高。他是一根货真价实的直肠,话说得透,不留一点迂回的余地。这本不是什么值得写上一笔的事儿,但在如今这个浑汤子场里,他显得是这样难能可贵。)
那时我很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欲望很强,以为已知的就是一切了。这些书里的人、情景和一些谈话是那时我经历过的,在生活中也不特别,仅仅因为我不知道更多的东西,才认为有趣,虚张声势地写下来。这些情景不再了,这些人也散了,活着的也未老先衰,我也不再那么说话和如此看待自己,所以有时我觉得自己失去了继续写作的能力。
年轻的时候认为有很多重要的在前面,只要不停地奔走就能看到,走过来了发现重要的都在身后发生了,已经过去了,再往前又是一片空白。对过去,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也没有任何偶然,都是必须经过的,我不信一个人可以有两个以上的选择。
关于文学,我越来越确定这是个人的事。这个世界很单纯,人和人之间需要的其实不多,相互了解只能横生误会。公众是个陷阱,为别人活着即便出自真诚也在技术上做不到。没有比想在别人的记忆中不朽更自欺的。几千年算永恒吗?写作是一条狗,你不变心它就陪着你,也是一面镜,照着你自己,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不是为了几个钱,我是不在乎这几本书印不印的。这些文字当年我写完就没再看过,现在看,像另一个人写的,一个狡猾乐观的小子。我在盲目中写这些小说,用意是引起别人的兴趣,小说文体本来就不老实,动机再是取巧,可见会有多少矫情、吹嘘和虚饰在里面。青年作家总是可疑的,也无非是揭疤、自渎,摆明反抗一切,高调入世,看似特立独行,骨子里却难逃代代相传的文人梦谈。社会很容易被质疑,人群总是显得麻木且腐败,理想就那么清白吗?关于人之为人,我们知道多少?我承认,我的世界观都是因袭来的,在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时就已经被植入,到需要和别人对峙时才发现我们来自同源头。东西方关于人的理想生活又有多大差异呢?也无非是策略之争,由此及彼或由彼及此,当然策略导致结果。问题不在于认同人类共有的自我肯定,问题在于这一切是确凿的吗?我们相信的和我们本来的是一回事吗?世世代代高唱的人类赞歌指的是我们吗?如果是,为什么我总是感到羞愧和一次次堕落而不是心安理得和渐次归位?为什么会有小说这样合法的精妙被推崇的虚构,还有那么多人从中获得安慰。
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我怀疑其核心已编入遗传而不必再通过教育获得了。我觉得自己像在大海里游泳,无边浪涛挥之不尽,什么时候才能登上彼岸,有从树上刚下来的原始人那样一个澄明无邪的头脑。
活下去,活在自我虚构和自我陶醉中,这大概是一个写作者的宿命,明白也没用。
影.
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
王朔曾经说:“我年轻的那个年代,常常是你老老实实的在家里坐着,你一个哥们突然哭着闯进来说被谁给揍了,那你就得二话不说立马撅着屁股满世界找砖头,不管有仇没仇都要去拼命。”我想这种简单粗暴的义气关系已经和那个年代一同流失了。王朔爱调侃的一句话是:“那时候人民内部矛盾都是人民自己解决。”人民自己解决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多的故事可以回忆,那些少年所做的疯狂的事,使他们在成年以后回忆起来都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很多年过去后,他们再也没有勇气去做,他们不再是凶猛的动物,他们已经老了,早已被生活驯化。
如果年轻男孩子的青春故事足够丰盛,那故事里不可缺少的就是一位集妖娆与纯洁于一身的神秘女孩,她的背景深不可测,她的社会关系纷乱复杂,她似乎已经和你成为亲密的伙伴,你以为你对她无所不知,可是有一天你发现她和那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你为她的复杂而感到屈辱,又为她的冷漠感到惊恐,你一直和她很近,终有一天你会知道你对她一无所知,你只是她精彩人生的过客。在这里,她是米兰。
他回忆起当时最有名的女孩,他曾和她很相熟,他们的关系是个秘密,她消失了,而他不肯说。20年的光阴已逝,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只不过,也许这些事太珍贵,他想独自一人回忆好多年。
占据一个人回忆的要塞,是轻易的事儿么?不,你没有那个机缘,是因为你不曾在阳光下,大汗淋漓地以她的身体展开对爱情和性,最初的想象。她夺取了他少年的凶猛,你再好,也只能拥有凶猛过后他软弱的人生。
音.
By The Sea- Eleni Karaindrou
爱有很多种的吧。一种是,你想和他牵着手,在街上、在超市里,走。你们做爱、做饭。你们看电视、给对方夹菜。你们在一起,像头驴子,转啊转,把时间磨成粉末,然后用粉末揉面,做包子、饺子、面条,吃下去,饱了,心满意足。还有一种,就是像我对你这样,远远地,用一点微弱的想象,张望。给这暗下去的岁月,涂一抹口红。这么些年来,我都不知道,我是在用想象维持对你的爱情,还是在用你维持想象的能力。
我想清楚了。想清楚这么些年来,为什么会对你念念不忘。也许就是因为我对一些遥远的东西,有一种偏执的倾心。你看,你离我很远,你总是离我很远。但这不是关键。关键是,你所热爱的那些东西,离世界那么遥远。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休西底斯。这种遥远,这种偏执的遥远,这种与逃避无关而与深入有关的遥远,让我眷恋。你看这世界,杀声震天的,都打成什么样。挣钱的瞧不起读书的,读书的瞧不起挣钱的。爱国愤青瞧不起民主愤青,民主愤青瞧不起爱国愤青。看周星驰长大的瞧不起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长大的,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长大的瞧不起看周星驰长大的。发财的瞧不起下岗的,下岗的诅咒发财的。这历史的死胡同,一路都是被揪掉的头发,踩落的球鞋,和打掉的牙齿。国内国外,都一样。太近了,太近了,他们靠在一起,挤成一团,脸红脖子粗,挤得都变了形。相比之下,你在我心里,就像一个奇迹。你思考,但是转过身去。打动我的,就是这样一个偏执的背影——在这摩肩接踵的世界里,挤累了时,我想知道,这个背影面对的是怎样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否有更多的安宁。
也许,我喜欢你,就是因为你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不可归类的人。唯一不需要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的人。唯一不被流行的情绪传染得感冒了的人。他们恐惧孤独,所以需要一个圈子。但你就在你自己的角落里,远远地,雕刻你自己的时光。而我,就这样远远地眷恋你。我可怜吗?我还觉得我可喜可贺呢。
我是说,从你那里,我学习到了一点信心。对孤独的信心。这一点,真的要感谢你。当然,你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稀罕。但是,在我这里,这很重要。每次,我被挤得失去重心,挤得想骂娘,挤得想脱下高跟鞋去敲“他们”的脸。突然之间,就会闪现出你的背影。远远地,像一声口哨,微渺,却明亮。于是我也想挤出人群。也开始接受,孤独对于人生,是多么灿烂的事。(文/ 刘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