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伦特)
他是一个“劳动模范”,一个模范军人,一个模范公职人员,他是“所有的权力都想把他吸收到自己的群体中去的那种人们梦寐以求的人才。”(《<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229)他——阿道夫•艾希曼,纳粹德国党卫军中校军官,犹太人大屠杀“最终方案”的执行者。

(艾希曼受审)
纳粹覆灭后,艾希曼逃到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获押回受审,旋被判处绞刑。艾希曼暴得大名,完全拜美国犹太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所赐。阿伦特参与报道了以色列法庭对艾希曼的审判,她为这次审判撰写的报告,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世界性的争议和轰动。
通过报道庭审,极大地改变了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根本之恶”的看法。艾希曼这个罪大恶极、穷凶极恶的纳粹分子,“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太正常了,甚至正常得可怕。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绳来看,这种正常比所有残暴加在一起更加可怕,因为它意味着,这类新的罪犯,这些实实在在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是在不知情或非故意的情况下行凶作恶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译林出版社,2017年,页294)从而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争议巨大的概念——“平庸之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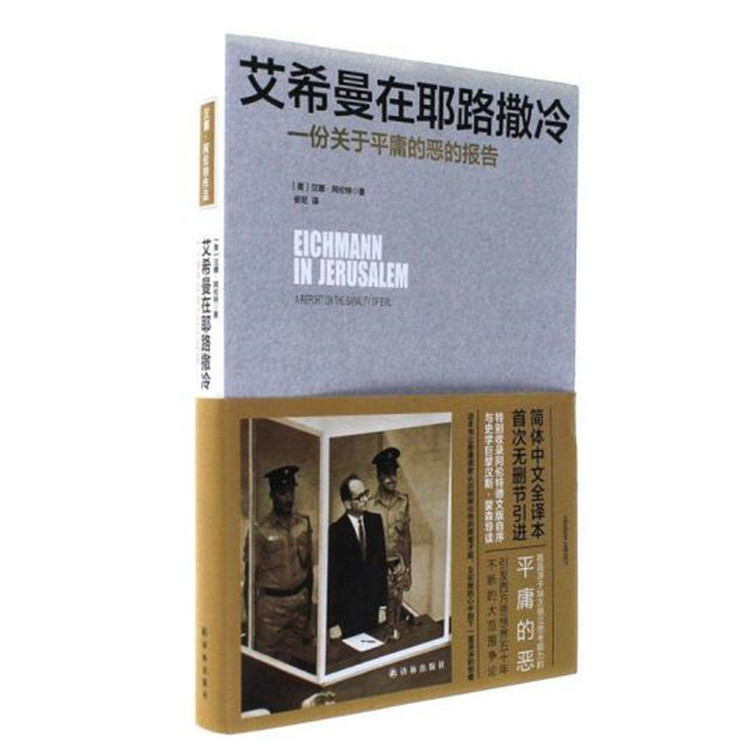
何谓“平庸之恶”?阿伦特指出,“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同上书,页10)她又说,“‘恶’正犹如覆盖在毒菇表面的霉菌那样繁衍,常会使整个世界毁灭。……‘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因为那里什么也没有,带来思考的挫折,这就是‘恶的平庸’。”(《<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页166)阿伦特认为,“平庸之恶”形成于“不思考”(或译“无思想”),而这恰是纳粹主义的体制特征。专制政体强制要求思想的绝对一致与统一,禁止思想的自由与独立,于是才会形成大批的“无脑族”(或称“脑残”)。当“不思考”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状态和精神习惯时,“服从”、“追随”与“一致”就成为一种自觉的社会行为。正如艾希曼所说:“从我的童年开始,服从是某种我在体系中不能摆脱的东西……顺从和服从命令的生活确实是一种非常舒服的生活。以如此的方式生活,确实减少到一个人需要思考的最小值。”对艾希曼来说,服从——省心、省力,轻松而舒服;思考——费心、费力,复杂而危险。于是很自然地选择了“不思考”和“服从”。
“不思考”和“服从”,是极权政体下“平庸之恶”的两个主要特征,二者只是前后关系,并非因果关系,不管怎样,这显然是一种主动的行为选择。
思考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对于极权政体来说,思考是危险的,“思考不可避免地对既定的善恶标准、价值和尺度,……对我们在道德和伦理方面遇到的风俗习惯和行为准则有种破坏和颠覆作用。”(《精神生活:思维》,阿伦特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页196)任何既定的公理、教条、准则、定论,是否永远正确,永恒不变,都要经过思考的过滤,“思想之风是一种能横扫人们得以指导自己行为的一切既定准则,使城邦陷入无序状态和迷惑公民的飓风。”(同上书,页199)真理不怕检验,公理不怕质疑。只有谬误与罪恶才会害怕论证与思考。正因如此,纳粹主义才会禁止和消灭一切思考,一切行为以元首的思想为标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行动,而这一切都要剥夺思考的权利。在这样的氛围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没有存在空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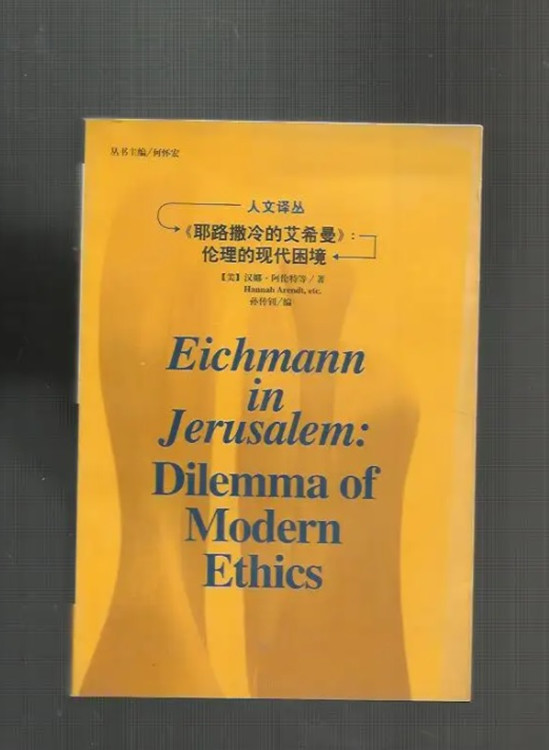
纳粹政权需要的是不会思考、绝对服从的工具,艾希曼就是典型例证。这个“见到尸体和血要作呕”,“只喜欢文件和统计一类的办公室的事务工作”的纳粹分子,似乎与大屠杀无缘,然而,他却是“杀人工厂的工程师”。(《<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页229)一部名为《专家》的纪录片,也对艾希曼的心理与行为进行了揭示。表面看,艾希曼“没有思想,只是‘上司手中的驯服工具’,那个队伍中的‘沧海一粟’”,不过,他却是一个“办公室罪犯”。(同上书,页230)艾希曼作为一个能力超强的行政干部,有其引以为傲的工作业绩,他把驱逐、转运、屠杀犹太人的各个环节,“简化成一条龙”,创造了“高效率”,实现了“史无前例的革新”,成就了“自豪不已的业绩”。甚至为执行纳粹“在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的命令,他从未犹豫与迟疑,他只“知道必须完成这件任务……,顺顺当当完成是首要的。……不能有悖于当年的对领袖绝对忠诚、服从誓言。”(同上书,页233)“在这种‘每个人都无思地臣服于相信别人所说的和相信的一切’的情况下,他们已经准备好和其他人一样的是——包括谋杀,甚至大屠杀。”(《阿伦特为什么重要》,译林出版社,2009年,页131)
“不思考”是精神活动,“服从”是社会行为。阿伦特指出,“对权威的服从,在很长历史时期内是被作为美德被人们所赞赏。但是为了邪恶的目的,被驱使去服从的行为必须重新评价。”(《<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页191)在行政体系内,服从是美德,但服从于恶政则是罪恶。在纳粹统治下,“与犯下背叛罪的犯罪相比,更多的人是因为服从犯下了罪行。”(同上书,页190)在几乎所有的恶政之下,人们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制服”出现在街头,控制着公共空间。他们身穿制服,即意味着他们手握公共权力。一般说来,服从于良政,他们是在维护公共秩序;服从于恶政,他们却在侵犯公民权利。面对民众抱怨,他们往往强调“奉命行事”,他们也是“身不由己”。鲍曼揭穿了这一事实,“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于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挑战的秩序的统治。它并非一群肆无忌惮、不受管束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披制服、循规蹈矩、惟命是从,并对指令的精神和用语细致有加的人所为,……”(《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02年,页199)然而,“不思考”并不是绝对的,他对于命令的对错、善恶“不思考”,但对如何执行命令、完成任务却殚精竭虑。换句话说,他对纳粹命令是否正义“不思考”,但却对如何实施屠杀想方设法。

“奉命行事”也是“服从”。即使在纳粹治下,“奉命行事”也是个人进退自如的选择。作为“行事”的主体,进则可以“奉命”为令箭;退则可以“奉命”以卸责。“奉命”之“命”有对错、善恶之分;“行事”之“事”也有对错、善恶之别。所“奉”之“命”、所“行”之“事”,都是对的、善的,自然没问题,而这正是“服从”的应有之义。所“奉”之“命”是对的、善的,所“行”之“事”却是错的、恶的,此之谓好经歪念。所“奉”之“命”、所“行”之“事”都是错的、恶的,那么,“行事”者并不能因此而免责。审判中,艾希曼出于求生本能,就把他的全部罪行解释为“奉命行事”,“臣服于一个好的政府是幸运,臣服于一个坏的政府是不幸。我运气不好。”他强调“自己只是齿轮系统中的一只,只是起了传动作用罢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页231)。对此说法,人们耳熟能详,这与“螺丝钉”的比喻很相像。然而,在罪恶的杀人机器上,每只齿轮、每颗螺丝钉都不是无辜的。在纳粹的国家机器上,“没有艾希曼这种人物的话,也没有其他忠诚的纳粹支持者及盲目执行命令的人,那么,希特勒、希姆莱和戈倍尔那样的猛兽会变得软弱无力,最终放下武器,他们会不过只是像不吉利的扫帚星一样掠过欧洲上空。”(同上)
纳粹政权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举起屠刀、扣动扳机、施放毒气的并不是希特勒本人,纳粹杀人机器正是由大量艾希曼这样的“齿轮”构成的,这种邪恶制度“把人变成官吏,变成行政体制中间的一只单纯齿轮,这种变化叫做非人类化,……”(同上书,页56)而这种“‘齿轮’理论在法律上来看是没有意义的。从而,把艾希曼这只齿轮放到无论什么地位都没有关系。……犯罪是审判的前提,哪怕是微小的罪行——机器上的任何一只齿轮,也不管被押上法庭与否,都要还原成人。”(同上)在战后,一些为纳粹效力的罪犯试图以“奉命行事”而脱罪,是根本行不通的。正如阿伦特所说,“在政治中,服从等于支持。”(同上书,页47)任何“奉命行事”的借口,任何“齿轮”的托词,都无法开脱自己的罪责。“奉命行事”作为脱罪的遁词,意在将其“行事”的责任与后果推给命令下达者。命令下达者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各类“组织”。他自辩称,他是“奉命行事”,不是个人行为,不是擅自行动,而是作为组织成员的“集体”的行为。针对艾希曼这一辩词,阿伦特写道:“即使他作为使人相信不过是作为组织中的一只齿轮的角色站在法庭上时,他仍是作为个人的人格出现的,要根据他所做的事加以制裁的。”(同上书,页144)
“平庸之恶”既有制度原因,也有个人原因。但是,法庭不会把制度作为审判对象,它会从罪行中析出具体的犯罪个人。在纳粹政体之下,面对强大的国家暴力与意识形态,每个人都有选择的问题,拒绝邪恶、明哲保身、同流合污,是三种不同的选择。就现实和人性而言,第一种是极高的要求,只有极少数勇者与智者才会作此选择,对大多数人并不现实。第二种虽然不具有正面意义与积极价值,作为人性的审时度势、趋利避害,似乎不应受到道德的苛责。第三种当然不是多数人的选择,但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现以“奉命行事”为托词,或被动同流合污,或主动助纣为虐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