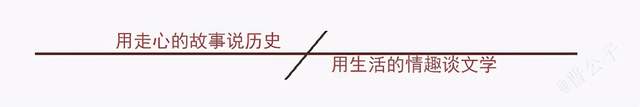
本期话题
《日月》是《诗经·邶风》中的一篇。它的作者究竟是谁,自古以来引发了学者们持续不断的讨论。而一旦我们找到答案,就会发现,这首小诗很可能是一个深陷政变动荡之中的国君夫人对国破家亡的历史的记录。
“其实,我查案真的好差啊,又没什么侦探头脑。所以我很羡慕那些师兄,用脑子琢磨琢磨,就破了案了。庄SIR,你好厉害,你是盲人嘛,看不见东西都这么厉害,我真的很佩服你。我私底下称呼你作‘破案之神’……”
几年前第一次看这部《盲探》的时候,菜鸟警员何家彤仰视庄SIR的模样曾让我十分感慨——可能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过类似的体验。
总有那么一些事儿,让我们感觉不可捉摸,手足无措,可它一旦落到别人手里,却迎刃而解,不费吹灰之力。于是乎,我们开始自我怀疑,怀疑自己是不是天资鲁钝;紧接着,我们开始了偶像崇拜,把别人“造成”了自己心目中的神。
我最初读《诗经》的时候,也为自己造了一批神:郑玄、朱熹象是神,闻一多、陈子展也象是神。因为他们跟庄SIR一样,总能从那一首首意旨含混的歌诗中嗅到隐秘的气息,并追踪这些蛛丝马迹,挖掘出歌诗背后的故事来。
比如《邶风》里的这首《日月》:
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胡能有定?宁不我顾。
日居月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宁不我报。
日居月诸,出自东方。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诸,东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报我不述。
——《诗·邶风·日月》
孟子曾说,“颂其诗,读起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我们要读懂一首诗,往往得有这么两个先决条件:这是谁写的诗?是他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诗?前一问是孟子说的“知人”,后一问是孟子说的“论世”。
就说这首《日月》吧,诗中的“我”是谁呢?他又因为什么事儿,要写这首诗呢?
以郑玄、朱熹为代表的古代学者们说,“我”是春秋时期卫国国君卫庄公的夫人庄姜。庄公死后,庄姜的养子卫桓公遭遇流亡公子州吁发动的政变,不幸罹难。国破家亡的庄姜悲愤之余,感而成诗,于是便有了《日月》。
可现代学者们普遍不相信这个故事,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日月》中的“我”是一个婚姻不幸的女子,她之所以要写这首诗,是为了抱怨丈夫对她的遗弃。
在我初读《诗经》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弄不明白,像郑玄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找到上面这些答案的呢——偶像崇拜有时候就是这样产生的。不是人家真的像神一样先知先觉,烛照万物,只是那个探索答案的方法我们还不知道。一旦我们自己窥入了门墻,才发现,“哦——,原来不过是这样的。”
“破案之神”庄SIR说:
“其实我查案,只是投入到案中人的处境,然后瞎猜。”
想象自己从案件的旁观者变成了当事人,“假如我是他的话,当时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做”。先复原出一个案发的场景,然后用勘察案情所找到的证据与它质证,逐渐修订场景中某些不合理的推断,一个真实的案情便会渐渐浮出水面。
找寻《日月》中的那个“我”,学者们其实也是靠猜的。甚至读诗的猜测比破案还要来得更便当。
因为《诗经》中的许多篇目都像《日月》这样,它本身既没有透露主人翁的身份信息,而在别的历史文献中,我们也找不到相关的旁证。于是在读诗的猜测中,我们甚至连质证的步骤都可以省略了。
只要将我们假定的主人翁的身份代入诗歌的文本,没有明显的违和与矛盾,那这个关于主人翁的猜测就能成立,聊备一家之说。
再说回到《日月》。虽然我们不能通过质证的办法去判断对主人翁身份的猜测,哪一个更真实,但我们仍可以通过对文本解释技术的比较去判断,哪一个猜测更合理。
假如我们将《日月》中的“我”设定为一个弃妇的话,诗歌的首章译作白话该是这样的:
日居月诸——太阳和月亮,
照临下土——光辉照地头。
乃如之人兮——竟有这种人,
逝不古处——不可再相守。
胡能有定——暴虐怎能止?
宁不我顾——竟不把我瞅。
——《先秦诗鉴赏辞典》
朱杰人、龙向洋二位先生翻译的这一段,从解释技术上说有一个明显的弱点:他们把“胡能有定”一句译作“暴虐怎能止”,这是添字为释。诗歌的原文只讲到“有定”,并没有说“定”的主语是“暴虐”。可是对主张《日月》为弃妇诗的学者们来说,“暴虐”两个字又是少不得的。
因为在这派学者还原的剧情中,丈夫暴虐不止乃是造成夫妇离异的主要原因。一旦拿掉了“暴虐”,弃妇诗的观点就将失去最核心的支撑。理解诗歌的最关键的信息不出自诗歌的文本而出自于解释者的主观想象,这不能不令人质疑,以《日月》为弃妇诗的合理性。
和弃妇诗的猜测相比起来,我还是更愿意把《日月》中的“我”看作庄姜。只是要做这种猜测,我们不得不对郑玄笺注的几处诗文做一点局部修正,否则诗意难以首尾贯通。《日月》开篇说:
日居月诸,照临下土。
郑玄解释这两句诗道:
日月,喻国君与夫人也。
我始终认为,郑玄的解释稍嫌有些胶柱鼓瑟了。假设诗中的“我”是庄姜,她为什么一开篇先说日月?原因恐怕是这样的:
“照临下土”之后的两句即“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庄姜所感叹者,该是卫庄公的谢世,翻译过来,也就是那个人溘然长逝,已经不在他熟悉的位置上了。
用日月的永恒来反衬生命的短暂,是悼亡诗中常见的修辞手法,比如沈约《悼亡诗》说:
去秋三五月,今秋还照梁。
今春兰蕙草。来春复吐芳。
悲哉人道异,一谢永销亡。
——沈约《悼亡诗》
庄姜在诗歌的一开篇先赋日月,意思是说,日月还像从前一样照临着卫国的土地,可是从前君临卫国的庄公却已长眠地下,不复在位。正是因为国家失去了这根主心骨,卫桓公和州吁才闹出了手足相残的惨剧,以致社稷动荡,生灵涂炭。
这样突如其来的灾难又引发了庄姜进一步地感叹,她说“胡能有定?宁不我顾”——“安定的局面何时才能到来?你(指去世的卫庄公)怎么就撇下我不管了呢?”这两句话,恐怕该被视作是深陷动荡之中的庄姜,对亡夫呼喊的心声吧。
首章经过这样串讲,该是说得通的。只是这又带出了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假如庄姜会在苦难中情不自禁地呼告庄公,那意味着她和庄公从前的夫妻感情应该很好。可郑玄却不这么看。
诗歌的次章写道“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郑玄解释说:
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相好之恩情,甚于己薄也。
按照郑玄的判断,早在卫庄公去世之前,庄姜就因为他的移情别恋而被冷落。彼时的庄公,一门心思都放在自己的爱妾,也就是公子州吁的母亲身上。
换句话说,郑玄将这句“逝不相好”解释作“他不再像从前那样对我好”。这是不是事实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史记》的相关记载:
庄公五年,取齐女为夫人,好而无子。又取陈女为夫人,生子蚤死。陈女女弟亦幸于庄公而生子完。完母死,庄公令夫人齐女子之,立为太子。
庄公有宠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长,好兵,庄公使将。石碏谏庄公曰:“庶子好兵,使将,乱自此起。”不听。二十三年,庄公卒,太子完立,是为桓公。
——《史记·卫康叔世家》
作为卫国的第一夫人,庄姜拥有高贵的血统和绝世的美貌。《诗经·硕人》一篇曾这样称赞她:
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诗·卫风·硕人》
如果说这位身份贵重、姿色绝人的卫国国母有什么能让人挑剔的地方,那就是她嫁给卫庄公之后,迟迟没有诞下元子。庄公后来不断临幸别的女人,这是事实;公子州吁的母亲因此成了卫庄公的宠妾,这也是事实。但这些事实都不足以证明卫庄公和庄姜的感情出现了裂痕。
因为无论卫庄公和庄姜的感情有多么好,他也不能因此绝了嗣,卫国更不能因此没了接班人。
按照那个时代的妇德,艰于诞育的庄姜不但不能阻止丈夫纳妾,反而应该积极促成庄公纳妾生子,这才能赢得社会舆论的谅解,否则她将成为史官笔下一个丑恶的妒妇。
根据太史公的记载,卫庄公后来至少又临幸过三名女子,但我仍坚持认为他与庄姜保持了良好的夫妻感情。
我们应该注意到《卫康叔世家》记载的这个细节:娶了庄姜之后,卫庄公又娶了来自陈国的两姊妹即厉妫与戴妫。厉妫虽然为庄公生了儿子,但这个孩子不幸夭折。而戴妫为庄公生了儿子——也就是姬完,后来继承了卫庄公之位的卫桓公——之后,儿子是活下来了,她自己却英年早逝。
照常理推论,如果卫庄公因为姬完年龄太小、长养为难而要给他找一位养母的话,最合适的人选该是厉妫。因为厉妫是戴妫的姊妹,是姬完嫡亲的姨妈,跟侄儿的血缘关系最近。可是卫庄公并没有这样做,他完全不顾厉妫此时也正膝下无子的事实,指定让庄姜收姬完为养子,并把这个孩子册立为了太子。
这个政治安排的意图很清楚,卫庄公是希望在自己百年之后,继位的姬完能成为庄姜晚年生活的保障,让她继续享受国母的尊荣。
至于说庄公对州吁之母的嬖爱,《左传·隐公三年》既称州吁的母亲为“嬖人”——也就是虽被宠幸,但身份仍然卑贱,又说大夫石碏曾建议庄公如果真的偏爱州吁,索性废掉姬完,改立州吁为太子,遭到了卫庄公的断然拒绝。
这两点都说明卫庄公对身后事的安排仍是以庄姜、姬完母子为重。卫庄公从未像晋献公宠幸骊姬那样,起念让州吁母子取庄姜、姬完而代之。这又怎么能说庄公生前与庄姜感情破裂呢?
“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这两句诗所表达的不该是庄姜对丈夫移情别恋的抱怨,而是庄公去世后,卫国随之而来的大动荡勾起了庄姜的丧夫之痛,让她更加深切地思念自己的亡夫,所以她才会说,从前疼爱我的那个人,再也回不来了。
同理,诗歌的第三章“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也不能像郑玄那样,解释作“无善恩义之声语于我也”。这个解释根本不符合语言表达的逻辑。
如果训“良”为“善”,既然言语不善,那就不能被称为德音,“德音不善”,这成什么话呢?郑玄也不是看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把“德”、“良”都视作“音”的定语,可是这又明显不符合原句的语法结构。
“德音无良”的“良”字,当如“良宵”的“良”字一样,训作“长”。德音无良也就是德音不永的意思。庄公中道亡故,不能与己偕老,庄姜所感叹者,乃是他的德音不再。
至于诗歌的卒章,“父兮母兮,畜我不卒”。郑玄解释作“己尊之如父,又亲之如母”,而《先秦诗鉴赏辞典》则翻译作“父亲啊母亲,夫爱我不长”。虽然两派学者对主人翁身份的猜测截然不同,但却都认为“畜我不卒”的主语不能是父母而只能是丈夫。
也就是说,两派学者在串讲文义的时候都遭遇了同样的困难:他们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日月》的第四章要突然将感叹的对象从丈夫换做父母,于是只好迂曲作解。
从原诗的文本看,“畜我不卒”的主语很明显就是“父兮母兮”,在其间强插入一个“丈夫”,释作“丈夫爱我不长”,这样添字为释实在太过武断。而郑玄把“父兮母兮”解释作“我”把丈夫看作是父母一样,比拟更是不伦不类。
我们不妨站在庄姜的立场上来揣测她的心境:州吁之难发生的当时,距离卫庄公的离世已经过去了16年。如果不是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导致养子卫桓公被弒,自己老无所依,庄姜该不至于又突然对身故十几年的亡夫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悲痛。
换句话说,庄姜的悲痛,其直接诱因是州吁之难而非庄公之死。因此,这首诗的主旨该是借思念庄公来哀伤国难,而不是反过来。
既然庄姜能把这份悲伤寄托在庄公的身上,她当然也能移情于父母。把“父兮母兮,畜我不卒”翻译过来,它的意思应该是:父亲、母亲啊,你们当初为什么不能养我到老呢?——言下之意,我如果不嫁来卫国,又怎么会遭遇今天的悲剧!
参考文献:
高本汉《高本汉诗经注释》;
孔颖达《毛诗正义》;
《先秦诗鉴赏辞典》。
— THE END —
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图片|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