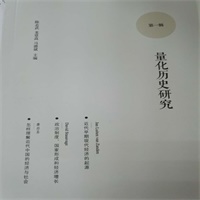欧洲从古典时代(classical antiquity)转向中世纪(the medieval period),是欧洲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转型之一。古典时代的欧洲经济和政治活动紧密围绕在地中海沿岸,而到中世纪时期,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已经转移到西北欧地区以及中东阿拉伯地区。促使这一转型的原因历史学家仍然存在争论,其中,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在其著作《穆罕默德和查理曼》中认为,北欧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的入侵并没有彻底改变古典时代长久以来的地中海商业传统,是阿拉伯帝国的扩张才彻底终结了欧洲地中海贸易网络,进而推动了西北欧的加洛林帝国兴起,并最终塑造了中世纪的欧洲经济地理格局。
为了全面考察欧洲从古典时代向中世纪转型期的经济结构变化,Johannes Boehm和Thomas Chaney两位经济学家借助独特的古代钱币流动数据来再现古代地中海地区间的贸易流量,并借助一个动态贸易结构模型揭示了地中海周围地区从公元4世纪到10世纪的实际消费情况,全面展示了对外贸易、技术进步和铸币税三个因素是如何共同推动了古典时代向中世纪的转变。
作为欧洲古典时代的重要标志,罗马帝国控制下的地中海地区长久以来都是整个欧洲的经济中心。公元395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逝世,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和西罗马。西罗马在北部日耳曼人的长期侵扰下于公元476年终结,其统治的地中海西部地区被不同的外族人所占领。而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Byzantine)帝国,则不断尝试收复原本西罗马帝国的土地。但到公元6世纪开始,东部的波斯萨珊帝国(Sasanian Empire)扩张与拜占庭帝国矛盾不断,公元602-628年的拜占庭-萨珊战争更是几乎耗尽了两国国力,由此产生的权力真空使阿拉伯帝国得以迅速扩张。
图1展示了阿拉伯帝国从公元623年到公元750年的扩张情况。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始自公元622年先知穆罕默德(Mohammed)出走麦地那;穆罕默德死后的正统哈里发时期(Arab caliphate),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开始不断加速;到公元661年四大哈里发时期结束时,阿拉伯帝国已经消灭了波斯萨珊帝国,并控制了整个阿拉伯半岛以及地中海东南沿海等地区。此后的阿拉伯倭玛亚王朝(Umayyad)时期,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仍然没有停止。
到公元750年倭马亚王朝被阿巴斯家族(Abbasid family)推翻时,阿拉伯帝国已经基本控制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Iberia,阿拉伯人称“安达卢斯”,al-Andalus)。阿拉伯帝国向东消灭了波斯萨珊帝国,但与拜占庭帝国之间领土边界得以长期维持。尽管如此,阿拉伯海军终结了拜占庭帝国在地中海东西海域的控制,对地中海沿岸城市的袭击变得十分频繁。
图1 阿拉伯帝国的疆域范围变化,公元634年到750年
虽然阿拉伯帝国扩张似乎的确影响了地中海贸易,但想要详细刻画在公元4世纪到10世纪地中海周边地区的贸易模式的转变却并非易事,其首要问题就在于缺少这一时期各地区间贸易流量的数据。然而,两位作者巧妙的利用货币的交换特征,利用钱币流动作为货物贸易流动的代理变量,解决了无法刻画古典时代向中世纪转型时期地中海地区贸易网络的困难。
具体而言,作者借助了“构建古典时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经济”项目(the Framing the Late Antique and Early Medieval Economy project,FLAME),该项目旨在研究对公元325年到725年地中海周边地区的经济活动,并以钱币(coin)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收集了欧洲、中亚和北非地区数十万枚钱币的铸造地点、时间以及最终贮藏的地点和时间等信息。
在此基础上,作者额外收集了公元725年后来自830个超过十万枚钱币的贮藏地信息,作为对FLAME项目的补充。所有的钱币都包含以下信息:1. 钱币的铸造地点,2. 钱币的铸造时期,3. 钱币最终的贮藏地,4. 钱币被贮藏的时间区间。作者将研究的地理区域限制在环地中海地区以及中亚阿拉伯地区(参见图2),并最终得到公元325年到950年的5625个钱币贮藏地,近五十万枚钱币的信息。
图2 研究地理范围及地区划分示意图
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后来的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其经济活动都高度货币化,因此钱币流动能够较好的反应当时的货物流动。根据古钱币的流动情况,作者总结了三个特征事实:第一,地理距离和政治边界的确会影响钱币的流动,即影响贸易。第二,更古旧的钱币会流向更远的地区。第三,钱币流动的地理分布在阿拉伯帝国扩张后产生了显著的变化。
根据图3,在阿拉伯帝国扩张进程开始前,钱币的铸造和流动集中在君士坦丁堡、罗马、迦太基等地中海周边城市。而到公元713,阿拉伯人已经征服了地中海东岸,北非和大部份伊比利亚半岛地区,钱币的流动模式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绝大部分钱币都铸造于地中海东岸、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阿拉伯帝国核心地区以及西北欧的法兰克地区,钱币流动网络也各自形成两个相对分离的网络。
图3 阿拉伯征服前后地中海地区的钱币流动情况
注:图中连线连接钱币的铸造地和最终发现地,指代钱币的流动。空心点代表钱币铸造地
基于上述特征事实,作者构建了一个包含货币扩散的动态量化贸易模型,从而将贸易成本、铸币决策、技术进步等因素纳入到分析古典时代经济地理的转变中去。此处,我们不对模型的细节做过多阐述,仅大致描述模型的构建思路和均衡条件。
作者的模型基于两个核心假设:第一,钱币是用作交易媒介。第二,钱币是可替代的。在这两个假设下,所有钱币的流动情况就可以视作实际货物贸易流的情况。每一期每个地区的贸易流量与Eaton和Kortum(2002)模型一致。由于货币本身同时承担了交换媒介和价值贮藏两种功能,因此即便在模型中钱币流动同样服从引力模型形式,但钱币流还需要额外考虑储蓄率。此外,钱币并不像货物一样只流动一次,而是会随着交易在其生命周期中持续进行流动。因此,钱币流动的贸易成本会随着其使用次数的上升不断下降,并在贸易网络中趋向均匀分布。
为了使模型匹配实际数据,作者假定钱币按照固定比例磨损折旧并最终贮藏到不同地点,根据数据计算得到的磨损率约每20年损失30%的钱币。贸易成本包括双边贸易运输时间,以及政治边界效应和信仰边界效应。其中,运输时间数据来自两个数据集,分别是主要测量地中海周边地区贸易路线和成本的Orbis数据库(Scheidel,2015),以及测量阿拉伯地区贸易路线的al-Ṯurayyā数据库(Romanov和Seydi,2022)。作者还详细设定了不同地区铸币厂的钱币生产模式和钱币的生命周期并使之符合历史趋势。最终的模型均衡在于通过选择货币存量来确定每一期的实际消费。更详细的模型参数和变量计算请参阅原文。
基于这样一个包含货币的量化贸易结构模型,作者将社会总福利,即整个社会的人均实际消费分解为三个部分:对外开放程度(openness),技术进步(technology)和贸易赤字(trade deficit)。其中,对外开放程度体现的是常规的贸易所得(Gain from Trade),技术进步则通过提高个体劳动的货币收入增加实际消费,贸易赤字则反映了铸币税(seigniorage revenues)的好处,即通过直接铸造货币在不增加出口的情况下增加进口,从而提高实际消费。
图4展示了拜占庭帝国和西北欧地区在公元4-9世纪的实际消费及其三个构成部分的历时变化。可以看到,拜占庭帝国从4世纪开始就一直是最富有的地区,其实际消费中更是有60%的消费依赖于进口。对外国商品的依赖很大程度上由拜占庭帝国的铸币税所支撑,因为其贸易赤字巨大且技术水平没有明显变化。而伴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拜占庭帝国遭受了全面的冲击:首先是拜占庭黑暗时期(Byzantine dark ages,公元6-8世纪),其国内铸币产出陷入停滞;其次是与伊斯兰世界贸易成本的激增,以及技术崩溃。与此同时,西北欧的法兰西和日耳曼地区的实际消费则持续上升,这一上升几乎完全由技术进步所推动,因为这一地区本身对外开放程度有限,贸易对实际消费的影响十分有限。
图4 拜占庭帝国对比法兰西和日耳曼地区的实际消费,公元380-880年
注:图中蓝色线代表法兰西和日耳曼地区,橙色线代表拜占庭帝国
作者进一步检验了阿拉伯帝国扩张前后两个时期,即公元460-620年与公元700-900年两个时期不同地区实际消费的变化情况,其结果展示在表1。可以看到,除了已经讨论过的西北欧和拜占庭帝国,原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埃及(Misr)和大叙利亚地区(al-Sham)在被阿拉伯征服后实际消费并没有显著下降,原本的贸易被阿拉伯帝国内部贸易所补偿,而铸币能力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最终的福利水平。阿拉伯半岛地区(Jazirat al-arab and al-Yaman)作为古典时代晚期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在阿拉伯征服之后实际消费大幅改善,其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和铸币税所驱动。
表1 公元460-620年与公元700-900年实际消费变化及分解
总而言之,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对原本基督教世界贸易网络的破坏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欧洲的经济地理分布,这有力的支持了皮雷纳对欧洲古典时代向中世纪转型的观点。但皮雷纳认为阿拉伯帝国扩张同样破坏了西北欧地区的经济,事实上,西北欧地区原本就较少依赖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的下降几乎没有影响,而铸币税带来的贸易所得甚至提高了实际消费。只有拜占庭帝国在阿拉伯扩张过程中遭受了明显的三重冲击。不同经济因素在塑造中世纪经济地理格局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而借助现代的动态量化贸易模型方法,我们能够在统一的框架下深入分析和比较不同因素的影响大小,从而丰富我们对传统历史问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