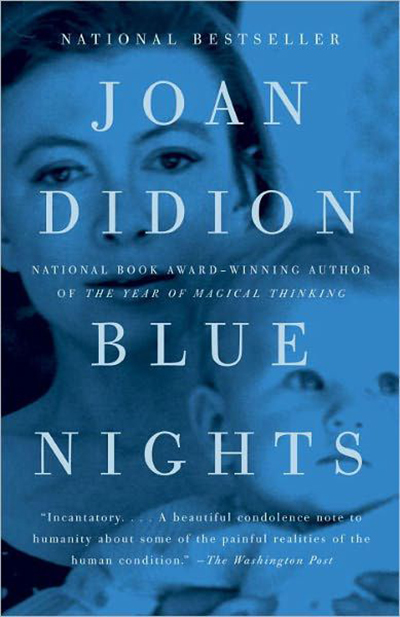
Blue Nights, Joan Didion, Fourth Estate, 2011书是这样开始的:
2010年7月26日。今天本该是她的结婚纪念日。
2003年琼·迪狄恩的女儿金塔纳·罗奥在纽约阿姆斯特丹大道的圣约翰大教堂成婚。日期很重要。一个像迪狄恩这样挑剔的作家,日期承载了许多重量。细节也很重要,有时候比主旨还要重要,甚至取代了主旨:
七年前的今天,我们从花店的盒子里拿出花环,它们是带土包装,我们甩掉了上面的水……白孔雀开屏了。管风琴响起。她粗粗的辫子垂在背后,上面编着开白花的千金子藤。她戴上薄纱时,千金子藤松动,掉了下来。鸡蛋花盛开。
迪狄恩这里那里都没有提到过,金塔纳长什么样子:她是高是矮,是胖是瘦,谁知道?
《蓝色的夜晚》题献给金塔纳。书名指的是一种暮光的颜色,“法国人叫一天中的这个点‘蓝色时光’。”四月末你就能看到它,“突然间夏天就临近了,成了一种可能,甚至一种承诺”;但只能在特定纬度看到,比如迪狄恩现在住的纽约,她出生的加州就看不到。当白天变短,这种暮光也随之消失:“当蓝色夜晚接近结束时(它们的确会结束),你能感到真正的凉意,一种对生病的恐惧。”那时迪狄恩快七十七岁了,在金塔纳的婚礼和写作《蓝色的夜晚》之间,她的作家丈夫约翰·格雷戈里·邓恩和女儿相继离世:书名的涵义显而易见。
2003年邓恩死于心脏病。“我当时正专心拌色拉。约翰在讲话,然后没声音了。”他的去世以及迪狄恩的反应——她的悲伤有各种复杂表现:心理的不确定,时时幻想他会回来(他会需要他的鞋子),以及他说自己要死了的时候她并没有立即相信他的内疚——是2005年出版的《奇想之年》的主要内容,不久就被百老汇改成了话剧,由瓦妮莎·雷德格瑞夫主演。邓恩去世的时候是12月30号。“你只是坐下吃个饭,你所熟悉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八天前,金塔纳发了四十度高烧,去上东区看了急诊,被告知得了流感;她在圣诞节那天住了院,当晚进了重症特别护理间。X光显示她得了双侧肺炎,血压显示败血性休克。“我觉得我做不到,”邓恩在探望女儿之后回家的出租车上说。“你没选择,”迪狄恩回答。后来她觉得自己可能错了。那个时候大家并不清楚金塔纳是否能活下来。她的病在《奇想之年》里是次要内容。“当我们谈论人必有一死时,我们在谈的是我们的孩子。”
1月中旬,金塔纳的药量减了下来,她得知父亲去世了。在他的葬礼上,“是她八个月前结婚的同一座大教堂”,她读了一首悼念父亲的诗。两天后,她和丈夫启程去洛杉矶,准备开始新生活。那是3月,也就是她首次患病三个月后。“她问我,你觉得我在洛杉矶会好吗?我说会的。”她在机场出来去取租赁车时昏倒了:
他们下了飞机。
他们拿了行李。
“当我写书时,”迪狄恩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告诉希尔顿·阿尔斯(Hilton Als),“我不断重新打我自己的句子。每天我都回到第一页,重新打一遍。这让我进入一种节奏。”她写《奇想之年》时也是这样吗?“这对这本书尤其重要,”迪狄恩回答,“因为太多东西依赖回声。”在《蓝色的夜晚》中,这节奏是一个长段落之后跟的两三行一句话的段落。那些日期,那些斜体字,几乎是仪式性的重复,感觉像一个套索,一句咒语,一种引诱,让你无法逃脱。你觉得你是在写自己的句子,然后发现你其实在模仿她的。
金塔纳被送进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的神经外科。可能是她摔倒导致了脑溢血,或是脑溢血导致了她昏倒。哪种情况并不重要。(“有两种可能,在我看来它们都无关紧要。”)问题依然是,她能否活下来。迪狄恩飞去洛杉矶,重新开始陪夜。“她是个冷静的人,”纽约医院的医生告知她邓恩的死讯时这样评价她。迪狄恩不觉得这评价没有根据,只是想,一个不冷静的人能被“允许”做什么。他们可以大喊大叫吗?
她没有尖叫,没有崩溃,不需要打镇静剂。她没有不停问医生要“预后诊断”,这是神经外科的其他病人家属爱做的。相反,她“提醒一个见习医生注意水肿部位,提醒另一个在做尿培养时检查导尿管里的血迹,坚持做一次超声波来诊断血栓是否是导致腿疼的原因”。如果这些让她不讨“医院里的年轻男女职员”的喜欢,随便他们去。迪狄恩是一个引人入胜的作家:她不一定要讨人喜欢,或和蔼可亲。
“在艰难时期,我自幼被训练去阅读、学习、翻检文献。信息就是控制力。”她熟知医生安排的所有神经系统检查的名称(“木村盒子测试。两点辨别觉试验”),以及金塔纳的昏迷程度(“格拉斯哥昏迷记分法,格拉斯哥预后评分”),她还知道金塔纳用的所有抗生素的名字,阿奇霉素、庆大霉素、克林霉素、万古霉素——这些都是节奏的组成部分。如果她不需要“预后诊断”是因为她很清楚不可能有,“我记得被告知,至少要三天才可能开始了解她大脑的基本状况”,所以她不问没有意义的问题。
五周后的4月底,金塔纳有所好转,乘救护飞机回了纽约。接下来是去另一家纽约医院的康复中心。喂食管随时准备,但已经不是必需。她的右手、右腿逐渐恢复功能,右眼也恢复了视力。周末她丈夫会带她出门吃午饭。顺便提一句,她的丈夫叫格里,他在迪狄恩的故事里时不时出现,没有被遗漏。
2004年12月31日迪狄恩写完了《奇想之年》,一年结束了。“约翰没有看到一年前的今天。约翰死了。”她不再争论这一事实,不再想着他的鞋子,不再通过他的眼睛去看自己:“今年是我二十九岁以后第一次通过其他人的眼睛看自己。”2004年12月31日,金塔纳还活着。一年前的此时,她在医院的重症病房,她的圣诞礼物堆在卧室,等着她好起来。但现在没有提到礼物,这是不祥之兆吗?
琼·狄迪恩八个月后的2005年8月26日,《奇想之年》出版的两个月前,金塔纳去世了。整整二十个月里她都在病中。迪狄恩在《蓝色的夜晚》里告诉我们:“二十个月里,她有力气不靠支撑走路的时间不过一个月。”
《蓝色的夜晚》要比《奇想之年》更焦虑,更多自问,它关乎恐惧,迪狄恩的恐惧和金塔纳的恐惧:害怕被抛弃,害怕时间流逝,害怕失去控制,害怕死亡;也关乎记忆,1960年代中到1980年代末迪狄恩和邓恩住在加州,金塔纳成长的那段时间的记忆;一段美好的时光,“百子莲也叫尼罗河的百合花,长长的花茎上摇曳着绽放的亮丽蓝花”;孩子们开始喜欢鱼子酱,生日时大家会放飞许多气球,任由它们飘去好莱坞的山上;那时恐惧被遮蔽了,或者说无法辨别,迪狄恩还是一个写书的母亲:
她荡过秋千的夹竹桃树枝看着眼熟,她踢过海浪的沙滩的曲线亦如此。
她的衣服当然更熟悉。
有段时间我每天看到它们,洗它们,把它们晾在书房窗外的衣架上吹风。
在看着她的衣服变干的日子里,我写了两本书。
听上去很美好。谁不想又有孩子又能写书呢?金塔纳生于1966年3月。她不是迪狄恩和邓恩的亲生孩子。迪狄恩在二十多岁时第一次想要孩子,当时她住在纽约,在《时尚》杂志工作。1966年她已经三十一岁了。她是不是一直想着要孩子,然后绝望了呢?还是有别的想法挤了进来?在《奇想之年》中,她提到过去一切都那么容易,“那段时间好像我们做什么都不会有后果”。收养孩子的决定也是这样吗?这是1960年代的万事不上心的一桩吗?那是1966年新年,她和邓恩跟朋友们在一条船上,他们在想下一轮喝什么。“也许因为厄斯金一家也在”——厄斯金一家是朋友的朋友,领养了一个女儿——
也许因为我提到想要一个孩子,也许因为我们都喝多了,于是谈论起了领养的话题……
就这样。
接下来的一周我见了布莱克·沃森。
布莱克·沃森是接生了厄斯金养女的产科医生。
三个月后他给迪狄恩和丈夫打了电话,说他接生了“一个漂亮女婴”,但孩子母亲没法养育她,你们有兴趣收养吗?他俩去了医院,看了婴儿,决定收养她,他们给邓恩的哥哥打了电话,去贝弗利山庄喝酒庆祝(“只有在重读我早年的小说时,里面总有人在楼下喝酒唱着‘温尼卡传来巨响’,我才意识到我们喝酒那么多,顾虑那么少”)。邓恩的嫂子莱妮约她第二天去萨克斯百货买全套婴儿用品,她只要花到八十美元,萨克斯百货就会送一个“婴儿摇篮车”。
我拿起杯子,又放下了。
我还没想过是否需要婴儿摇篮车。
我还没想过是否需要全套婴儿用品。
正在发生的一切都难以想象,有一个小孩跟买这些东西似乎成了同一事业不可分割的部分。
倒不是说迪狄恩对物质不感兴趣,她对服装及其历史尤其感兴趣。衣服和日期有同等的分量,它们标记了时光的流逝(“我买那件黑色印花丝毛裙子的时候,班道尔精品店还在西57街”),尤其是好时光(“她穿了克里斯提·鲁布托的鞋”,“她在圣坛前跪下时你就能看到鞋的红底”),并且能够区分时代的分野(“现在我再看那些老照片,会惊诧于有那么多女人穿香奈儿外套、戴大卫·韦伯的手链”),情绪的变化。婴儿摇篮车是个转折点:“在婴儿车之前,一切都显得随意,甚至无忧无虑,人人都爱穿的贾克斯运动衫或莉莉·普利策的纯棉印花度假衫没有精神境界的不同。”
在婴儿车之前,他们曾计划去西贡,“我们有杂志委约,有通行文书,一切都准备就绪。包括,突然有了一个孩子。”那一年尤其不适合去那里旅行——美国开始轰炸北越,她却没有想过放弃计划:“我甚至去店里买了想象中我们需要的东西:唐纳德·布鲁克斯家的粉彩亚麻裙子,包特豪家的婴儿遮阳伞,好像我和她马上要登上泛美航空,然后在西贡法租界的体育圈俱乐部降落似的。”最终未能成行,并非因为“明显的原因”,而是因为邓恩必须得完成一本书。
在金塔纳和莉莉·普利策的转折后不久,恐惧来临了,“她出生后我没有一刻不在害怕”,“害怕游泳池、高压电线、水池下的碱液、药柜子里的阿司匹林……响尾蛇、激流、滑坡、门口的陌生人、无法解释的发烧、没有操作员的电梯、空荡荡的宾馆走廊”。这是个叫人着迷的清单,“激流”“滑坡”并列时听上去特别和谐(Riptides和landslides押韵——译注)。等到金塔纳六个月大时,领养手续全部办好,迪狄恩有开始担心孩子会被生母要回去,被带走。几年后她意识到自己“不是家里唯一担心这些的人”,金塔纳也会问:“要是沃森医生打电话来的时候你没接会怎么样?”“你要是不在家,要是你不能去医院见他,要是当时高架上出事故了,我会怎么样?”迪狄恩的回答很轻快:“既然我没有合适的回答,索性拒绝去考虑它们。”好吧,也有道理,虽然有些平淡无奇。迪狄恩对别人说了什么更感兴趣,而不是他们为什么说,她更感兴趣的是人们感受什么而不是为何感受。弗洛伊德学派那一套,对她没什么意义。她有自己的一套句法。
什么时候迪狄恩才意识到,金塔纳并不算健康,她的情绪变化太快,长大以后会抑郁焦虑(“我们去看过许多医生,得到过各种诊断,听到过各种病的名字”)?是当她在车库门上贴一张“妈妈语录”说“你要刷牙,要梳头,我工作的时候你要安静”的时候吗?还是更早一些,她还不到五岁,告诉父母他们不在家的时候她给精神病院打电话“问如果我发疯了应该干什么”的时候?还是她给21世纪福克斯电视台打电话问“怎么才能变成一个明星”的时候?还是几年之后,她告诉父母她正在写一部“只给你们看的”小说——金塔纳去世后迪狄恩发现了这小说,它的女主人公叫金塔纳,小说里她死了,而她的父母“根本无所谓”。
迪狄恩现在看金塔纳小时候的照片,开始想自己怎么会没看到“她表情里的令人惊诧的深和浅,如水银流动的情绪变化”。但这里的标准又是什么?父母要有多警惕,才能日后不后悔?或是要有多幸运?“当我们谈论我们的孩子时……我们谈论的其实是……为人父母的迷惑?”迪狄恩问道。她谈论金塔纳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在想自己?
“我是问题所在吗?一直以来都是我的问题吗?”她无法找到办法帮五岁的金塔纳拔牙时这样问道。
我对母亲最连贯的一段记忆是她用一根线绕在松动的牙齿上,另一头拴在门把手上,然后用力摔门。我试了这一招。牙齿纹丝不动。她大哭。我拿了车钥匙,用线拴门把手不成后我已黔驴技穷,只想着快快送她去三十多英里外的加大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的急诊室……
后来她又有一颗牙齿松了,她自己动手拔了。我已经失去了权威。
“我不认识太多自以为是成功父母的人,”迪狄恩不屑一顾,“那些喜欢引用指标以显示(他们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的人——斯坦福学历、哈佛MBA、在顶级律所工作。”这些指标不太会让迪狄恩刮目相看,所以她选了它们。无论如何她已经相当成功,不需要金塔纳为她争光。但是父母已经不需要的那些成功指标,恰恰是金塔纳着迷的。迪狄恩和邓恩除了写小说,还写电影脚本,他们有很多好莱坞的关系,过着好莱坞式生活。于是有了金塔纳的小说,以及她给21世纪福克斯打的电话。金塔纳四五岁时,迪狄恩带她去看《俄宫秘史》。迪狄恩问她喜欢吗,她说:“我觉得这片子肯定能红。”“这是不是她对自己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的位置感到迷惑?”迪狄恩在书里这样问,我倒觉得别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家长要带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去看《俄宫秘史》。“是不是我们在她在没有生活能力的时候就让她开始承担责任了?是不是我们的期望导致她的回答并不像个小孩?”
这个问题在不同语境中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重复着。他们不需要答案。安慰和保证也属于迪狄恩不需要的东西。她在跟自己交谈,衡量过去,回想往事,给自己作伴。她把自己暴露在外,“我是问题所在吗?”拔牙惨败之后开车找医生,想去西贡拗造型又没能成行,这些叙述并没有回答问题,但滑稽好笑,都是我们女人爱写的自曝故事——不过迪狄恩即使在极度沮丧之时,下笔也比别人更无情。
比如说金塔纳的毛病是“如水银流动的情绪变化”等等。“我怎么会对如此清楚明显的迹象视而不见?”她自问。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再后来,有了各种诊断。“躁郁症……变成了OCD,OCD是强迫症的缩写,强迫症又变成了别的什么,那个病的名字我怎么也记不住。”一个又一个诊断接踵而来,迪狄恩变得越来越激烈:“我没见过一个‘诊断’能指向‘治愈’,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结果,只是不断确认有病而已。”最终诊断结果停在了边缘型人格障碍,手册上说:“这类病人,时而看似可爱、镇定、心理正常,时而陷入想自杀的绝望。”至少这一诊断是迪狄恩可以接受的。“我见过她可爱,见过她镇定,也见过那种想自杀的绝望”:
我见过她躺在客厅的地板上,一心想死,她的公寓在布伦特伍德公园,从那个客厅可以看到粉色的木兰花树。她不断抽泣着说,让我入土,让我入土为安吧。
请注意粉色木兰花树,无论这一刻多么痛苦,迪狄恩也没放过节奏和装饰物。书中有几处幕间休息,有外人进入。金塔纳的生母是其一,这个插曲被冷处理了。迪狄恩对她略有反感,无大兴趣。另一个插曲比较烦心,有瓦妮莎·雷德格瑞夫的女儿娜塔莎·理查德森(Natasha Richardson【1963-2009】,英国演员,瓦妮莎·雷德格瑞夫和导演托尼·理查德森的女儿。动作巨星连姆·尼森的妻子)——她和父母一样是迪狄恩的朋友,2009年初在滑雪时遭意外去世。她比金塔纳大三四岁,似乎要优秀很多:
我和约翰到达的时候……娜塔莎在看管“公爵老巢”(Le Nid du Duc是托尼·理查德森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蓝色海岸的海滨小镇圣特罗佩的房产,经常接待文艺圈好友,画家大卫·霍克尼、小说家衣修伍德等都是常客——译注),17岁的城堡女主人,要为30个人开一夏天的派对。她得管整个别墅群的后勤补给。她烧饭端饭,完全没有帮手,30个人的一日三餐,还不时有人爬上山来蹭饭……娜塔莎确保金塔纳和罗克珊娜在海滩上找到好位置……娜塔莎把金塔纳和罗克珊娜介绍给意大利男生……娜塔莎能做完美的牛油沙司……娜塔莎设计神话,缔造罗曼史。
可怜的金塔纳。娜塔莎忙着做牛油沙司的时候,她躺在地毯上一心想死。迪狄恩写朋友女儿跟写自己女儿时不太一样,可能有几个原因。娜塔莎是外人,无论得到了多少夸奖,也都因为她是外人才被夸奖(不是说她不值得夸奖)。不像金塔纳,她没有进入迪狄恩句子的节奏;她没有得到单行的待遇,也没有被允许打断迪狄恩与自己的对话。除了心痛的对比之外,很难知道娜塔莎在这里扮演的角色,除非是作为迪狄恩在一生中感到痛心失去的另一个人物。
《蓝色的夜晚》是一本关于金塔纳的书,是题献给她的,封底有一张她的照片,看上去好像21世纪福克斯已经让她成了明星;她是全书的中心,更确切地说,是迪狄恩记忆的中心,是她痛失的至爱。但是,迪狄恩本人是书的主题,它最好的主人公。这不是说她不想念金塔纳,她想得要命;也不是说她要霸占聚光灯,或是她推卸责任,或是她只想着自己;她的写作是有分寸的,有它自己的自恋优雅。
快到结尾处,金塔纳已经从前景淡去,迪狄恩写到如今的自己:脆弱、不确定、不安稳、无儿无女;害怕从折叠椅上起来;害怕承认自己不知道怎么启动一辆陌生的车;害怕自己无法再讲故事,“再也不能把字放在对的地方”;害怕死亡,害怕活太久;她告诉自己不要哀怨,要习惯孤单;她在卧室晕倒过,醒来时没法动弹,碰不到家里十三部电话中的任何一部。简言之,她发现自己不是在变老,而是已经老态龙钟:
一天我们看马格南1968年在迪奥大秀上拍的索菲娅·罗兰,心里想着,那也可以是我啊,那一年我也在巴黎,我也可以穿那条裙子啊;一眨眼的功夫,我们已经在这个那个医生的办公室里,听医生说哪里又不好了,为什么我们再也不能穿四英寸跟的红色麂皮凉鞋了,再也不能戴大圈金耳环和搪瓷珠项链了,再也不能穿索菲娅·罗兰穿的裙子了。
“当我开始写下这些时,”迪狄恩在书开头就说,“我相信它的主题是孩子,我们有的孩子和我们希望有的孩子,我们指望着孩子会依赖我们……于是我们和他们都无法忍受去深思生老病死,甚至彼此的长大和变老。”接着,“当书页逐渐积累,我慢慢发现它的主题是人无法面对衰老、生病、死亡的必然性……只有等书页继续积累时,我猜明白这两个主题是一回事。当我们谈论人必有一死时,我们在谈的是我们的孩子”——那些我们死时已经无法哀悼我们的孩子。
(本文选自玛丽-凯·维尔梅斯文集《谁不爱被当成圣人对待》)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