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导读
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时间2021年11月3日早晨在家中去世,享年91岁。消息经确认后,各大媒体纷纷推出纪念文章。我们选取了《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2009年对李泽厚先生的一篇访谈。选择的理由是:这篇访谈比较全面的回顾和梳理了李泽厚对改革开放开始之后的那个思想解放时代的影响,且经过李泽厚先生本人审定。(由于某些原因,在刊出时有删节)
在整整一代人的记忆里,八十年代是最开放的年代,所有人对人类先进的知识充满了学习的渴望,所有人对未来都充满了热情和想象。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等代表著作及其承载的思想,对那个年代人性的回归、思想的涌动,包括“美学热”“文化热”等现象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重发此文,表达对李泽厚先生的敬意和纪念。李泽厚先生千古。
《批判哲学的批判》
马国川:当年,你在北京大学读的是哲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哲学所工作,但是为什么你发表的是美学文章,而且以此成名?
李泽厚:这主要是人民日报、文艺报等中央报刊搞美学大讨论的缘故。我从小就喜欢读诗词小说,对文学有兴趣,同时也对哲学、心理学有兴趣。我的性格比较内向,不喜欢和人交流,上大学时主要是自学,自己跑到图书馆看书,看了很多美学方面的书,也积累了某种看法。美学名家朱光潜、宗白华都是北大的教授,但是那时候学校没有美学课,我虽然对美学有兴趣,但是在学校始终没有见过两位前辈。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哲学所工作,我没有做研究生,也不想做。最早我被分配到上海复旦大学,但复旦大学拒收又回到北京。不久,恰逢美学界开始了“美学大讨论”,我就很自然地参加了进去。美学一直是一门哲学学科或哲学分支,所以我写美学文章也不奇怪。我本来对美学有浓厚兴趣,而且我一直不太在意学科的区别。
马国川:“美学大讨论”是从1956年开始的,延续到60年代初。
李泽厚:本来是以批判朱光潜过去的美学思想开始的,所以说不上平等和心平气和,但这是一场具有学术意义的讨论。1949年以后的许多讨论都以讨论开始、以批判结束,最后总是一种意见压倒其他意见,只有美学是例外,开始是三派,讨论结束还是三派,因此美学始终保持了难得的某些学术自由度,这对美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
马国川:你关于美学讨论的文章发表不到半年,反右运动就开始了。你很幸运地逃过了反右运动……
李泽厚:反右运动开始前,我就离开北京和我们所里一些人到敦煌去考察壁画。一个月后从敦煌回到北京的时候,反右的高潮已经过去了,而且当时所里的右派名额已经超过了一般单位的右派比例,所以有人说是“漏网右派”。虽然如此,因为我二十几岁就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文章,因而环境压力很大,“白专”之类的非议颇多,下放劳动我在单位大概是时间最长的一个。先是“大跃进”中,被下放到太行山区的农村劳动,后来又下乡劳动一年。以后参加“四清”工作两年。如果说第一次下放劳动最深的印象是累,那么第二次就是“饿”了。每天只能吃到四个白薯,没有别的东西吃。当时老乡还有自留地,我们则是什么都没有。6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算是个“逍遥派”,不介入那些纷争。我那时候已经结婚了,就尽可能地不去所里,躲在家里看看书。1970年,我们所集体下放到河南信阳“**干校”。去干校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箱子,是统一的,可以放衣服什么的,我则把我最喜欢的和自己觉得最值得读的书放到箱子里带到了那里。
马国川:是什么书?
李泽厚:我在行李中偷偷放了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英文版“人人丛书”里的一本。书不厚,但很“经看”。当时在干校,只准读《毛泽东选集》,连看马列也受到批评,要读其他书就更难了,只好又像回到解放前的秘密读书一样,阅读时上面放一本《毛泽东选集》,下面是康德,还偷偷地做些笔记。我决定写一本评论康德思想的书。1972年我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后,在家里我利用干校时的笔记正式写起来。别人也帮我借一些书,当然都是不能声张的。
马国川:在万马齐喑的年代,写书是一件危险的事,而且即使写出来也不可能发表。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你的思考和写作?
李泽厚:我没有想何时出版,虽然我深信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但是没有想到会很快出版。我的父亲早年去世后,母亲含辛茹苦抚养我们兄弟,有人说,等儿子长大你就可以享福了。母亲常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这话影响了我一生。只要一念及“不问收获”的话,我就继续写下去。1976年发生地震,我住在地震棚里,条件很差,我倒很充实,因为书稿写作已接近尾声了,书名是《批判哲学的批判》,副题是“康德述评”。我从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立场全面评述了康德学说,而且借评论康德,提出了人类学本体论的哲学观点。
马国川:这本书1979年正式出版,当时卖了三万册,在学术界是卖得最好的书。一本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纯学术著作会为什么会如此热卖呢?
李泽厚:时代使然吧。那时,学术界刚刚从时代的重创下醒过神来,一些人心有余悸,许多人严重失语。不要说做学问,连话都不会说了。《批判哲学的批判》是学术著作,没有八股腔,引起了青年学子的关注。
马国川:《批判哲学的批判》出版时,也正是高考恢复不久,许多刚刚进入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是你的热心读者。
李泽厚:那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农村里经风雨见世面,滚打跌爬,历尽磨难,对社会和人生都有自己的思考。再加上当时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号召的思想解放运动,对这些刚刚从社会底层浮出水面的大龄学生来说,陈旧的知识早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陈腐的说教更让他们心生厌恶。而我的书有些不同,所以受到喜爱。
我的书里有许多与当时不同的思想。我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讲,人是使用、制造工具来吃饭的,今天为止,什么都得靠工具,离开工具,人就没法活。这个就是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人类生存首先是物质生存,包括衣食住行和寿命,这是历史的基本要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是精神。人类要生存,吃饭并不容易,再伟大的真理都是从普通的事件中来。海内外都有人批评吃饭哲学“庸俗化”,可我就坚持我这个吃饭哲学。人的嘴巴有两大用处,一是吃饭,一是讲话,吃饱了饭就要大声说话。所以光喂饱人的肚子是不行的。
马国川:“吃饭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这个看似浅显的道理,却被之前空洞的道德说教蒙蔽了,而对于那些已经看透了道德说教虚伪性的青年人来说,你的声音确实新鲜而弥足珍贵,所以你成为他们崇拜的偶像。而且在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你用学术词语表达的意见也和一些政治家所力推的“思想解放”产生了“共鸣”。
李泽厚: 我曾经说,我和邓小平是“一致的”。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和后来写的《主体性提纲》中,再三强调,马克思主义应从批判的、革命的哲学转化为创造性的、建设的哲学。当然,我没有得到任何来自官方的授意,完全是个人研究得出的学术结论,而这个结论恰恰和解放思想的时代主题相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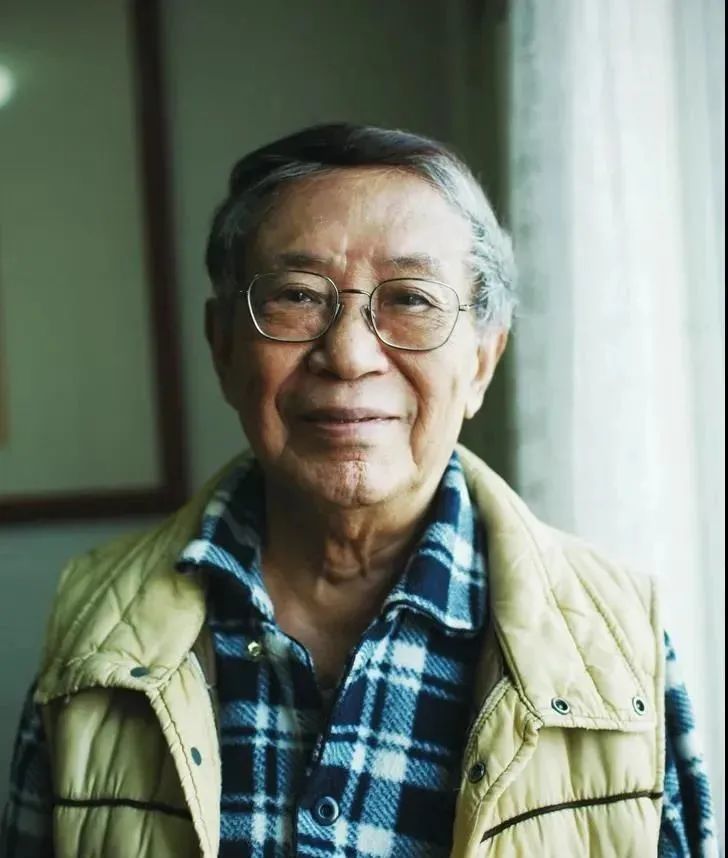
李泽厚先生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姜晓明摄
“美学热”
马国川: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出版的同时,中国大地上正在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诗歌热潮,读诗写诗、做文学青年似乎是那时的时尚。
李泽厚:那真是诗歌的春天!尤其是那些年轻的诗人,经过漫长的冬天后,终于在这个诗歌的春天里找到了创作激情和创作方向。北岛、舒婷、芒克、江河、顾城和杨练等诗人在北京创办了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在诗歌艺术上进行了探索。我读到了油印的《今天》,很感动,因为其中有着强烈自我意识。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潮著作开始大规模的译介进入中国,文化艺术思潮也进入一个以反叛和个性解放为主题的创作高潮。朦胧诗是代表。
马国川:这些诗确实与传统的诗歌大相径庭,所以有人指责这些诗“叫人看不懂”,并以此为由来否定它们的意义和价值,“朦胧诗”便因此得名。甚至有人说年轻诗人在历史观上太片面、情绪上太绝望悲观,呼吁人们帮助这些“迷途者”,以“避免走上危险的道路”。
李泽厚:还有人义正词严地痛斥朦胧诗是“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呢。但我说,朦胧诗是新文学第一只飞燕。它改写了以往诗歌“反映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实质上就是一场人的崛起运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的心声如洪流般倾泄而出时,这般洪流最敏锐地反映在文艺上,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也包括绘画方面。
马国川:你是第一个出来肯定朦胧诗的,你对“星星画展”的支持就是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年轻人。乍暖还寒时候,支持年轻人的探索是需要勇气的。
李泽厚:在长久的压抑之后,青年人要寻找新的表达方式,我为《星星画展》写了文章支持他们。写文章时我心里想的仍然是朦胧诗。当时不断传来的对舒婷、顾城的斥责声……一切都似乎如此艰难,我甚至准备再过冬天。
马国川:星星画展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起点,展出后引起了轰动,但是也遭到查禁。一些年轻人为了展出作品的权利,还高呼“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的口号游行。
李泽厚:我在《画廊谈美》为年轻人辩护:“在那些变形、扭曲或‘看不懂’的造形中,不也正好是经历了动乱,看遍了社会上、下层的各种悲惨和阴暗,尝过了种种酸甜苦辣的破碎心灵的对应物吗?政治上的愤怒,情感上的悲伤,思想上的怀疑;对往事的感叹与回想,对未来的苦闷与彷徨,对前途的期待和没有把握;缺乏信心仍然憧憬,尽管渺茫却在希望,对青春年华的悼念痛惜,对人生真理的探索追求,在蹒跚中的前进与徘徊……所有这种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混乱的思想情感,不都是一定程度地在这里以及在近年来的某些小说、散文、诗歌中表现出来了吗?它们美吗?它们传达了经历了无数苦难的青年一代的心声”。
马国川:“它们传达了经历了无数苦难的青年一代的心声”,这个表述很到位,所以“星星画展”撼动了当时的社会,当时几乎所有喜欢美术的人都去看。
李泽厚:我的文章发表在《文艺报》1981年第2期上,不久社会上掀起了“反精神污染运动”,“星星画展”被点名批判,所以我才有“我准备再过冬天”的感慨!但时代毕竟在迅速前进,尽管要穿过各种回流急湍,一代新人的心声再也休想挡住了。现在,“朦胧诗”“星星画展”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艺史上确立了不能忽视的位置,为文艺史和广大读者所认同,异端已经化为传统。
马国川:如果从广义上说,不管是朦胧诗还是星星画展,都是当时美学热的一种反映。
李泽厚:1949年以来有两次美学热。第一次是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第二次就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第二次美学热中活跃的中年人大多是通过第一次美学讨论引起了兴趣,以后选择了美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第二次美学热是第一次美学热的继续和发展。二者的差别在于,第一次美学热是自上而下,而这一次是由下而上,是一种群众性的由下而上,特别是很多青年人当时对美学有一种狂热的兴趣。
马国川:那时侯,工厂女工也要买美学书看,美学成了学子纷纷向往的显学。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在各专业的研究生招生与公共选修课中,美学专业总是名列前茅。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举,举国上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不是经济学等别的似乎更“管用”的学科,为什么偏偏出现“美学热”?
李泽厚:因为特殊时代以丑为美的现象实在太多了,一些野蛮的、愚蠢的、原始的行为也被推崇,给人们的教训太深了。这样,寻找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就带有很大的普遍性。有些年轻人告诉我,他们就是为了追求一种美的人生理想、人生境界而对美学有兴趣,研究美学的。
马国川:文学艺术也是一个原因吧。
李泽厚:对,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对美学的兴趣。那时文学非常热,而对于什么是美的、成功的作品,官方和民间的认识往往有差别,甚至相反。人们就追问:到底什么是美的成功的作品?判断一个作品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与美学有密切联系。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变革,日常生活中美的问题也突出了,比如喇叭裤、披肩发、牛仔装、蛤蟆镜到底美不美?是美还是丑?引起了社会上人们的广泛争论,它几乎关系到每个年轻人。美学热的兴起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的。美学热符合了社会进步的思潮,也是促进这个社会苏醒的符号。
马国川:你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就是以美学作为最终的理论总结。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涉及了美学问题。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编辑的大型丛刊《美学》(通称“大美学”)问世,这是中国当代第一本专业美学刊物,大约每年编发一期。刊物名义上是研究所美学室,实际上是我主编的,整个编辑部也只有我一个人。1980年出版的《美学》第二期发表了从美学角度重新翻译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朱光潜先生节译的,由此引发了美学界持续多年的《手稿》研究热,推动了中国美学的研究。同年还在昆明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美学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周扬很支持美学,他担任了名誉会长,朱光潜任会长,王朝闻、蔡仪和我三人任副会长。会议结束后,好些著名报刊发表了纪要和侧记,许多报刊纷纷发表美学论文进行争论。
马国川:这次会议对“美学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一位学者曾经回忆说,1980年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召开之际,他正在四川某大学读书。当时一些著名美学家应邀顺道来校讲学,“千人大厅坐无虚席,直至饱和,群情振奋,如春潮涌动”。
李泽厚:1980年后,“美学热”进入高潮。到1981年,新时期的重要美学著作已大部分出齐,如朱光潜的《谈美书简》、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和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等等。
“一部死的历史,你讲活了”
马国川:还有你的《美的历程》,也是1981年出版的,那是你的名作。
李泽厚:这本书我是在1979年交稿的。写作的过程很快,大概只有几个月。可思考的时间长。如“伤感文学到红楼梦”50年代就已经有了。盛唐的思考是60年代,那时我下放到湖北干校,在农田劳动,忽然间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浮现脑际。当时《春江花月夜》是被严厉批判的,认为是颓废文学,可是我觉得它是成熟期的青少年对人生、宇宙最初觉醒的“自我意识”,是通向“盛唐之音”的走道。“青铜饕餮”是七十年代写的。
马国川:厚积薄发。
李泽厚:根据许多年断断续续的思考,许多年陆陆续续写下的笔记,所以短时间就完成了书稿。
马国川:写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
李泽厚:在很长时间里,大部分的论著把很活泼的文艺创作僵化成了死板的东西,许多文学史与艺术史把文艺创作割碎了。我认为不管是艺术、文学还是美学,都离不开人的命运,也离不开历史;更不满足于当时“僵化”的、被割裂得七零八碎的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美的历程》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动笔完成的。
马国川:是不是可以说,《美的历程》是伤时忧世之作?你的许多著作都隐约透露出学术研究背后对时代和对国家的关怀,《美的历程》结尾的最后一句说:“俱往已,然而,美的历程是指向未来的。”
李泽厚:我不写五十年以前可写的东西,也不写五十年以后可写的东西。心中暗想着钱钟书的著作学问,他的著作也许永垂不朽,但我只为我的时代而写。《美的历程》起先以《关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札记》为题,1980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美学》第二期上发表了前三章。次年3月,该书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
马国川:该书十年之内印了八次,后来又有了多种版本,无疑是学术著作中最畅销的。它没有采取体系性的美学研究方法,而是在理性研究中流露浓厚的诗情,堪称一部打开了的心灵史,使人们直接感触到中华民族的心灵历史,感染了一代读者。连冯友兰老先生都称赞它是对中国美学、中国文学,以至于中国哲学最精练浓缩的概括,“一部死的历史,你讲活了”。
李泽厚: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繁琐的东西,比较注意书籍、文章中的新看法、新发现,比较注意科学上的争辩讨论。我主张写文章不要人云亦云,而要力求新鲜,不管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美的历程》确实说不清该算什么著作,专论?通史?散文?札记?都是,又都不是。1981年我发表文章《走我自己的路》后,一位领导紧张兮兮地跑到我家里对我妻子说:“怎么能用这种标题?这还了得?”
马国川:“走我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句话还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格言,到处出现,好象谁不说谁不够“品位”。
李泽厚:重要的还是要有思想。我的书希望给人启发,它不是教材,只是发表自己一些不同于流行看法的意见。
马国川:《美的历程》对中国古代文艺史做了一番“艺术社会学”的考察,阐明了“人性”与“审美心理”的一致性,宏扬人性。所以《美的历程》和朦胧诗一起,起到了一种“启蒙”的作用。有人甚至宣称以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为代表的一拨人是“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
李泽厚:这话说“过”了。我不是狂妄的人,但也不是谦谦君子,我确实影响了许多青年人。80年代很多人称呼我“导师”“精神领袖”,对于这些,老实讲,我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从小就听到过很多过奖之辞,所以听到这些也没有如何飘飘然。我在单位里的待遇也并没有因为这些有了什么好的改变,相反,有很多人一直攻击我,到今天也仍然如此。对于这我倒习惯了。
马国川:那时你确实像一个“青年导师”,一次你去北京大学哲学系座谈,然后在学校食堂就餐。结果万人空巷,食堂里的长方桌旁围绕着你的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学生。
李泽厚:特殊时代啊。在那时,中国的公共生活还没有“超女”之类的娱乐明星,生活单调,而且刚刚解冻的人们对现实、未来充满了探索的激情。每个学生都是问题青年,都洋溢着一种青春的气味和对思想的渴望。粗朴而贫乏的物质生活反而更容易催生一种精神的追求。
马国川:易中天说,《美的历程》让他们这一代学人明白了,原来学问还可以这样做,甚至就该这么做。比方说,讲哲学,可以并不一定要套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讲文艺,也不一定要套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别。
李泽厚:在此之前,这种套路是金科玉律不能违背的。
马国川:更重要的是,许多人从你的书里领悟到,一个人文学者,就应该把学术研究和人生体验结合起来,把历史的遗产当作鲜活的对象,把做学问、写文章、出版著作变成自己生命的流程。你用自己成功的实践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李泽厚: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人做与人生无关的学问也很好。但我一直主张,青年人与其做半吊子的学者,就不如去做生意、做企业家,或者做别的。当然做那些也不容易。至于我的书,我当年就说过,主要是为青年人服务,不过我写作时没有想过怎样迎合青年人。我只希望找到一些时代所需要的、应该有的东西,能够抓住一些客观的、有价值的东西。我相信,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不会被埋没的。其实,我一直认为后来出版的《美学四讲》《华夏美学》在学理上更重要。
马国川:但很多人不认同这个判断。《美的历程》的出版是第二次美学热的标志性事件,着着实实地给美学热添了一把火,使得美学热更“热”了。但是从学术的角度考察,任何“热”必然地包含着肤浅、赶时髦、凑热闹、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立异以为高。美学热恐怕也不例外。
李泽厚:我在1985年就提醒人们,美学热毕竟并非好事,已经把某些人热昏了头,美学热在学术界乃至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了严重的俗滥倾向,什么“爱情美学”“军事美学”“新闻美学”等等都出来了。所以从这时起,美学热就出现了退潮的趋势。
马国川:第二次“美学热”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除了普及了美学这个概念及一些美学观念之外,主要还在于它承担了美学之外的职能。
李泽厚:总起来说,美学充当了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翼,或者说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思想启蒙没有满足于对历史悲剧的简单清算,而是向着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深处挖掘,结果形成了“文化热”。
“文化热”
马国川:“美学热”过后,继之而起的是“文化热”,这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李泽厚:如果从广义上说,文化热里头也包括了美学热,或者说美学热是文化热的前奏或一部分。
马国川:80年代中期,政治氛围相对宽松,到处洋溢着启蒙和人本主义的活跃气息。知识分子受到民众的支持。同时,先锋文学和新潮美术、先锋音乐密集出现。这期间产生了三个大的民间文化机构:以金观涛为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甘阳、王焱、苏国勋、赵越胜、周国平等为主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等为主力的“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你也是中国文化书院的主力。这三大文化机构的成立,可以说是“文化热”的标志。
李泽厚:我和三个文化机构都有联系,但都未深入参与。既是“中国文化书院”的成员,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文化:中国与世界》创刊前和我讨论过,这个名字还是我最后和他们确定的,但我没参加他们的活动。
马国川:其实,你对文化的关注很早。你在《美的历程》等书中提出的许多概念,包括 “儒道互补”“魏晋风度”“建立新感性”“审美积淀”等美学话题已经是超越了美学的文化思考。更早之前,1979年你出版的另一本书《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其中的许多话题也都涉及到了文化。
李泽厚:在50年代我发表了《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研究》等文章,《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汇总了50年代和70年代末两个时期的有关文章,做了统一修改。《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批判哲学的批判》和稍后出版的《美的历程》三本书,全讲的是过去,起点却出于对现实的思考,所谈的问题都或多或少与现实有关联。
马国川:《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后记”说得很明白:“之所以应该重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正是在于中国近百年来的许多规律、因素、传统、力量等等,直到今天还在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这本书里就提出了许多很重要的命题。你1980年发表的《孔子再评价》一文,提出了“文化-心理结构”的概念,你说孔子学说为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奠定了基础。
李泽厚:我主要的力量是研究中国思想史,试图改变一下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史陈陈相因的面貌。几十年来,哲学史只是简单地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我想打破这种格局,所以我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等角度进行研究。当时在长期的闭关自守之后,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和各民族大接触大交流。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学者应该反省一下自身的文化和心理,对本民族的文化有一个清醒的自我意识,减少盲目性。
马国川:1985年你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这本书在文化热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李泽厚:这部思想史论也是学术性的,着眼于古代历史上各种思想、学派、传统的根源、特质和影响。当时,在文学界,“寻根”、“认同”的问题讨论得热火朝天,在哲学界文化界,关于传统文化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而我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试图从今天中国的角度反思自身的历史和文化。
马国川:但是这种努力却遭到了许多误解。因为它与此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似乎有所不同,所以有一些人认为你接受了新儒家的影响,甚至背叛了自己。
李泽厚:我完全不接受港台新儒家。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始终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不加分析地采取骂倒式的批判,另一种是在文化认同的口号下鼓吹复古主义。对两者我都明确反对。所以有许多人骂我。记得在八十年代前期,刚刚觉醒人们的强烈要求从政治重压和旧有秩序中解脱出来,但社会思想还很沉闷很保守。一次我去开会,专家学者一律蓝灰毛服,只有我穿一件不同颜色的夹克,许多人侧目而视,甚至是怒目而视。当然和我比起来,青年人处境更艰难、压抑、苦恼。那时候人们都说这一代没有希望, 是报废的一代。我到处与人争论,我在1978年就说,希望在年轻人身上,不在老一代身上,但是许多人不同意,包括外国学者也包括我这一代人。我写文章为青年辩护,后来收录在《走自己的路》中的许多短文目标都集中在反对旧势力、旧标准、旧规范上,就是为青年人呐喊鼓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