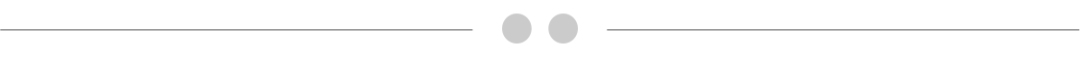《Legal High2》
我们的生活由很多隐形的事物维系着。法律是其中一种,即便大部分人并不了解法律,但所有人的生活都以法律为基底运行着。
拿结婚来说,它是拍红底照、登记领证、买房、办婚礼,但这套仪式的背后,是婚姻家庭法的管理。在文化层面上,结婚或许值得庆祝,但褪去文化脚本的包装后,结婚意味着进入一个制度,人们受它保护也受它约束。
以婚姻制度为起始话题,我们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法学研究者翟志勇进行了一次对话,除了婚姻还谈及取消文化、法律的有限性。
一个贯穿对话的线索是,法律由不完美的人类设计,注定是不完美的。比如它有冗杂的程序,比如它无法立竿见影地解决具体问题,但法律依旧是维系现代生活的重要工具。混沌发生时,我们需要一套秩序来厘清方向。或许,在放下对法律的过高期待后,它能为我们提供更务实的视角。
1.
“婚姻的最高承诺是爱情”
看理想:在您的音频节目《正义的实现:法律系统40讲》中,听众对婚姻相关的法律比较感兴趣,某种程度上说明大家希望更理性地对待婚姻。您如何看待类似“婚姻不是爱情的最高承诺,只是一种契约”这样的说法?
翟志勇:我认可这句话,但我认为这句话更好的表述应该是:“婚姻的最高承诺是爱情,最低承诺是契约”,婚姻可以没有爱情,但不能没有契约。我这么说,跟法律看待人性的方式有关。
整个法律制度的设计,有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怎么看待人性。你认为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会决定你如何设计法律制度。
事实上,法律是“以人性恶作为预设,以人性善作为预期”的。婚姻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体现,如果一切都能靠爱情解决,就不用婚姻法了。制定婚姻法的重要考虑就是,爱情不管用时,还有婚姻法兜底,所以婚姻法的很多制度设计其实是为离婚做准备。
个体可以一冲动不顾后果地结婚,但法律必须考虑冲动的后果,如果离婚了,大概率会涉及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因此就要提前考虑这些问题的制度设计。当然,法律还是希望大家的婚姻能长久,所以婚姻法虽然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但还是会鼓励双方相互忠诚、相互扶助的。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进入婚姻后你做不到期待没问题,但你得完成最低限度的一些要求。因此,我才说爱情是婚姻的最高承诺。
《婚姻生活》
看理想:那么婚姻作为一种制度,在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分别意味着什么呢?
翟志勇:婚姻法一方面完全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另一方面也会从社会层面出发做一些设计。
先说个人,现在的婚姻法完全贯彻婚姻自由,就是你愿意结就结,愿意结婚就适用这个制度,你不愿意结婚,制度也不会干预你。至于来自家庭的干预,比如催婚,那是另外的问题,法律也不会管。但如果是父母强制干预,法律就会保护当事人的婚姻自由权,父母也不得强制干预。
从社会层面上讲,你结了婚,选择了这个制度,它作为一项社会制度还是会有一些考量和安排的。结婚后可能会有孩子,一旦涉及到孩子,就不再是两个人的问题了,必然会有一些强制性的社会规范,比如履行父母的责任,而离婚时对于子女抚养,法律也有一些要求。另外,基于对家庭中弱势一方的保护,法律禁止夫妻之间的虐待,禁止家庭暴力,要求双方有相互扶助的义务等。
婚姻法为了保障家庭的稳定性,会有强制性和禁止性的规定。但从整个制度设计的倾向来讲,法律还是鼓励大家去结婚的,所以往往会给结婚的群体某些特殊优待。
看理想:法律为什么要鼓励大家结婚?
翟志勇:一方面,社会制度的设计一定是希望人类能延续下去,至少目前来看,自然生育是人类延续的必须,所以法律鼓励大家结婚生育。
另一方面,人是社会性动物,必然会处在各种社会团体或社会关系里,法律会对这些关系提供保护。而所有社会关系里,家庭是最基础的,对于社会稳定有最重要的作用,因此所有社会都会把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单元来优先考虑。我们的《民法典》中有“婚姻家庭篇”,不仅仅强调婚姻,也强调家庭。如果婚姻状态是稳定的,家庭是稳定的,有助于良善社会的建立。
《母亲》
看理想:既然生育是人类延续的必须,您觉得我们的法律有在考虑单身生育的可能性吗?
翟志勇:我们的法律有在考虑这方面的事情,包括两会中有一些人大代表提案,卫健委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总体上来讲,我们的法律在婚姻家庭问题上是相对保守的,其他东亚国家在这些问题中也是相对保守的,这当然跟传统文化有关系。
我个人的意见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会越来越个人化,人总是会希望自己做一些选择,那婚姻、家庭、生育问题,就是整个社会个体化的最后几个堡垒。我们其实在很多方面已经完全尊重个人的选择了,但在婚姻家庭方面还是对个人选择有很多限制。
不过随着生育技术的完善和成熟,我们能看到在全球范围内,单身女性的冻卵会慢慢地放开。中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但需要在技术和制度更完善之后,我们才能最终放开。我认为未来仍然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看理想:在国外,一些性少数群体在争取结婚的权利,但同时,也有其他群体在争取不结婚也能和伴侣建立受法律保护的生活的权利。这之间有矛盾吗?为什么法律还是会强调用婚姻去证明或承认各种关系呢?
翟志勇:性少数群体争取结婚的权利,首先是为了承认。在这个群体看来,婚姻法不让这个群体结婚,就构成了一种歧视,所以这首先是为了承认而做的斗争,涉及尊严问题。此外,也会涉及到利益,很多国家在税收上对家庭有特殊的优惠,没有结婚的人是享受不到的。
关于法律为什么要用婚姻制度来承认男女之间的这种关系,因为法律上的婚姻关系涉及到诸多其他的法律关系。
拿我们自己的法律来说,我们是不承认事实婚姻的。任何法律制度,一旦确立了,它的影响是系统性的。如果我们承认事实婚姻,就会涉及到如何证明两个人的夫妻关系。在一些人眼里,你们可能是夫妻,但在另一些人眼里不一定。
甚至我们也不排除有人同时和多个人在一起的可能性,那该如何认定彼此之间的婚姻关系呢?而婚姻关系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债务乃至子女抚养等一系列问题,事实婚姻会使整个法律变得异常复杂。
大家如果想接受婚姻制度的保护,可以选择结婚,如果不想受到它的限制,可以选择不结。保护会带来束缚,最终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2.
法律管不了所有事,
所以需要一些社会空间去自我解决
看理想:某些时候,婚姻会成为犯罪的遮羞布,比如在婚姻内,一方对另一方实施了暴力,外界看待这个问题时很容易将事情弱化、缩小。法律会怎么处理私人领域的冲突?
翟志勇:从法律制度的设计上来说,家庭暴力是法律明令禁止的。现在的《反家庭暴力法》里有“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如果你面临家暴的风险,可以向法院申请这个保护令,来防止家暴发生,这是一个事先的救济。我们过去都是事后救济,也就是在家暴发生后才去救济,现在至少有事前救济的途径。《妇女权益保障法》甚至将“人身安全保护令”扩展到恋爱关系及恋爱关系终止后一方对另一方的伤害。
但为什么家暴还是很难解决?一方面,家庭是一个很私密的空间,法律通常不会主动介入家庭关系中,法律甚至还会保护家庭关系的隐私性,比如你不能随便去别人家里打探或窥探,所以对于发生在私密空间里的事,法律处于一种“你不来找我,我也不去找你”的状态。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去寻求法律救济,法律只能任由你自己处理,除非发生了刑事上的伤害事件。这是第一个问题,法律需要尊重家庭关系的隐私性和自主性。
《婚姻生活》
第二个问题在于举证。硬暴力可能相对好举证,但一些家暴是软暴力,没有肉眼可见的伤害,举证会困难一点。另外,很难要求家暴受害者有保存证据的意识,因为伤害发生时更多是非常伤心。但是刑法有无罪推定和罪行法定的原则,法官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完全基于同情来定罪量刑。
我们当然不能去怪罪受害方,因为有时救济手段并没有那么好用。这需要法律的制度设计尽可能去完善,比如说妇联组织、受害人所在的街道或所在单位,都有义务去帮助家暴受害者。但整个保护机制的启动还是取决于受害者。
看理想:您谈到法律的救济手段有时并不好用,我们最近能观察到一种现象,就是一些人在受到侵害后发现法律程序实在是太难走了,因此转向网络进行曝光。虽然得到的结果不会被法律承认,但这会是很多受害者选择的路径。
翟志勇:确实,法律制度比较讲程序,有一定的标准和条件,所以寻求法律帮助会有门槛。回到法律本身,立法者在设计制度时,当然是为了保护受害者,但同时也要考虑诬告的可能性,因此法律会讲证据讲程序,这样做的代价就是,一些受害者可能因为寻求法律救济成本过高而放弃。
所以也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选择网络曝光,因为这是成本最低的方式。近年来出现的“取消文化”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社会中的一些弱势群体的权益没办法通过法律来维护,因此只能以一种社会运动的方式来解决。
《黑暗荣耀》
“取消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审判或私力救济。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当然希望利用各种机制来为弱势群体提供救济,但社会中一定会有一些伤害是法律没办法触及的,这些领域就只能依靠自我救济或社会救济,统称为私力救济。
法律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只要你在私力救济的过程中没有违法行为,法律就不管。这个社会必须留有一定的空间,让社会自己解决一些问题。法律不能管所有事情,它没有这个能力,也不适合。但很残酷的是,如果私力救济超过了必要的限度,违法了,法律还是要管的。
3.
每个人心中的正义都不同,法律怎么办?
看理想:在不同的案例上,不同人对处罚结果有不同的期待,比如中国民间就有种说法是“杀人偿命”、“以牙还牙”。法律自然不会去满足个体的想法,那么想问问,法律在衡量处罚时会看重什么呢?是否可以谈一些宽泛的标准?
翟志勇:民事和刑事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举个例子,在民事案件里,我们法律的基本赔偿原则是赔偿对方的实际损失。我们国家的法律里是没有惩罚性赔偿的,但美国有,之前有些比较特殊的案子,像一个人买咖啡被烫伤,获得了几千万的赔偿,这就是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的目的不是说这个人的烫伤值几千万,而是督促商家提供更安全的产品。它追求一种社会效应,而不是针对受害者的公平救济。
在刑事领域里,量刑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刑法中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处罚,是对过去的行为的惩罚,还是对未来犯罪的预防?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再比如现在会讨论死刑是不是一个好的惩罚措施,很多国家废除死刑的原因在于,它起不到预防或震慑的作用,外加一些宗教文化的因素,所以会反对。
从过往的学术研究和各国的情况来看,并不是所有犯罪都能用重刑解决。所以如果要用重刑,就需要搞清楚效果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但这个问题更多是犯罪学问题,是一个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学问。
任何一个社会中,犯罪都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为刑法中的处罚而消除掉犯罪。比如很多人因为贫穷而犯罪,那解决方式不应该是处以重罚,而是解决贫穷。提高刑事处罚只是降低犯罪率的可选项之一,还需要去评估这个选项是否能达到预期目的。
看理想:所以是否可以说,法律在衡量处罚时,相对而言更看重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而不是具体的受害方的感受?
翟志勇:对的,在我们的刑事诉讼里,受害者并不是诉讼中的一方,刑事诉讼里是国家来追究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受害人满不满意不是刑法要考虑的。
在刑事案件里,犯罪嫌疑人侵害了另一个人的生命,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是对法律秩序的公然挑战,处罚不仅是因为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更重要的是他挑战了国家的权威,因此才由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
《毒舌律师》
看理想:学习法律后,您看世界的视角有发生任何转变吗?
翟志勇:我在《法律通识》这档音频节目里就讲,法律本身不是正义,法律是实现正义的一套机制,而法律为了实现正义,它的机制设计需要特别复杂。
我们中国人喜欢包青天,因为他有求必应,有冤必帮你解决。但真实的法官不是包青天,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设计各种复杂的机制,来做出相对公平的审判,来实现正义。所以为什么司法过程那么复杂,因为它不相信任何一个人,不能把最终结果寄托在任何人身上。
每个人追求的正义,只能在法律程序机制里一步一步去实现,最终可能如你所愿,也可能不如你所愿。
但我们没办法,要通过法律来实现正义就是这样的。这是人类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慢慢吸取的教训,逐步演化出的一套程序机制,它对正义的实现肯定达不到100分,但它可能达到80分,或者至少能及格。
看理想:您有没有过在法律系统面前感到特别无力的时刻?能否谈谈具体的事例,以及您是如何应对这种无力感的?
翟志勇:无力的感觉会有,但特别无力不太会有,主要是因为我熟悉这套法律系统,我知道很多事情不是法律能够解决的,所以我对它没有抱过高的期待。
举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一回我在马路上走,突然有人对着我拍照,对方解释说他在拍风景,只不过我出现在风景里,但他确实把我拍进去了,我不清楚他的目的,但他侵害了我的肖像权,侵犯了我的人格利益。
这时我对他提出了抗议,他说那你报警好了,让警察来处理。我知道报警后会跟他一起去派出所做笔录,我最终能获得的,可能就是让对方把照片删除。当然也有可能这张照片删不掉,已经被对方发出去了。我能判断,通过法律来维护我被侵犯的权益需要付出的成本是什么,能够达到怎样的效果,但这个效果不是立竿见影的。
《毒舌律师》
很多时候,你会感受到法律给了你一个选择,但它不能立刻解决你的问题。虽然会感到无力,但我不会因此对法律失去信心。原因是我清楚法律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这样,它无法对所有伤害提供100%的救济,但我们仍然需要它,因为社会中绝大多数侵害还是需要靠法律解决。
我们不能因为法律没考100分,就对法律失去信心,因为这个制度就不可能总是考100分,我们要做的让它尽可能考80分、90分,与此同时接受它考不了100分。
这是对法律的一个客观认知,既不能把它拔得特别高,把它直接等同于正义,也不能把它贬低得一无是处。我们要客观地看待法律的能与不能,法律只能在它恰当的位置上,为我们提供保护,我们也只能以恰当的方式来接受法律给我们提供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