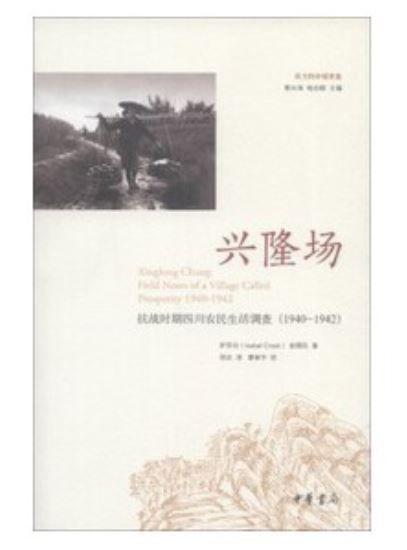
《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加]伊莎白(Isabel Brown)、俞锡玑著,邵达译,中华书局2013年1月出版,416页,66.00元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借马可之口表达了自己对异域的看法:别的地方是一块反面的镜子。旅行者能够看到自己拥有的是何等的少,而他所未曾拥有的、永不会拥有的是何等的多。当年轻的社会活动家伊莎白(Isabel Crook)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离开加拿大前往兴隆场参加乡村建设实验时,她一定会认同这句箴言的前半部分:兴隆场如镜子一般反射出四川乃至整个中国在抗战时期的农村风习,呈现图景与人们的普遍认知相去甚远。而对于出身小康之家、生活情调丰富的年轻学者来说,她能够在兴隆场看到的,是当地人拥有的一切远少于她的想象,不然她也不会作如此开篇:
大多数日子里,兴隆场——一个仅有八十二户人家的小集镇,看上去平淡无奇、缺乏生气,似乎恰是农村单调生活的缩影。
兴隆场周围数里以内,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村落,百分之九十的人家都居住在简陋的土坯屋里,绝大部分农民挣扎在贫困线上,大约三分之一入不敷出,另有一半勉强糊口。人们的衣服色彩单调,买不起夹衣的穷人要为过冬犯愁。人们的饮食单调,随着物价的上涨,穷人们会加大主食里蚕豆的比例,没有油,就用水煮干菜下饭。伊莎白等人无法咽下煮老的蚕豆皮而将其丢弃,这被邻居认为是浪费粮食的做法,多次加以批评。
与“洋学生”在价值观上有龃龉是自然的,对乡民来说,这位身穿白衬衣黑套裙、披着米色外套的外国女人虽然与兴隆场格格不入,但也不失为一道美丽的风景,只要她不惹什么乱子就好。但注意到当地妇女处境的伊莎白总因同情心和责任感的驱使,试图去做点什么。加入孙恩三的乡村建设实验工作组后,她的主要任务是协助调查全乡一千五百户居民的经济生活状况,鼓励缠过脚的年轻妇女读书,劝得病的乡民到西医诊所就诊,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为改变当地吃盐困难的问题,伊莎白和同伴俞锡玑还试图创建食盐合作社,触动了当地哥老会和大盐商的利益,很快便败下阵来,乡村建设计划也随之名存实亡。
虽然实业没有成功,但伊莎白的深入调研积累了一份宝贵的战时农村资料,完成了这本著作,为后人近距离观察战时中国的乡土社会提供了窗口。沉浸在作者的娓娓道来中,你可以感受到许多历史学家试图揭露的“真实的中国”,经典如费孝通的“熟人社会”“差序格局”,近有王笛新书《碌碌有为》从微观视角展露的市民风习,以及近代社会组织的巨大转折给战时农村带来的深层褶皱。
一、兵荒马乱的贫穷
对于兴隆场的贫瘠,伊莎白首先将其归于地理因素,一是绵延的低山丘陵使得可耕种的农田支离破碎,其次是灌溉水源的不足,最为重要的春雨也常常缺席。在引入新稻种和梯田垦殖技术后,生产力有所提升,但没有带来普遍的改善,贫富分化的金字塔结构逐渐形成。伊莎白调查了一千四百九十七户居民,其中拥有六十石稻田的大地主有十二户,与一百三十六户中小地主、有地商人构成了金字塔的上层;中小农户及手工业者可以混个温饱的有五百四十七户,占比百分之三十五;最为穷困潦倒的无地佃农、赤贫自耕农是数量最多的一个群体,共有八百零二户,占比百分之五十五。
对占比百分之九十的“下等人”,伊莎白有个极为精彩的比喻:他们的命运就像露在外面的衣服袖口和裤脚,最先被岁月磨破。那些原本就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农民,在灾祸面前显得尤为弱不禁风,轻轻一击,整个家庭就会瞬间瓦解。
不幸的是,这样的灾祸实在是太频繁普遍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特别是抗战军兴,即使兴隆场并不在漩涡的中心,但战争与变乱总会如涟漪一般荡来,从深处搅动着这个集镇的根基,引发权力格局的嬗变和民众命运的颠沛。比较典型的,例如征兵问题,一个青壮劳力的离开可能造成一个家庭经济状况的失衡,连续被抓壮丁甚至会导致宗族的衰败,那么负责征兵的乡绅、保长就拥有了一项生杀予夺的大权。当然他们也还要对上负责,努力凑够指标人数,否则也可能遭遇牢狱之灾,先前从乡民身上搜刮的油水也得吐出来。
四十年代的兴隆场梯田
袍哥冯庆云便是如此发迹的。他通过经营茶馆积累了人脉,投靠义兴社做大了生意,在担任乡长的六年时间里,田产从二十石猛增至一百石成为本地头号地主,多半是借征兵之机敲人竹杠。按理说兵役法关于征兵年龄和免于服役条件的规定是明确的,但执行人依然有巨大的发挥空间,使得本应成为征兵大户的、有钱有势的大家庭逃脱兵役,将指标落在最穷、最落魄、最无助的那些人身上。伊莎白就亲眼目睹了这样一次征兵:
八名壮丁——有几个被五花大绑——在荷枪实弹团丁的押送下,准备去璧山报到。有个背上背着娃娃的女人放声大哭,双手扯住队伍里丈夫的胳膊,旁边没人管的年仅四岁的女儿则一脸茫然仰头望着父母,显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一个老妇人绝望地搂着儿子。一名壮丁默默站着,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脑袋被脖颈上的一颗大痦子顶得歪向一侧。另一人骂骂咧咧直呼倒霉,因为这次征兵仅三个保有份,结果就摊上了自己。一名团丁回应道:“傻瓜,怪就怪你生错了地方,这年头中国人没有不倒霉的!”
如此私人化的表述和“壮士出川”的历史记忆似乎是大相径庭的,在后一种语境中,川省在抗战初期进行了慷慨盛大的宣传,三百万将士在父辈“国难当头、匹夫有分”的教诲下奔赴前线,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事实上,宏大叙事总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肉情感细密缀成的,民众对抗战的支持和对兵役的抗拒并不是一个悖论。据徐乃力、侯坤宏等人研究,中国军队的平均死伤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三,平均四人上战场便有一人非死即伤。尤其是战争初期,中国军队的死伤率比日军高出十倍,到了战争后期也高出三倍,如此高的风险自然使多数民众视从军为畏途。
倘若能做到公平行事,中国人是可以慷慨赴死的,而将征兵也变成一种剥削,无人心服口服。不公平存在于兴隆场事务的方方面面,富人和穷人、乡绅和乡民、男人和女人之间显著的不平等,起源于人的逐利本能,为资源流动提供了势能,但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后就阻滞了进步。
二、匪与兵:互通的两级
要解释这一点,土匪问题是很好的切入口。在兴隆场落草为寇的无非两种人,一种是吃不上饭铤而走险的穷人,还有就是逃避兵役的青壮年。伊莎白敏锐地注意到,这些土匪并不符合文人们惯常描述的“劫富济贫”形象,他们抢劫的目标没有大地主,而是属于中间阶层、靠经营副业赢利的乡民——例如卖完猪回家,兜里揣这一把现钱的养猪户,或有一两架现代织机,刚购入一批面纱或刚织完几匹棉布的纺织户。他们有现钱且毫无自保能力,从逻辑上讲确实是土匪最好的猎物。
但他们又是什么人?如上文所提到的,他们恰是那个最经不起灾祸冲击的群体,被土匪洗劫一次,就容易沦落成无以为生计的穷人。所以这个过程冥冥中似有循环:受到冲击——落草为寇——掠夺他人——逼良为匪。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底层互害,伤不到金字塔顶端的老爷们分毫,但后者才是灾祸的始作俑者,正是他们用苛捐杂税和土地兼并将底层财富蚕食到濒临崩溃的程度。伊莎白指出,地主除了心安理得享用佃农贡献的租子(全年收成的三分之二)外,还把贮存粮发霉、虫蛀鼠咬的耗损都转嫁到对方头上。契据里还暗含各种不成文条款,要求佃户为地主无偿提供各种服务,比如抬滑竿、代买东西、修缮房屋、看家护院等,事实上使佃农成了地主的附庸,很难挣脱这种依附关系而独立。
这种循环也显示出了“熟人社会”的特质,即所有人的生活轨迹都有交集,彼此命运交错。土匪即使脱离了原来的环境,还依然熟谙其规则并通过收集信息取利,他们知道谁家大约有多少财产,有多少雇工和劳力,有无自卫手段,与当地官员的关系是否密切等等。例如大地主曹跃显和蔡云清固然富得流油,却永远不会被列入他们劫掠的清单上,因为他们有人有枪,家里有多层的塔楼,视野开阔,军事化设计,完全可以抵御土匪的进攻,惹上这些地头蛇是极不划算的。
林耀华的《金翼》便讲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一群中学生被土匪劫持以后,他们试图隐藏自己本地人的身份,但被土匪轻易识破了。经过调查,土匪还逐个说出了他们的身世,谁是湖口店主的儿子,谁是县参议的儿子等等。县参议雷吾云得知儿子西文被抓后,立刻派人来谈判,土匪释放了西文并表达歉意,因为雷吾云在地方衙门有影响,完全可能找他们的麻烦。原本凶神恶煞的土匪笑着对西文说,为什么第一天不说自己是雷参议员的儿子呢,说了就不会亏待他了。
兵是合法的匪,匪是非法的兵,从暴力攫取利益的角度来说,兴隆场头面人物的本质与土匪并无不同。连年的军阀混战提供了一条非正常的阶层跃升途径,蔡云清就是混迹在军阀队伍里获得了权力。面对驻地29军士兵的扰民,只有“蔡旅长”带头出面斡旋,才有可能维护乡民利益。当中日空军在璧山空战后,中国飞机摔落在兴隆场的田野上,也是靠蔡旅长赶到现场组织指挥救援,将伤员送至璧山医院,并自掏腰包付滑竿费和医药费。这样的行为当然是受到称颂的,但蔡云清绝非善类。他开在镇上的茶馆每日都有赌局,靠抽利日进斗金,并与鸦片商人勾搭,这些行为实质上都是对本不富裕的乡民敲骨吸髓。
三、国家权力的介入
总而言之,抗战初期中国农村这种以乡绅豪强主导的社会格局是反现代化的,它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对官方权力下探汲取资源形成了极大的障碍。国民政府内迁后,决心集全国之人力物力以持续抗战,就要在大后方进行一定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造,势必要开始新一轮的权力重组和利益分配。
1940年7月1日,基层政治区划启动改革,兴隆、大鹏两个相邻的联保合并为大兴乡。这项举措的名义是精简机构、减少开支,实际上的效果是大大削弱了各乡保长手中的权力,而且辖境重新进行了划分,使得以往以宗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也随之被打破。手握人事权的县长委派大量外地人当乡长,代理本地精英的胥吏被扬弃,两方的明争暗斗颇为激烈。首任大兴乡长的唐恭义只干了七个月,期间被蔡旅长多次找茬,借口征粮办法不公告到县衙,最终被调出本乡。
第二任乡长唐友谭的日子也不好过,蔡旅长不但攻击其治匪无方,还唆使乡民联名指控乡长以权谋私。1941年3月,唐乡长在与驻军的冲突中落了下风,被关进重庆的军事监狱后花了两千元保释,回来后便立即卷款离职。任职时间最长的郭安康可谓深谙人情世故,上任后即去茶馆拜码头,自掏腰包请蔡旅长等头面人物吃饭,但最终也是无所作为,其关于禁烟、禁赌、反腐的种种措施均告失败。
以禁赌为例,1941年夏,郭乡长召集本地士绅开会,督促他们兑现捐款助学的承诺。蔡旅长首先发难,主动表示将拿出部分赌场收入作为修缮学校的费用,郭乡长顿时进退两难。如果应承下来,就等于承认赌博合法,此前严格执行的禁赌措施就显得区别对待;如果拒绝,那就是和蔡旅长撕破脸,以后的工作更加难办,于是此事便不了了之。
更为复杂的是战时军粮的征收问题。在国民政府介入前,地主冯庆云主管收税和义仓,其核定税额自有一套标准,又因人而异,无权无势的小自耕农最为吃亏。为平均税收,政府重新丈量登记土地,但兴隆场的测量规则极其复杂。因为地势崎岖、土地形状极不规则,当地人遵行一套按产量计算面积的方法,计量标准(旧石、新石、市石)和土地类型(山田、梯田、旱田)混杂使用,形成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外人包括外来的官员难以摸清门道。这就类似于王安石变法的基层遭遇,执行标准过于严格明确就会造成“一刀切”的不公和过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则要耗费大量人力,迁延多时却收效甚微。
对于自己1940年至1941年在兴隆场的经历,伊莎白认为是一个现代化改革浪潮席卷而来又盛极而衰的过程,他们撤离时的心情是失落的。但伊莎白并未中断对中国的热爱和研究,1947年她与丈夫大卫·柯鲁克穿越封锁来到解放区,以河北省武安市石洞乡的十里店为样本进行土地改革研究,并完成了以之命名的著作。1948年,柯鲁克夫妇到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前身)任教,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英语高等教育教材,培养出新中国首批外事干部。在北外躬耕七十余载后,2023年8月20日,一百零八岁的伊莎白在北京辞世。
伊莎白在家中与年轻时照片合影
兴隆场后来的权力斗争主要在冯庆云和孙氏兄弟之间进行,抗战胜利后,当地豪强在反共与亲共之间抉择不定。蔡云清在袍哥好友的劝说下避居璧山,孙宗禄拒绝了冯庆云合作反共的要求,也离开了兴隆场。冯庆云则继续盘剥乡民,解放后投靠地主武装负隅顽抗,很快便被镇压,作为反革命匪首被枪决。至此旧的权力体系土崩瓦解,兴隆场走上了中共土地改革和行政改制的正途,新时代开始了。
四、余记
镇上有两户做香的人家,每家男人的工作就是去屋后竹林里砍竹子,然后削成长短一样的竹条。妇女负责把木炭灰调成糊,均匀涂抹到竹条上(这时小孩也会插手),再送去别人那里敷一层散发香味的药粉,木炭和药草集市上都有出售。这两家人一天能做大约三千根香,即便全卖掉,顶多也就挣四五块钱。
这是伊莎白描述的一段副业生产情况,如此细致鲜活的生活场景在书中比比皆是,令人印象深刻。透过这些纷繁的人间烟火,读者可以感受到系于生计的喜怒哀乐,体察出苦涩的时代况味:在极不稳定的战时农村,平民的百般挣扎也难以完成财富的积累,因此便无法形成足够力量的中间阶层。缺少一个安居乐业的群体,底层社会和上层权贵之间就没有缓冲地带,只有无休止的盘剥蹂躏。当矛盾和仇恨不可调和时,赶上权力格局变化的风潮,社会革命便会异常暴烈。
国民政府的权力下探乡村,在行政、教育、医疗等方面进行现代化改造,重拾保甲制强化控制,也可以看作是社会企稳的一种方式。但在资源匮乏(包括人力资源)的条件下,政府不得不借助“劣化”精英来进行改革,而后者则依靠公职身份扩充自身权力、追求不当利益,使得地方的政治秩序依旧紊乱。有学者认为,“兴隆场困境”反映出国民政府改革中的固有缺陷,即权力下移的党国体制过于理想化,在汲取资源的过程中必然导致地方社会的抗拒。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今天,如何在基层执行国家权力,需要进行何种程度和方式的干预,仍然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兴隆场》依然有常看常新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