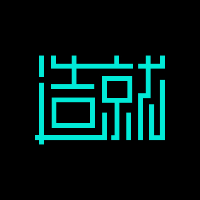" 傅踢踢,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了七年新闻,曾在《南方都市报》、新华社上海分社和《解放日报》实习,毕业之后在《文汇报》的国际新闻部、经济部和文化部先后担任编辑、记者和文化评论员的工作,在多家媒体平台上开通了自己的专栏,拥有自己的个人微信公众号。2016年7月,傅踢踢从《文汇报》辞职,选择做一名作家、编剧。已经出版了《越孤独越自由》。 "
怎么看待才华这件事?
我觉得首先每个人都有才华,才华这件事情其实是天赋,如果用“天赋”这个词来代替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明确,是你天生的一些特征。
我觉得一个挺残酷的现实是,天赋这个事儿,很多时候比努力更重要。
我们经常会说一些鸡汤,会说一些鼓舞自己,让自己相信,让自己更愿意拼搏的话,好像努力大过天。我觉得努力大不过天,尤其是在一些非常重要创作的维度上,可能在一个工作上面,在一个可能需要你去付出标准化的工作上面,努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创作上面,才华其实比努力更重要。
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说法,叫做老天爷赏饭吃。很多人可能看起来那么轻描淡写,或者就信手拈来,一写就是你可能要花很多很多努力琢磨,甚至你觉得你写不出的东西。
还有一些说法叫祖师爷赏饭吃,就是你进了这一行,每一行有每一行的祖师爷,祖师爷好像赏了一口饭,你在这一行可以通过自己的才华和努力,相对来说获得自己的位置。但是好像你又不会成为这个领域当中的天纵奇才。那我觉得其实也已经很难得了。
琢磨一下“赏饭”这个描述,其实挺有意思的对吧,你赏的是什么饭,是白米饭还是菜饭,是蛋炒饭;是赏你很多,还是很少。这件事其实是“赏”的,而不是你天然通过努力就一定可以获得,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我个人会非常认同和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不是意识到你的才华天分有多高,而是意识到你才华天分的短板在哪里,尽可能去规避短板,去找到它可能更自由的发挥空间,然后看一看它能够走到多远——这其实是一个人判断自己才华最重要的标准。
而不是说我挑了一个事情我喜欢做,然后我就硬要去试,试出来我在这个地方才华有多高、有多深,如果没有,那我再换一个方向,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对的路径。
内容创业的黄金时代,它被流量绑架了吗?
我们经常说今天是一个内容的黄金时代,我觉得所谓的黄金时代,就是指每一个有才华的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自己可能有限的才华给极尽地施展出来,让别人看到。
在不同的方向上,在各自感兴趣的领域上,基于自身的特点,去做出一个独特的作品,做出一个独特的作品线,这其实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事,今天还远远没有到这样的一个黄金时代。所以与其关心大家的才华是不是有天花板,我觉得更重要的问题是,你现在有的,已经挖掘出来的那些才华,是不是已经充分地施展出来了。
我写公众号很久了。公众号其实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文体。创作上它有点像是杂文或者散文,是基于创作者出发的一个作品。但公众号非常不一样的是,排完版推送出去的那一刻你就接受了反馈,你就接受了检验,反馈来自真实的用户,你不知道他是谁、来自哪里、是什么样的知识水平、喜欢什么东西,但是他就会给你留言,他就会直接告诉你他对这个文章的认识、他对你讨论的话题的观点、他的亲身经历、他的故事。
而所谓的检验是指它的阅读数,你所谓的流量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这篇文章受欢迎的程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很多的公众号的作者,或多或少,不能说被这些流量和反馈绑架,但一定会被它影响,这很现实。
有些公众号的作者觉得我的阅读数不高,是因为别人不理解我,我觉得这是孤芳自赏。孤芳自赏在某些创作特例当中是好的,但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所以公众号的流量、公众号的反馈一定是一个正向的事儿,但是一个正向的事情,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去接纳它,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这其实特别关键的,否则就会进入另外的一个极端。
在今天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令人担忧的事情。比如说因为只要流量高了,我的东西看上去就获得了市场的认可。所以我就盲目地,或者刻意地去迎合市场,于是我们就会看到那些永远热门的话题——明星的绯闻八卦、一些基于两性的相对比较低俗的话题,就会成为很多平台的主流。但在这个时候,你就完全把内容作为一种生意来看待了,一切就是流量导向的,它的逻辑就是流量逻辑。
可是内容本身有流量不能取代的东西,它有本身自成一体的逻辑,除了受欢迎程度、除了反馈之外,它也有作者自己的坚持,它也有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专业上的判断标准,这件事情还有人在乎吗?我觉得有,但是很多人会慢慢把它跟公众号这件事情剥离开来。
就是当你们要来判断我的作品的时候,我希望告诉你们,我不是一个公众号的作者,我是一个严肃的作者,我是一个有专业要求,对自己有追求的作者,当你们在看我公众号的时候,我希望看到的,就是我对时下最热门话题的一些呈现、一些观点,甚至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漫画、视频等等,都已经可以算作公众号这个内容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了。
我有一种担心,就是公众号慢慢会成为一个因为流量高度聚集、而内容本身也会市场化的地方,市场化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所以要强调一下。但是如果一个市场当中只有市场化的东西,其实挺让人遗憾的,就像是你在整个院线,只看得到商业电影,看不到文艺片,每年只能在电影节的时候,去买一些文艺片的票去看,你会觉得这或多或少是一个遗憾。
我们希望的市场是一个更饱和的市场,是一个更分层或者更丰富的市场,它能够让不同的人在这里实现不同的需求,也能实现某一个人的不同需求,这才是特别好的、特别理想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公众号在早期野蛮生长状态当中,还有一些这样的诉求能够偶尔零星的实现的话,今天在流量逻辑的捆绑下面,大多数人都在慢慢往流量靠拢。但是靠拢的方式会不一样,有些人就是索性放低身段,通过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去做;还有些人就是我仍然坚持自我,但不得不考虑流量,会去写一些可能大家会感兴趣的话题,但这写作方式仍然是自我的。但这个“自我”跟“我想要创作一个作品”之间,仍然会有不小的距离,我很难说哪种好,但我会希望说,不论哪一种好,我希望至少有一些我们认为很重要、很珍贵的东西不应该绝迹,不应该在整个市场当中消失,也应该有一些更好的机制,或者更好的拥趸去支持那些愿意做自我的人,让那些人不要陷入孤芳自赏的境地。
创作的乐趣
然后在今年,我其实做了一个对我个人而言蛮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写了一个话剧剧本。
这个剧本的年代,或者说它的创作背景,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因为我自己是1987年生的。
而我写的这个故事,年代其实远在1987年之前,所以我其实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做资料,去建立在我出生之前的那个,我们所谓的80年代,理想岁月的一个情景,当时的人怎么生活,关心什么事情,他们在校园里面谈恋爱的时候聊什么,他们整个人的群体,呈现出怎样的精神面貌。
我觉得这个工作本身是写作带给我的乐趣,其实也是重新回到一个自己陌生的,只在影像和文字当中见到过的年代,去进入一个这样的历史情境,带给了我很多的愉悦,让我有很多这种安心踏实的感觉。
所以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从工作,或者从自己在从事的事业的角度来说,带给我很不一样的满足,让我重新找回了那种在喧嚣、在一些嘈杂的声音当中安静下来的力量。我们创作初衷是去呈现我们所说的,跟今天并不一样的80年代,你知道有一个说法很有名,叫做“我的故乡在80年代”。
很多人尤其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他们会觉得那个年代,有非常强烈的时代特征,比如说理想主义,他们物质条件也考虑,但他们考虑得相对比较少;而且会分阶层,比如说有一些工薪的,或者普通老百姓,他们因为离生活的现实非常近,所以他们或多或少考虑一点,但知识分子,一些可能心有远大抱负,想要报效祖国的人,他们整个人所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和他们追求的生活目标,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出发点,可能是先去探究这个不一样究竟是什么,然后是什么动机,是什么心理,是什么时代特征,造就了他们的这个不一样。
有一个书我挺喜欢的,叫《时代的精神状况》,我觉得一个写作者,如果你想要去进入一个时代的话,你就应该去探究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如果我们说得再大一点,我会觉得80年代的精神状况,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是有挺好的参考意义的,不是说哪个高哪个低,或者捧哪个贬哪个,而是说当我们知道有一个时代它曾经是那样,它跟今天如此的不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深究一下它的不同,对于我们今天能有什么参考意义,我觉得这其实挺重要的一个事儿。
然后我去建立的这个校园背景的爱情故事,它有理想,有那个年代的诗和远方,也有很质朴的每个年代的人都会有的情感。然后处理情感的方式,会有什么不一样,这都是我们会感兴趣的话题。
流行文化仅仅是满足当下的愉悦吗?
我自己是流行文化很忠实的信徒,一个流行文化的狂热的爱好者。所以我能理解你的问题涉及的一个外延。
现在你会发现一种还蛮明确的趋势,比如说听古典音乐的可能看不起听民谣的,或者看话剧的看不起那些为了麻花走进剧场的那些观众。对我来说,我自己不是很认同这种程度的鄙视链。每一个作品它在市场上会得到一个明确市场的反应,这个反应是基于这个市场客观现实而产生的。如果它有流行的理由,与其去强行根据个人的品味去分一个高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去探究为什么这样的作品,有人觉得不好,但它仍然会成为流行,这个问题本身更有意义,而不是在这个鄙视链当中找到自己的优越感更有意义,所以这是我关于流行文化一般的态度。
但是我在今天会看到一个蛮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好像说对于流行文化的追逐,一旦融进了一个叫“自我”的东西之后,会有点变味。说得抽象一点,我会觉得它可能是只有流行没有文化了,或者文化层面的价值,好像慢慢被很多人在评价的时候给剥离掉了。
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些观众是非常资深的剧场观众,他可能三四十岁的年纪,已经看了一两千部话剧了,他有一两千次剧场经验,而有的观众他可能一年只进1到2次剧场。从一个所谓的评判流行文化的标准来说,我当然更愿意相信有非常丰富剧场经验的观众的判断。相对来说,他也有更丰富的评价体系去评价一个作品。可是在今天我看到网上很多人,会有一种逻辑是,虽然我只进过一两次剧场,但我喜欢的就是好的,我不喜欢的、我不理解的那些东西就不行,就不讨人喜欢。
进一步衍生出一些什么话题?我们知道今年可能会有一些剧爆红,让我们去深究背后的原因,我们会觉得说OK,它满足了一些当下的愉悦,它让我们爽到了,它可能一集就解决了一个小boss,整个都是一个打怪的过程。
像这样的东西能够流行,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合理性,视作唯一的流行文化标准,这其实是一种蛮大的危险。其实流行文化本身不排斥精英的东西,不排斥经典的东西,很多经典的摇滚乐,其实它有非常丰富的文化素养和文化意涵在里面,跟当时的社会情境,甚至是历史事件结合得非常紧密,可以说它们会改变整个历史、整个世界的进程。但是在今天我们好像很难看到一个这样的作品,尤其我们中国流行文化的圈子里面。
回头想想,其实罗大佑也许写过这样的歌,或者我们换个角度说,也许李宗盛写过一些歌,虽然它是关于人心、关于情爱,但是他写在80年代的歌在今天仍然会传唱,仍然会打中我们内心的那个最柔软的部分,让我们觉得他写的就像是我们自己一样。可是今天,我们还有这样的流行文化吗?我觉得好像很难有这样的作品,能够撑过四五十年或者更久,到了2100年的时候,还觉得“哇!这些21世纪第一个十年、二十年做出来的作品,他们写的真好”。
所以这会让我产生另一种警惕,一方面我会觉得去建立一个鄙视链,去呈现自己的优越感,这件事情不对。另外一方面我会觉得把自我凸显得太大,觉得我喜欢的就是好的,爽到的就是好的,其他的都不行,我不能理解的东西,我不愿意去学习,我不愿意去探究,我只是觉得我不理解,所以它不好。我觉得这样会阻碍文化的发展,流行文化本来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哪些东西是你原本深信不疑的,
可能随着年龄增长,开始有所怀疑?
我体内其实有一个燃烧的中二魂,我会看很多民工漫,都会特别燃。但是另一方面,我又会觉得,我对于整个世界是始终怀疑的,我很少有一些深信不疑的东西,我深信不疑的,可能都是那些特别抽象的大道理,我觉得这就不值一说,很多人会有一种很乐观的坚信,在我看来是不那么确信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叫正义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真理,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希望它成为一个真理,但我知道它可能永远不是。我觉得所谓的成长就是发现,原来我们想要的人生,我们接受的那个人生,最大的成长不是得不到,而是知道自己输得起。
这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很多人都要接受的过程。我们原来觉得最大的痛苦,是我想要这个东西而我得不到,在小孩的时候,在青少年时期,我觉得那太遗憾了,太难过了,虽然这个难过也很快会被平复过去,但是当时的难过是很真实的。可是在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到了30多岁,我会慢慢明白,原来输得起是更好的状态,我当然要去追求,我当然要去尝试,我不会因为那件事情可能得不到而退缩了。
我会知道如果输了,如果没有得到,它也是人生合理的部分,这是从个体意义上而言,然后我觉得如果说得再大一点的话,我觉得人就是要相信正义可能真的会缺席的,但是它不会缺席在所有的角落,它某一些事情上面,正义可能就不仅仅是迟到而已,它可能真的就不来了。
我们有很多吉祥话,这当然是很美好的意愿,这很美好的意愿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你千万不要每一句都当真,否极不一定泰来的。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说恭喜发财万事如意,是很美好的心愿。但是知道这个美好的心愿就够了,你的人生是不可能万事如意的。这样说可能有点悲观或者有点丧,但我反倒觉得你要接受这一点,你不能把你的人生建立在那种非常虚幻的乐观上面,就觉得正义永远会来的,人生总会顺利的,如果现在的人生,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将来还是会再起的。
我觉得在今天不是很流行丧吗?我觉得很多人是通过丧文化来消解人生的无奈和挫折,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丧完之后,消解完之后,你发现你的痛苦没有那么严重了,所以你进取的动力反倒变弱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危险。
我觉得我的那种悲观和怀疑论,其实是我不断努力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动力。我会觉得人生就是说不准的,那我眼下每一分每一秒,我就要好好努力,可能就要拼尽全力去做。就像我前面回答才华那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既然才华是有限的,那我就先把这个有限的才华,全部施展出来再说,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人,都应该去有的一个状态和一个心态上的转变。
2018年度关键字
逝。
这个“逝”没有什么悲伤的色彩,可能更像是《论语》里面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生最大的一个感触,不是突然而来的悲伤和突然而来的快乐,而是这些事情既然就那么突然来了,然后匆匆地又走了。
这个我这一年最大的感受,知道匆匆这件事了,知道原来日子不是一天一天过,而是一周一周过,一个月一个月过,知道眼下错过了这个事、这个人,可能这辈子你就不会再遇见了,一期一会了。你就会知道说,原来逝去的东西那么重要。这是我觉得今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字,我希望自己以后就会对每一件事,每一个人,用一期一会的态度去面对,然后能够更好地珍惜。
文字 | 黄扬;校对 | 慕名而来
互动话题:
你是如何看待“丧”这件事的?
每周评论区,被zan最多的评论者,将获得造就送出的礼品一份
加入社群:
添加小编微信(zaojiu12),发送暗号“进群”,带你进入神秘的造就官方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