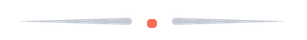编者按:《中国艺术》(Chinese Art)是西方早期研究中国艺术的重要文献,1958年在纽约出版,上下两卷。作者William Willetts(魏礼泽)(汉学家、西方艺术史家)从中国的地理特色着手,系统梳理了玉器、青铜器、漆器、丝绸、雕塑、陶瓷、绘画、书法、建筑等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他坚持客观描述作品的方法,“并不对所讨论器物给予美学价值论断,而是让器物自己说话”。
“让器物自己说话”,与观复博物馆“以物证史”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我们选择翻译此书的原因。此次我们邀请到美国CCR(Chinese Cultural Relics《文物》英文版)翻译大奖获得者对此书进行正式专业的翻译,译者也是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国际索引数据库)和AATA(国际艺术品保护文献摘要)收录的美国出版期刊Chinese CulturalRelics的翻译团队成员。
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此次翻译将存疑处一一译出,其后附有译者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本书,在绚烂璀璨的器物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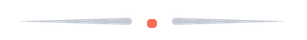
有人说:“Huang氏的花鸟画对色彩的把握非常精彩。笔法新鲜细腻;墨线几乎不可见,整个作品都是由淡色填出。这种画一般叫做写生。Hsu His则倾向于笔墨豪放,色彩简略,也就这些。他的笔法中精神气质是首要的。有一种特别的生命动感。Huang Chuan不喜欢这种处理,称之为粗鄙,拒之为毫无风格”。
这种院画派不喜欢的非正统画法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完全不确定,著名的没骨画法是否由Hsu His或者其儿子,或孙子Hsu Chung-ssu发明。但我们很清楚其面貌。《芥子园》这样描述:“对于写生来说,花卉一般无需轮廓。只需要用白色调和透明或不透明颜料即可。画之前就必须有成熟的概念。这种花卉和有轮廓的那种不同。枝叶都必须用颜色完成。我们称之为没骨画法……”。日本知恩院、法隆寺和井上收藏的传为Hsu氏长辈的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色彩分层用于巧妙表达阴阳向背和立体轮廓。莲花瓣用细描表现,填充精巧的大红色调和色,而法隆寺收藏的两幅画中,浮萍的造型由棕土色水洗色单独支撑。
毫无疑问,到了11世纪中期,一种新的自由风格加入到了中国画的技术库里面。但我们无法肯定的说,没骨画法完全放弃了勾线,或者不能说放弃了勾线的首要位置。11世纪晚期的批评家Kuo Jo-hsu在讨论一幅没骨画时说,这幅画的题款是著名的书法家Tsai Chun-kuo,其风格可以追溯到Hsu Chung-ssu。Kuo评论说,这种创新或许是由于Hsu的某种创作冲动,但他并没有完全抛弃轮廓线”。现代批评家都同意,没骨属于墨线轮廓和水洗色的结合。这种风格从Hsu家族传到了Chao Chang。后者又将其传到12、13世纪的那些伟大花鸟画家,从而形成所谓第二种院画风格。
在构图上,日本的这些据传是Hsu的画展现了Huang Chuan以来的复古派以后的大进步。其视野收窄。之前的画不愿意将自然蔓延生长状态做剪切,而这种剪切在《聚鸟图》里面就能感受到。或者在更早的山水画比如《祈雨图》(图42)中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早期做法被克服,手段是从自然秩序中提炼出概念意象,从而具备了秩序和意义,可以看到一种可辨识的“物”。
图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