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从1934年到1936年,法国文学巨匠罗曼·罗兰万里飞鸿,先后两次,向傅雷打听他的朋友敬隐渔。奈何经多方咨问,傅雷也没有得到确切音信。罗兰者,巨擘也,宗匠也,大师也,何以如此关怀一个籍籍无名的中国青年?最新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敬隐渔研究文集》,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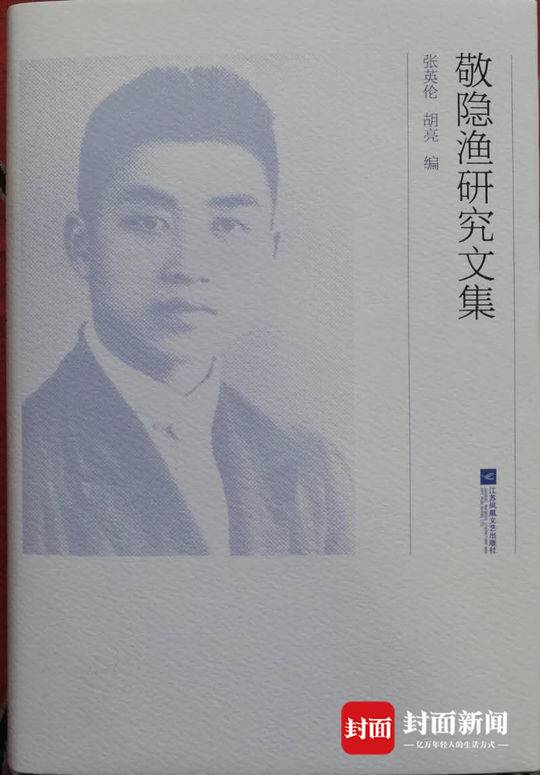
那么,敬隐渔是谁?这不光对大众读者是一个问题,甚至对文学圈内不少人,疑问也是成立的。《敬隐渔研究文集》的编著之一、诗评家胡亮说,“若干年前,叶灵凤就曾发出叹息,‘敬隐渔的名字,现在知道的人大约已经不会很多了’,而今天,眼看敬隐渔就快被——甚至快被文化界——忘得干干净净。好在一些素心独持的学者,比如王锦厚,尤其是张英伦,仍在一点点剔除历史的尘封,试图拼凑和还原敬隐渔的眉目。”
首次将《约翰-克利斯朵夫》译介到中国
首次将《阿Q正传》译介到法国
敬隐渔是诗人,作家,翻译家,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先驱者,生前主要居留在四川、上海和法国,与罗曼·罗兰、鲁迅、郭沫若等中法文豪都有交往。
敬隐渔
根据专家考证,敬隐渔1901年生于四川遂宁,1909年赴彭县白鹿乡,入无玷修院,复入领报修院,1916年赴成都,入天主教会办的法文学校,1922年赴上海,入中法工业专门学校,结识郭沫若(创造社掌门),1925年赴法国,先后入里昂大学、巴黎大学和里昂中法大学,结识——或者说投靠——罗曼·罗兰,1930年返上海,1932年后不知所踪,或以为蹈海而死,或以为投湖而亡,享年不会超过32岁。胡亮说,“敬隐渔的一生,坎壈,穷窘,病痛,遄速,雪泥鸿爪,电光石火,很快消散于茫茫天地,却让远在欧洲的罗曼·罗兰牵念难忘,其间自有一段非同寻常的奇缘。”
敬隐渔曾首次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译成汉文(没有最后完稿),介绍到中国;还曾首次将鲁迅的《阿Q正传》译成法文,介绍到欧洲。曾得到罗曼·罗兰、郭沫若、茅盾、成仿吾等人的高度评价,被目为创作、翻译和学术研究的“天才”(可惜是个“短命天才”)。综合各方面史料来看,很有可能,敬隐渔最后因为身体或精神疾病蹈海而亡(一说投湖以死)。
《敬隐渔研究文集》作为敬隐渔出生120虚年献礼,由现居巴黎的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英伦和川籍诗评家胡亮联合编著,江苏文艺出版社精装出版。全书分为三卷:卷一史料,收入敬隐渔、罗曼·罗兰、鲁迅、巴萨尔耶特等人的相关通信,以及罗曼·罗兰的相关日记,均由张英伦先生译为汉语。其中敬隐渔致信罗曼·罗兰的书信有40多封。卷二为论文,收入胡亮等11位当代学者关于敬隐渔的14篇最新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张英伦的《“一封信”水落石出》,胡亮的《可能的七里靴》等。卷三则收录张英伦精心编订的《敬隐渔年谱(1901-1933)》。该书既是敬隐渔研究的重要成果,又是早期中法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生动个案,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醒目空白。
在胡亮研究看来,敬隐渔的主要身份,是小说家,其次,才是小说翻译家。作为小说家,敬隐渔的作品有《苍茫的烦恼》《玛丽》《嬝娜》《养真》《宝宝》《皇太子》和《离婚》,其中《养真》是《苍茫的烦恼》之修改稿,而《离婚》乃是直接以法文写成之小说。1925年12月,其小说集《玛丽》由商务印书馆初版,1927年再版,1931年三版。作为小说翻译家,敬隐渔的作品则分为两类:汉译法作品,法译汉作品。法译汉作品有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之《海上》、《遗嘱》、《莫兰这条猪》和《恐怖》,法朗士(Anatole France)之《李俐特的女儿》,巴比塞(Henri Barbusse)之《光明》,罗曼·罗兰之《约翰-克利斯朵夫》。1930年11月,敬译《光明》由上海现代书局初版,1931年再版,1932年三版。汉译法作品有郭沫若之《函谷关》,陈炜谟之《丽辛小姐》,落华生之《黄昏后》,鲁迅之《孔乙己》、《阿Q正传》和《故乡》,冰心小姐之《烦闷》,茅盾之《幻想》,郁达夫之《一个失意者》。1929年3月,敬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由巴黎里厄戴尔出版社(Editions Rieder)初版,很快就有英文转译本《<阿q的悲剧>及其他现代中国小说》,1930年初版于伦敦,1931年再版于北美。
与罗曼·罗兰如子如父
胡亮特别注意到1926年,他认为这个年份“让人激动”,“仅仅在此前十四年,罗曼·罗兰才完成《约翰-克利斯朵夫》,仅仅在此前四年,鲁迅才完成《阿Q正传》。然而,就在1926年,敬隐渔已首次将《约翰-克利斯朵夫》译介到中国,参差同时,又首次将《阿Q正传》译介到法国——或者说欧洲。对这两部作品的选择,乃至改译《红楼梦》的计划,都很敏捷而坚定,可以看出年轻的敬隐渔实在是目光如炬。”
自1926年1月10日至3月10日,敬隐渔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未完成),经郑振铎——他与鲁迅皆为文学研究会成员——连载于《小说月报》第17卷第1至3号。自5月15日至6月15日,敬译《阿Q正传》经罗曼·罗兰修润和推荐后连载于《欧洲》第41至42期。胡亮说,“当时在世的两位伟大作家,罗曼·罗兰和鲁迅,经敬隐渔,完成了互读,也完成了如兄如弟的遥握。如果天假以年,敬隐渔必当促成这两个伟大人物——他们可以分别代表西方和中国——实现更为直接而深刻的对话。”
1925年9月10日,在瑞士奥尔加别墅,敬隐渔初次拜访罗曼·罗兰,后者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了他们的热烈交谈,其中有句话,“他写小说和诗歌”,说明敬隐渔得见其思想导师,终于没忍住,或有言及,“我也写些诗歌”。除了新诗,敬隐渔还填词,作旧诗。敬隐渔的孤独——甚至不用读其诗与小说——被罗曼·罗兰一眼看出。1925年9月11日,他再次接见敬隐渔,并在当天日记中写到:“可怜的小家伙好像极度地孤独。”
虽然敬隐渔与罗曼·罗兰缔结了如子如父的友谊,“可能也是和罗曼·罗兰往还最早、时间最久、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中国青年”,却最终见弃于鲁迅,——1930年2月2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到,“敬隐渔来,不见”。或以为鲁迅不见敬隐渔,是因为他正在接见冯乃超。鲁迅在日记中写到,“午后乃超来。波多野种一来,不见。敬隐渔来,不见”。冯乃超来访在前,故而相见,波多野种一和敬隐渔来访在后,故而不见。根据陈子善先生的研究,当日下午,鲁迅与冯乃超商议左联纲领等事。夏衍所著《懒寻旧梦录》,曾忆及当时他也在现场。或以为鲁迅不满敬隐渔,是因为后者及创造社扣押甚至销毁了罗曼·罗兰写给他的信。根据张英伦先生的研究,罗曼·罗兰这封信,并非写给鲁迅,而是写给敬隐渔。敬隐渔1926年1月24日致鲁迅信语焉不详,“原文寄与创造社了”,故而引起了后者的猜疑和愤懑。如果鲁迅接见敬隐渔,文学史上自然就少掉一桩悬案。
小说可以直接视为未分行的诗
在胡亮看来,敬隐渔的几篇小说,《苍茫的烦恼》《嬝娜》《养真》,尤其是《玛丽》,都用第一人称,都带有非常明显的自传色彩。《养真》的主人公叫作“K先生”,《玛丽》的主人公之父则叫作“K老先生”,而敬隐渔,在法国读书的时候,恰将自己的姓名译为“Kin Yn-Yu”。《苍茫的烦恼》,还有《玛丽》,主人公都叫作“雪江”,此名或涉“隐渔”,后来敬隐渔填了一首词——《忆秦娥》——袭用柳宗元《江雪》之诗意,补充交代了这两个符号的意义关联。至于《嬝娜》,主人公叫作“孑生”,正指向敬隐渔那无时不有的漂泊感和孤独感。而在《玛丽》里面,还透出来更多自传信息,比如,“母亲躺在床上,中了一颗流弹”——敬隐渔的母亲,正是这样的死法。
小说毕竟还是小说,还是来看敬隐渔的夫子自道。1924年12月10日,敬隐渔再次给罗曼·罗兰写信,曾有提及,“我也写些小说”,似乎可以印证前文的观点。面对这位伟大小说家,敬隐渔非常谦逊,没有直接自供为——像孑生在《嬝娜》中那样——小说家。虽说如此,可以看出,他还是更信任自己的小说——而不是散文或诗歌——的才华。
在胡亮看来,敬隐渔的几篇小说,除了《离婚》,“却都有诗的氛围。这几篇小说,大都穿插着——甚至通篇都是——独白、呓语、意识流和抒情性段落,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小说碎片,散文,散文诗,有的甚至还可以直接视为未分行的诗。”
穿上七里靴的早逝天才
对于敬隐渔的才华,创造社同仁每每高度赞赏。成仿吾和周全平均称之为“天才”,郭沫若则称之为“创造社的中坚”、“多才的青年作家”。罗曼·罗兰也是高度赞赏,他认为敬隐渔的法文,“造诣实在罕见”,“很完美”,“是规矩的,流畅的,自然的”,对敬隐渔抱有厚望,后来,甚至不惜拒绝了傅雷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请求。
在收入《敬隐渔研究文集》中的名为《可能的七里靴——介绍敬隐渔的诗与译诗》的长文最后,胡亮这么评价自己这位乡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活到五十岁,甚或四十岁,敬隐渔就有可能成为很重要的诗人和译诗家,还有可能成为更重要的小说家和小说翻译家。敬隐渔凭其刚起步的写作,已经留名中法文化交流史,留名现代小说史,但是,他却几乎没有留名任何新诗史——即便是刘福春先生那部洋洋数百万言的巨著,《中国新诗编年史》,也查不到哪怕一丝敬隐渔。敬隐渔穿上他曾无限向往的七里靴,自由的七里靴,刚起步,一步七里,两步十四里,很快就陨入了黑暗无垠的湖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