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国,标语是政治文化,也是时代标志。小区一隅是当地的税务局,办公楼周边就有不少政治标语。其中一条是这样的: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这条标语很有气势,核心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
说实话,经历过“文革”的人,不论主动或被动,总还是读过一点马列的。“九一三”之后,毛泽东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要求弄懂弄通马列六本书。当时我正上高中,农村无书可读,放假时找老师借来一本《反杜林论》,带回家中,埋头攻读,囫囵半片,总算通读一过。那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知识密集、内容深奥,虽然似懂非懂,但通过这本书得悉知识的海洋如此辽阔,也是重大收获。
二
1843年,对马克思来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一年,25岁的马克思与他童年时代的女友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燕妮出身贵族,她父亲是普鲁士政府的枢密顾问官。马克思的父亲则是一位犹太人律师,他本人则是耶拿大学刚毕业的哲学博士。而燕妮不仅“生的异常美丽,而且具有非凡的才智与品德”(梅林《马克思传》),按中国的说法,他们二人可谓青梅竹马、金童玉女。婚后不久,燕妮即陪伴马克思在欧洲多国间颠沛流离,屡遭驱逐,沦为世界公民。

这一年,马克思与左派黑格尔派的阿尔诺德·卢格合作,在巴黎创办了一本被恩格斯称为“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刊物”的激进杂志——《德法年鉴》。这是马克思为抗议普鲁士当局的书报检查令被迫辞去《莱茵报》主编之后,第二次参与报刊工作。这份杂志只发行了一期(1844年一、二期合刊),就无疾而终了,据恩格斯说,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它在德国的秘密传播遇到很大困难”,二“是由于在两位编辑之间很快就暴露出原则性的分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页393)第二条原因很重要,“道不同不相为谋”,“三观”不一致,只能分道扬镳。
这一年,恩格斯通过为《德法年鉴》供稿与马克思建立了通信联系,从此,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开始了40年的合作,成为终生的亲密朋友与同志,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这个主义,其实是他们二人共同的精神劳动的结晶。
这一年,通过在《德法年鉴》(包括一年前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按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真正完成了“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页83)这当然是相当传统的说法(甚至在今日俄罗斯,对列宁的评价也并非都是正面的)。本文引述的马克思这篇《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正是这期杂志的内容之一。
三
《德法年鉴》的创办,经历了将近一年的艰辛筹备。两位合作者——马克思与卢格,曾多次通信,就办刊及其他问题交换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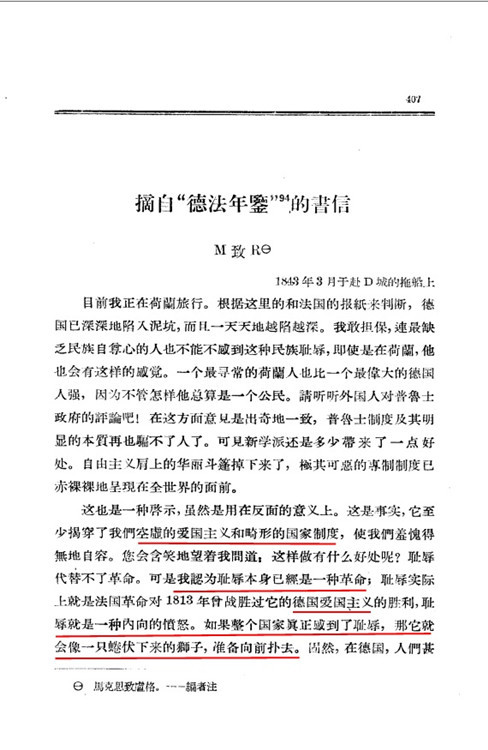
1843年5月,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提出了一个犀利的命题,他把普鲁士称为“庸人的世界”,并形象地指出,“所谓庸人是世界之主,只不过是说世界上充满了庸人及其伙伴,正如尸体充满了蛆虫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卷,页409。以下同书引文只注页码)阅读此文,足以纠正许多人的先定之见,即以为马克思的文章都是深奥难懂、文法复杂、语言枯燥的理论砖石,孰不知马克思是一个运笔如剑、文笔老辣、文采斐然的文章高手。
马克思所说的奴隶,当然不是指德国的社会等级或阶级构成,曾被马克思抨击的莱茵省等级会议就有诸侯、骑士、城市、乡村四级代表。因此,马克思所说的庸人,是从分析人们的社会心态或精神状态着手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鲁士的庸人,不仅包括德国的奴隶,也包括这些奴隶的主人,这个看法不是令人意外吗?庸人生存状态是怎样的呢?“庸人所希求的生存和繁殖(歌德说,谁也超不出这些),也就是动物所希求的。”(页409)这话与告子的“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十分相近。“生存”,“食”也;“繁殖”,“性”也。如果人们的“希求”只限于吃喝与性交,这与动物何异!马克思虽然以各类动物如“蛆虫”、“牲口”、“癞蛤蟆”等指代这类庸人,他的讽刺还是相当克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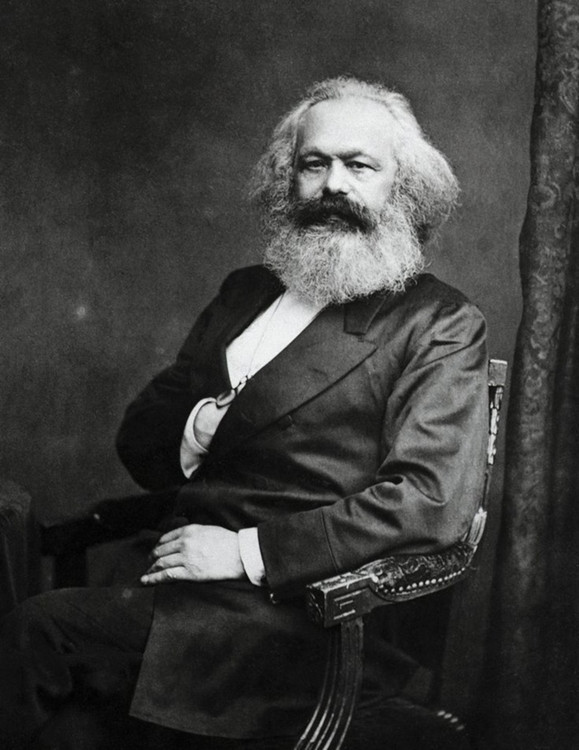
马克思进一步描述了这些人的奴隶心理,“那些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就像繁殖出来的奴隶或马匹一样,完全成了他们主人的附属品。”(页409)这些普鲁士庸人,只是一群“没有头脑”的“忠臣良民”,他们唯唯诺诺、浑浑噩噩,头脑僵化、不会思考,“无论是奴隶或主人都不可能说出他们所想说的话;前者不可能说他想成为一个人,后者不可能说在他的领地上不需要人。所以缄默就是摆脱这个僵局的唯一办法。Muta pecora,prona et ventrioboedientia〔垂头丧气,唯命是听、默默无言的牲口〕。”(页414)“不感到自己是人”、“不可能说出他们所想说的话”,“唯命是听”,“缄默”以对,这就是普鲁士庸人的部分心理特征。国王和贵族无论怎样压榨或凌辱自己与同类,他们忍辱含垢,苟且偷生,反而通情达理地认为,“国王也不容易”。一当域外风吹草动,则是一犬吠形,群犬吠声,充分表现出庸人们对国王的一片忠诚。
四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庸人社会所需要的只是奴隶,而这些奴隶的主人幷不需要自由。虽然,人们认为土地和奴隶的主人优越于其他一切人而称他们为主人,但是他们和他们的奴仆一样,都是庸人。”(页409)庸人是可悲复可怜的,奴隶的主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骑在那些只知道做主人的‘忠臣良民,幷随时准备效劳’而不知道别的使命的政治动物的脖子上。”(页409)他们的精神世界仍然是庸人。庸人世界里的庸主,如同《动物农场》的那头“伯克夏公猪”,“按资格来说,他们完全适宜于支配和统治这个动物世界;……他们在接受朝拜时,对这些在下面蠕动着的、没有头脑的动物扫一眼,这时他们除了想到拿破仑在别列津纳河所讲的话之外,还会想到什么呢?据说,拿破仑向他的侍从指着许多掉在别列津纳河里快要淹死的人叫道:Voyez ces c rapauds!〔看这些癞蛤蟆!〕”(页410)这群“不知道别的使命”,只知道“随时准备效劳”的“忠臣良民”或“政治动物”,自然是不幸的,然而,统治他们、管辖他们,居高临下地接受他们“朝拜”,瞧不上这些“蠕动着的”“政治动物”的庸主们,也并没感受到奴隶们的夸张拥戴与廉价谄媚带来的荣耀,没有感到奴隶们“高级红”和“低级黑”带来的快感,他们俯瞰大地,鄙夷地看一眼“这些癞蛤蟆”,只能勉强地满足一下空虚的心灵。将近100年前,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笔下的蠢人,与马克思的论述非常相似:“绝对的服从,就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甚至连发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无须思想、怀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自己的意愿就够了。”(《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页33)服从者与命令者的愚蠢,都在他的射程之内。
这些奴隶动物般地苟活着,生存着,他们的主人甚至把他们当作“蠕动”着的“蛆虫”或者讨厌的“癞蛤蟆”,马克思归纳道,“庸人的世界就是政治动物的世界,……这种制度的原则就是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页410)一涉及“政治动物”,马克思很自然地联想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页7)”的论断,他不无讽刺地写道:“如果德国的亚里士多德想根据德国的制度写一本他自己的‘政治学’,那末他定会在第一页上写道:‘人是一种动物,这种动物虽然是社会的,但完全是非政治的’。”(页410)因为这些庸人们首先不具备关注政治的智慧,同时失去了关注政治的勇气。“少谈政治”、“莫谈国事”,几乎成了几千年来的生存智慧,如同当今的微信群主,为了群的安全都会制订这样的群规。
五
批判社会与人性,作为后起者的鲁迅与马克思有点近似。不过,鲁迅批判的是国民的“坏根性”(《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32),矛头主要是向下的;而马克思不仅批判国民的坏根性,更批判国王(与制度)的坏根性,矛头是向上的,后者始终是主攻方向(这从他初出茅庐就批判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林木盗窃法以对莱茵省等级会议,可见一斑),他的《资本论》甚至“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尽管后人牵强附会地称鲁迅也是马克思主义者,鲁迅却坦承,“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鲁迅全集》第12卷,页496)鲁迅接触与掌握的更多的是列宁主义或苏俄主义。这正是他晚年始终为苏俄政权赞颂与辩护的基本原因。他曾如此表态,“有马克思常识的人来为唯物史观打仗,在此刻,我是不赞成的。”他“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鲁迅全集》第4卷,页128)然而,这项工作他是不做的,“虽然并非不知道有伟大的歌德,尼采,马克斯,但自省才力,还不能移译他们的书,所以也没有附他们之书以传名于世的大志。”(《鲁迅全集》第8卷,页310)鲁迅一生移译了大量苏俄与东欧的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却没有翻译过马克思的任何作品,不知是否因为如上所述的谦虚精神。
六
在一个庸人充斥的社会里,人自觉不自觉地堕落为“非政治动物”,而庸人社会完全是制度的产物。寥寥几笔,马克思勾勒了专制制度的特征——“在普鲁士,国王就是整个制度;在那里,国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总之,一切制度都由他一个人决定。”(页412)马克思的论述递次深入,“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是事实。”(页411)那是一些什么样的事实呢?“他眼看着这些人为了他而淹在庸碌生活的泥沼中,而且还像癞蛤蟆那样,不时从泥沼中露出头来。”(页411)马克思这段话充满散文笔调,但他没说出来的话是,这些“政治动物”的困顿与窘境,恰恰拜国王所赐。
马克思对专制制度的抨击,直击人性深处,普鲁士虽然不是《动物农场》,马克思却尖锐地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幷且和人性是不兼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页414)在马克思的概念里,君主制与专制制度是同义词,穿着蟒龙袍的皇帝,穿着燕尾服的国王,穿着西装的独裁者,都是独裁专制,“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哪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页411)在口头上,即使他把“人”捧到天上,也改变不了这一本质。
七
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庸人世界的奴隶与主人的关系。他显然认为,在专制制度下,庸人与君主是相伴相生、相辅相成的,“庸人是构成君主制的材料,而君主不过是庸人之王而已。只要二者仍然是现在这样,国王就既不可能使他自己,也不可能使他的臣民成为自由的人,真正的人。”(页412)庸人不过是搭建权力金字塔的砖瓦与石料,君主的伟业构筑于万千庸人的白骨之上,没有成千上万的苦役与劳工,就没有秦始皇的万里长城。庸人不可能选出服务民众的公仆,君主不可能成为爱民如子的明君。专制制度的根本特征是权力缺乏监督。人们都知道英国学者阿克顿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人们却不知道紧接在后面的一句:“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自由与权力》,商务印书馆,2001年,页342)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独裁者总是以“伟大人物”自居。其实,阿克顿论述专制制度比马克思更深一步,“国家专制主义而不是君主专制主义是现代的最大危险。”(同上书,页338)毕竟,后来的专制主义极少是以君主或国王的身份出现的。他进一步指出,“当现代专制主义诞生以后,国家就以主权者的身份向任何事物施加影响和提出要求:商业、工业、文学、宗教都被宣布为国家的份内事务,相应地,这些领域也就被国家霸占和监控。”(同上书,页339)阿克顿生活的年代,比马克思稍晚,他同马克思一样,没能看到后来的苏俄革命,他的上述观点只是一种理论推测。不幸的是,他的推测成了现实。遭到暗杀的苏俄革命的领导者托洛茨基写道:“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通往奴役之路》,[英] 哈耶克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页116)这“唯一的雇主”,不仅履行着君主的职能,也比君主更具欺骗性。
八
在庸人成堆的地方,出路何在呢?马克思诙谐地指出,“满载傻瓜的船只或许会有一段时间顺风而行,但是它是向着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页408)他给庸人指出了两个出路或目标,“人是能思想的存在物;自由的人就是共和主义者。”(页409)前者是初级目标,后者是高级目标。作为灵长类动物的人,起码有脑子吧,至少能思考吧!作为一个心灵健全的人,一个人性正常的人,才有可能追寻自由。他提醒说,“必须唤醒这些人的自尊心,即对自由的要求。……只有这种心理才能使社会重新成为一个人们为了达到崇高目的而团结在一起的同盟,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页409)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只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从不提倡“民主”与“自由”。这显然是极大的误解。请注意,马克思对专制制度的社会转型,提出的设想不仅包括“对自由的要求”,而且要“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甚至还有更加深入的论述,“既然我们已经沦落到了政治动物世界的水平,那末更进一步的反动也就不可能了。至于要前进,那末只有丢下这个世界的基础,过渡到民主的人类世界。”(页412)请注意,马克思所憧憬的“民主的人类世界”,并未加上“德国特色”或“普鲁士方案”的限制词。
九
这样的社会转型不是天上掉馅饼,离不开志士仁人的努力与奋斗。马克思是学者、是思想家,他不是将军、不是政治家(倒是马克思的女儿曾送给恩格斯“将军”的称号),他拥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服务人类与世界的智慧与思想。他这样说,“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幷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页414)“揭露旧世界”是途径,“建立新世界”是目标,马克思与恩格斯一生致力于“揭露旧世界”,至于“建立新世界”,并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何况所谓“新世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受难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是必然会使那饱食终日,醉生梦死的庸俗动物世界坐卧不安的。”(页414)在专制制度之下,“在思考的人又横遭压迫”是肯定的,而“受难的人在思考”却并不一定。在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就有太多“都怪自己命不好”,“老爷总是对的”,“胳膊拧不过大腿”,“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一类苟且偷生的活命哲学。马克思作为一个年轻学者和思想家,他对《德法年鉴》提出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页416)马克思一生多篇重要著作的标题都示以“批判”二字,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等等,即使未标“批判”的著作也充满了批判精神。马克思的批判,从根本上说,是理论上、逻辑上、学术上、政治上的批驳、评论、分析与判断,与“文革”中以整人为目的的“大批判”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马克思以下的论述,表面上是为《德法年鉴》这本杂志确立的办刊方针,我们“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眞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页417-418)这个年轻的思想家,不仅体现了令人钦佩的政治勇气与批判精神,而且体现了立足现实,为人类探求真理的伟大追求。批判就要清理脚下的垃圾与羁绊,就要涤荡历史的因袭与弊端,而这离不开摆脱名缰利锁的彻底的批判精神,“人类要洗淸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眞相。”(页418)先不说这种看法是否纯粹的“负能量”,清洗自己的罪过,说出罪过的真相,作为一种使命,谈何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