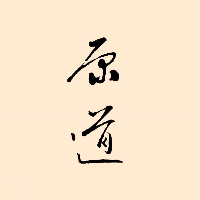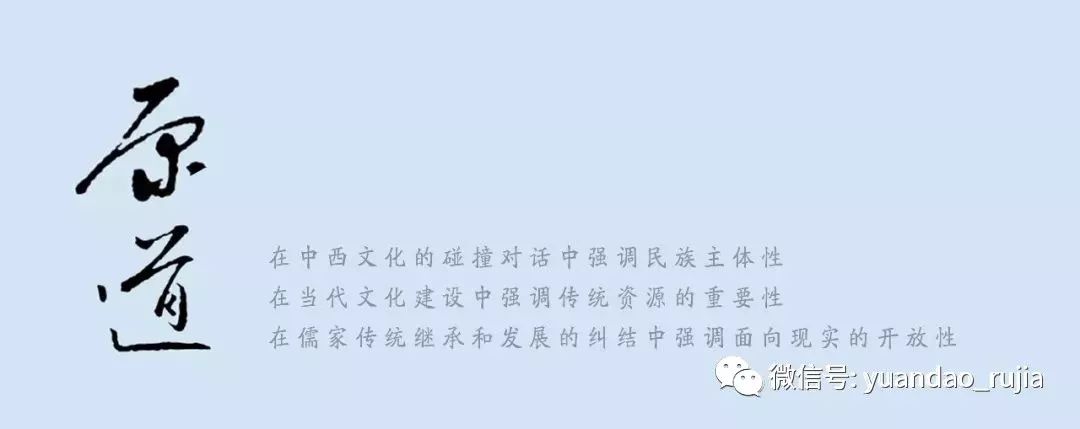
真理的存在方式:阿兰·巴迪欧电影哲学思考
李 双
(阿兰.巴迪欧:《存在与事件》,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内容摘要:电影的思想角色在于处理与现实的关系。从前关于哲学的传统思考中,不谈论真理,是无法想象的。而在反哲学、反形而上学思潮盛行的今天,谈论真理,反而成了不合时宜的。
阿兰·巴迪欧在洪流中逆势而上,提出真理的回归,重返柏拉图。与萨特、福柯、德勒兹等法国哲学家一样,作为不折不扣的影迷,巴迪欧的真理观同样统领着他的电影哲学,真理如何在电影中存在,电影要表达什么,是他关注的核心问题。
电影作为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如何能达到无限真理?理解巴迪欧艺术真理观的关键在于掌握“艺术配置”的含义,并将其诉诸于电影。理念对电影的拜访、感性材料自身缩减为电影本质,此双向运动构成了理念在电影中的独特存在方式。在缩减中获得纯粹的电影理念过程中,主体保持对真实的激情,直面真实与伪饰的距离,从而达到无限真理。
关键词:阿兰·巴迪欧;哲学;电影;真理;艺术
在思想界,电影不仅被看作一种艺术形式,更重要的角色在于处理与现实的关系,这是诸多哲学家涉及电影的原因。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在《运动—影像》《时间—影像》中提出独特的见解:电影并不是现实的幻影,一旦生成,就成为自身的主体。换言之,电影自身在运动、感知时间。
仍健在的阿兰·巴迪欧对电影的思考,被视为一场与吉尔·德勒兹的想象对话。他不仅认为电影是一种思维方式,更将电影视为真理生产的重要前提,提出电影生产真理的论断,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电影的哲学地位。
概言之,巴迪欧有机结合了生成性的真理生产程序与独特的电影艺术形式,提出了革命性的电影本体论以及具体的实践理论,对电影学界乃至哲学界都有着重要意义。
一、艺术—真理的生产程序
艺术与哲学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柏拉图驱逐诗人,认为艺术是真理影子的影子;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认为艺术是关于现实的摹拟,无法带来任何理性的知识抑或真理。
英国经验主义的休谟认为美的本质是人心上产生的效果,与对象无关,更与普遍的真理无关;康德统一了德国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认为美感在于想象力和知解力的和谐,承认主观的普遍性,真理统领着美的理想。
集美学大成的黑格尔在康德的基础上,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艺术成为真理的化身。到了尼采则试图破除形而上学,宣称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尼采笔下的“真理”已不是柏拉图、黑格尔所说的理念,更不等同于“主观与客观契合”的知识—真实,而是指对无意义世界变化过程的认识。艺术作为一种强力意志拯救世界,由此高于真理。
在海德格尔眼中,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他并没有真正克服柏拉图主义,仍然在形而上学的二元论中完成另一种可能性。为此,海德格尔站在“思的另一端”,真理成了“存在”。他认为艺术能生产真理,因为艺术作品中已有真理的自行置入:“超感性领域”与“感性领域”在此获得了统一。
(海德格尔)
然而在巴迪欧看来,这只不过是海德格尔自以为是地将艺术与哲学缝合,同样没有理清艺术与真理的关系。更为糟糕的是,当尼采、海德格尔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形而上学”潮流,真理在存在的澄明、去蔽中陷入了神秘主义。
正是在这个思想背景下,巴迪欧提出“重回柏拉图”“重返真理”的口号。但实际上两人的真理观相去甚远。众所周知,柏拉图的真理是理念,实存的事物只能分有大写的“理念”,真理是“一”。巴迪欧认为,真理是一种“生成性”的程序,一次事件在现实的裂缝中溢出激发了程序,忠实于事件的主体在其中出场,促使有限的事件能生产出无限的真理。
显然,巴迪欧强调的是真理与事件的关系。由于事件是偶然的、个别的,从而造成了真理的“多”。如此看来,他虽然重提普遍性的真理,但这种普遍性是建立异质性之上的,确保彼此之间具有共存的可能。
笔者认为,这也是巴迪欧提出注重异质、差异的艺术之所以能够生产真理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与海德格尔借助哲学理解艺术不同,巴迪欧认为艺术生产真理的过程不需要哲学,艺术自身就能生产出真理。
不仅如此,巴迪欧把艺术与真理的关系归纳为教诲式(didactic)、古典式(classical)和浪漫式(romantic)等三种模式。他认为,在教诲式中艺术无法产生真理,古典式认为艺术是对真理的模仿,浪漫式则将艺术理解为真理的化身。
巴迪欧看来,以上三种模式都未能真正揭示艺术与真理的关系,于是提出第四种模式:“非美学式”(inaesthetics),即艺术自身(包括艺术创作、作品流通、受众接受、文化影响等)就能生产专属于艺术的真理:艺术—真理。
为了更好理解四种模式,笔者以梵高的名画《农鞋》为例略加解释。教诲式模式(如柏拉图)思考农鞋,会认为画中的这双鞋是对现实中个别农鞋的模仿,而现实的农鞋是对农鞋理念的模仿,因此艺术作品与真理隔了三层。虽然绘画分有了一部分美的理念,但有限的艺术绝对无法生产真理。
(梵高:《农鞋》)
在亚里士多德代表的古典式模式眼中,现实的农鞋则是绝对的真实,因此描绘事物应有的样子的艺术就是对真理的直接模仿。海德格尔则属于浪漫式模式,他强调,梵高再现的并不是个别存在者(现实的农鞋),而是物的普遍本质,即存在之真理的化身。
海德格尔赋予了艺术认识器物存在的重要性,“只有在这个作品中,器具的器具存在才专门显露出来。”巴迪欧标举的“非美学式”模式,不仅斩断了艺术摹仿现实的传统,而且反对将艺术视为哲学的对象,拒斥把艺术当作哲学的工具。
在此基础上,巴迪欧用内在性和独特性来审视艺术与真理的关系。如前文所述,真理生产源于事件,事件促发的真理必定是内在于事件的真理。事件断裂了艺术的旧有秩序,从惯常的经验中溢出,这个过程始终内在于艺术的生产、传播及其效果。
所谓的独特性,则意味着艺术所证实的真理绝对属于它本身,不仅每次真理生产的过程都是独特的,而且,不同艺术作品之间的真理也是截然不同的。巴迪欧看来,浪漫式模式虽然符合内在性要求,却与独特性不符。海氏谈论艺术所生产的真理即存在,是一种共性,可以在不同的艺术作品中流通。如此生成的真理自然也就缺乏独特性。
为了进一步阐释“非美学”即艺术生产真理的过程,巴迪欧提出了“艺术配置”的概念。它不是一种艺术形式,一段被视为对象的艺术史中的时期,也并非一个技术性的装置,而是从一个特定的事件开始,组成实质上无限复杂的系列作品。
具体说来,当旧有的秩序无法超越自身,平庸不断重复,事件这股暗流就在平滑的现实下涌动。这股暗流的力量足够大时,将会瞬间喷薄而出破坏旧有的秩序。前所未有的新事物诞生后,勇于接受并忠实(loyal)于事件的那部分人成为主体。这时,我们就可以说,新的艺术配置诞生了。如此看来,艺术配置使有限的艺术作品具有事件性的力量,促使整个真理生产程序的发生。
艺术配置中的“事件”,是指一系列与当下习以为常的艺术规则、风格等发生明显断裂的作品,标志着一种新的可能性。类型更迭、风格演变、体裁创新都是事件的结果。
巴迪欧举例解释,在悲剧诞生之前,古希腊在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活动中以歌颂赞美诗为主,只需要一个演员和歌队就能完成。埃斯库罗斯第一次在古希腊话剧中引入了两位演员,并使两位演员之间产生了对话,通过语言与行动表达出了悲剧的情节。
但古希腊悲剧这个艺术配置并非单靠埃斯库罗斯一人就完成的,而是直到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创作了数百部悲剧才得以完成。再如,海顿、贝多芬等多位音乐家撕裂巴洛克时期的通俗音乐,成就了古典主义音乐的艺术配置;从塞万提斯到乔伊斯等多位文学家创作的小说文体断裂了散文的“统治时期”,从而实现了小说的艺术配置。
由此看来,尽管事件在形式上可能是一个人名、一个流派、一种风格或者一种体裁,但真正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包括概念形成的历史背景、艺术本身的特点和受众的接受程度等。
在具体的艺术生产中,有限的事件如何生产无限的真理?巴迪欧认为关键在于实现无限的艺术配置。笔者理解,真理生产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内在、持续、循环往复地发生的,因此无限的真理并不会在一次生产后就停滞在程序末端。
真理一旦生成,曾经无法辨识的事件占据了主体位置,逐渐被接受为新的知识。然而,为了避免跌入旧有秩序的深渊,重复旧知识被取代的下场,无限的艺术配置需要持续地对自己的界限、终极作出发问,将自我对象化,在撕裂自身的裂缝中事件再次溢出,产生无限的真理。
“一旦停留在艺术内在的局限中,那艺术自身,包括每一次的修改,将始终是破坏性的和无关紧要的。”这个过程巴迪欧称之为事件性的自我揭示,即反思自身、断裂自身,让事件从内在的裂缝溢出,不断充实真理的内涵,最终形成无限的艺术配置,达到无限真理。
画家毕加索正是无限艺术配置的绝佳代表。巴迪欧在《电影》中提及,毕加索在20世纪3、40年代的非人物画像虽然白纸黑笔寥寥几笔极其简单,但这是建立在他世纪初时的立体主义风格,是从他的立体主义的立场进行的表达。
笔者认为,毕加索上万幅画作并不意味着重复,相反,他的画作类型多样,其中能窥看他创作风格的阶段性变化,各种类型的断裂中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毕加索作品)
毕加索早期“蓝色时期”、“粉色时期”仍属于印象派,但绘画中所体现独特的人物面部立体线条已经与传统印象派拉开了距离。此后非洲文化对他的影响充当着强有力的事件,彻底阻断了与印象派的关联,使毕加索走向了全新的立体主义。在反思绘画的边界与终极后,毕加索晚期在平面的绘画中融入时间维度,叙事性地表现了他当下的政治思想,开创了超现实主义风格。
毕加索穷尽绘画的可能性,没有停留在一般画家所满足的舒适圈中,而是不断挑战看似圆融的真理,在内部进行事件性的自我揭示,从印象派的自身内部分裂出立体主义,再从立体主义的内部揭示出抽象派,真正实现了“毕加索”这个艺术配置的无限。
二、电影—真理的生产程序
(一)《黑客帝国》的隐喻:电影真理的生产程序
“在所有艺术中,电影无疑是最有能力思考、最能产生牢靠真理的艺术。”在电影理论文集《电影》开篇编者安东尼与作者巴迪欧的对话中,后者如此掷地有声地断言。
巴迪欧在此书《电影的辩证寓言》一文中剖析了《黑客帝国》(The Matrix , 1999)与柏拉图洞喻的同构性,认为救世主尼奥作为主体如何逃脱假象的母体就是柏拉图所言如何逃离洞穴的过程。而在澳洲学者亚历克斯·林(Alex Ling)看来,更重要的是,巴迪欧电影真理的生产程序本身就与《黑客帝国》的情节叙述设定十分相似。
电影中,预言师家中的孩子盯着手中的勺子,勺子逐渐弯曲,证明了这并不是真实世界里的勺子,只不过是人造的虚拟效果。电影艺术同样如此,它不断向外界发出讯号,证明自己仅仅只是影像,而非真实。
正如意念能改变勺子的形态,电影通过拍摄手法后期剪辑等,选择性呈现或扭曲原本世界的样子。电影作为真理的艺术,通篇为蒙太奇和剪辑,是假象的集体;《黑客帝国》中母体(Matrix)以假象冒充真实世界。救世主身处其中,如何抽离质疑母体?同样,电影—真理如何脱身于假象?笔者认为,这就是事件从假象溢出,撕裂平滑的现实,主动生成真理的过程。
(《黑客帝国》剧照)
在《黑客帝国》中,尼奥一开始只是母体之中的一个元素,他将母体呈现给他的一切视为真实。直到墨菲斯出现,他带着尼奥逐渐认识藏身在现实背后的母体,向尼奥证明一直以来信以为真的不过是母体通过电脑程序操纵下虚假的结果。
尼奥虽然被墨菲斯认作是救世主,但他并不是一出场就成为了毋庸置疑的主体。尼奥一开始是被母体操控着的,正如他进入程序后被编写出来的红衣女子吸引住。
为了让尼奥获得主体身份,墨菲斯对他进行了一系列训练。他将尼奥带入母体内部,告诉尼奥要“解放自己的心灵”(free your mind)。尼奥在训练过程中克服对外界的恐惧与怀疑,摆脱母体对其心灵的控制。
既然墨菲斯同样能克服母体虚假的控制,但为什么只有尼奥成为了主体?笔者认为两者的差距是在影片最后尼奥营救墨菲斯的情节中体现出来的。祭师预言者对尼奥说,他和墨菲斯中必有一死,然而当墨菲斯被抓,尼奥全身而退的时候,尼奥不顾预言作出了营救墨菲斯的选择。
墨菲斯从始至终都听信着祭师的预言,相信尼奥就是救世主,而尼奥则企图破除预言。在真理继续生成的无限配置中事件会从内部再次撕裂看似圆满的真理,进行事件的自我揭示,在影片中内在的事件就是对祭师预言的怀疑。
沉溺在第一层真理之中的墨菲斯过分信任祭师,将预言当作无限真理。相比之下,尼奥将自身与预言拉开了距离,没有沉迷预言,而是用自己的生命挑战预言的真实性,最后也成功让墨菲斯和自己都存活下来。
正如《黑客帝国》中墨菲斯对尼奥说,母体被制造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在其中诞生,他有能力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变一切,根据他的标准重塑母体,重新创造真实世界。正是他将我们第一批人解放,并教导我们这个真理:只要母体存在,人类就永远不可能自由。
可见,并不是认识到母体的虚假就足以成为主体,主体的革命性力量在于他能重新创造真实的世界。一旦停留在第一重真理,那么只是由于事件的出现否定了母体,若想创造新的世界达到无限真理,必须不断进行事件性的自我揭示。
尼奥在影片最后说,他要创造的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这意味着,尼奥意图创造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终点,取代了旧秩序的新秩序如果一成不变,那必然会被新的事件撕裂。巴迪欧的真理需要不断在无限配置中断裂自身,进行事件性的自我揭示,实现无限的真理。因此真理是无限可能的省略号。
(二)生产真理的事件:电影中的断裂
巴迪欧认为,“电影真理的生产是在断裂中创造综合”。断裂发生即事件出场之时,生产真理的配置发生了变化,真理就在这断裂与变化中产生。电影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横空出世,打破了绘画的平面性、音乐的不可见性、戏剧的舞台性,它断裂了传统艺术的表现方式,以不可辨识的面貌出现,成为了撕裂旧有秩序的强大力量的事件。
电影虽然区别于传统艺术,但传统艺术的影子在电影中均有迹可循,用巴迪欧的话说,电影综合了各种艺术。充当事件的电影并不是彻底对旧有事物的否定与推翻,它从传统艺术断裂的缝隙中溢出,将各种艺术的特性重新综合在自身的形成过程之中。
巴迪欧认为卢基诺·维斯康蒂的电影《魂断威尼斯》(Death in Venice, 1971)片头中清晰反映了传统艺术与电影之间的关系。马勒的第五交响曲伴随镜头流动,印象派风格的视觉效果渲染了沉静。电影独特之处在于对艺术的综合,朦胧的景色与主人公阴郁的神情通过镜头剪辑穿插浮现,沉重的旋律在影片中铺开。
(《魂断威尼斯》剧照)
在观赏过程中,观众绝非割裂地体验各种艺术,而是对电影整体进行审美,同时直观感受电影的叙事性与艺术性。电影并非多种艺术的简单相加,绘画、音乐与戏剧表演的艺术特质在电影中得到彰显的同时,电影对艺术进行了综合并赋予了更复杂更深层的审美感受。
巴迪欧提出,电影是蒙太奇和剪辑的艺术,是对可见物进行提取的艺术。这注定了电影不可能表达完整的现实,在提取过程中必然有对现实的取舍。巴迪欧认为电影运动是虚假的,并将电影的虚假运动分为三种:1.整体运动,即剪辑对空间、时间的重新组合;2.局部运动,即镜头对可见物的截取;3.不纯运动,即电影中对其他艺术的引用。
巴迪欧用维姆·文德斯的电影《错误的举动》(False Movement,1975)举例,他认为片尾主人公朗诵其在影片中反复提到的诗时,三种运动各自表达了不同的真理。
在整体运动中,朗读的这首诗成了影片的主体,诗从电影的对白语言中撕开裂缝,生成了诗意的真理;在局部运动中,主人公的神情透露出他企图逃避,试图断裂与情节的关联,人物脱离角色与情节,电影的真理在这里体现为对存在的惊叹;在不纯运动中,演员的身份与电影的艺术割裂了诗的纯粹性,主人公在此朗诵的诗并非纯粹的诗,而是交杂在电影与诗之间新的主体。
电影充斥着虚假的运动,为什么仍能生产真理?笔者概括电影—真理的诸特点:1.电影—真理是混杂的、多元的;2.电影的虚假运动是电影—真理生产的条件;3.电影—真理体现在电影时间的经过中。
在《错误的举动》中,一个片段从三个侧面能生成三种不同的真理,这意味着电影—真理是混杂的、多元的。没有唯一普遍的电影—真理,一部影片通常对应着多个真理。
至于第二点,巴迪欧认为这三种虚假的运动在电影中交融为一个结,换句话说,这三种运动伴随着影片,并共同体现在电影中的每一个瞬间。笔者理解,电影这三种不同侧面的虚假运动其实就是电影的三个基本属性,因此虚假性本身就内在于电影之中。
巴迪欧称,一部影片就是运用镜头与蒙太奇展示理念的经过。可见,蒙太奇、镜头、不纯这三种虚假运动是电影生产真理的条件、前提与手段。虚假的运动在电影构建的时间中展开,电影—真理也在这个过程中生成。
如上文所述,电影若要生产无限的电影—真理,必须在内部进行事件性的自我揭示。电影需要审视自身,将自身对象化,即内在地思考自身的虚假性。电影的内容表面上均是虚假的,而清楚意识到虚假、理解虚假、突破虚假,才是达到电影—真理的途径。
虚假运动并不是电影生产无限真理的障碍,相反电影通过直面自身的虚假性、思考自身的虚假性,探索自身与虚假的距离,从虚假运动中提炼无限的真理。电影之所以与其他艺术区分开来,原因在于电影创造了一个特殊的时空,电影的完成依赖于这个时空的建构,电影—真理也在电影时空的过程中展现出来。
三、电影中真理的双重运动
(一)减法:提炼真理
巴迪欧提出,电影生产真理的基本原则——减法(subtraction),即真理的无限性体现在真理从已知的知识形式中作减法,继而成就其纯粹而简单的特质。
在外部,电影作为事件撕裂了旧有艺术的形式,对各种艺术作减法,提炼艺术精粹的部分并为自身目的所用。就电影内部而言,减法意味着从电影复杂多余的材料中去除干扰电影纯粹目的的元素,最终实现简化,实现无限的真理。
在音乐、绘画、甚至舞蹈和写作中,创作者是从纯粹开始。正如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所说,“你开始于空白页面的纯粹”。艺术的首要问题就是忠于原初的纯粹。
然而电影开始于无序、累积、不纯,巴迪欧眼中,电影创作的过程充满艰难,即便是拍摄一个酒瓶,也有太多无关的东西妨碍着,例如酒瓶里的酒、标签、酒瓶玻璃的质量等等。
(电影的拍摄)
如何才能在电影无限的复杂中提炼出纯粹的理念?巴迪欧在此举了四个例子:1.戈达尔在城市噪音混沌的基础上,用条理和等级将各种声音区分开,把声音的混沌转化为窃窃私语,创造当代寂静;2.某些电影中汽车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场所,摆脱了汽车平庸的印象,锻造了一种新的纯粹;
3.通过使色情影像转化成爱的影像,或者将其风格化,再或者成为二度色情“超色情”,使其走向一种新的简化;4.将枪战风格化,成为一种舞蹈,成就纯粹。正如巴迪欧所说,“电影接受并吸收这种无限的复杂性,从中产生纯粹”。
据此笔者可以概括认为,此处提出了电影中实现纯粹的几个方法:1.承认并遵从社会的基本形态,包括都市生活中声音的吵杂、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存在,创造纯粹要以现实为前提;
2.在处理冗杂的试听材料时要有针对性、主题性、目的性,每个画面都有内容并为电影目的所服务,如汽车疾驰而过要么指代时间、地点的更替,要么作为故事叙述发生的场所,或者与人物的命运相系;
3.将材料艺术化、风格化,好的电影在满足故事叙述的基本要求之外,需要展现独特的审美情趣,如同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在处理暴力场景时,依靠音乐、剪辑、动作等创造具有节奏感及画面冲击感的暴力美学。总结上述三个方法,减法的原则是尊重现实、明确主题和创造艺术风格。
巴迪欧在《世纪》中说过,减法与清洗,即与彻底毁灭现实性不同,减法是要承认真实与虚假之间的距离。认识到这个联系与距离,需要一种渴望真实的情感,换言之,减法的终极是对真实的激情。
因此,笔者理解,电影中的纯粹并不是通过形式化的镜头语言就能获得,关键在于创作的信念与情感,是否有对真实的激情。正如救世主尼奥的觉醒,就是真实的激情最好的体现,使他有能力去突破母体的桎梏,质疑真实和虚假之间的距离。
因此,无限的电影真理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拍摄方式、叙事模式、艺术手法,而是要从内部直面真实与虚假的间离,并保有对真实的激情,即使拍摄的是最虚幻的科幻片,也拥有最真实的情感。
(二)拜访:保持真理
巴迪欧认为,真理在电影中的运动是拜访(visitation),拜访是理念在电影中特有的存在方式。巴迪欧此处使用的理念(Idea)一词来源于柏拉图,即真理之义,为了统一全文下述均使用真理一词。他认为真理在电影中是经过、拜访,而在绘画中是停留。
电影与绘画不同的地方在于,电影是一种关于永恒过往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过往”因“经过”才存在,而绘画只是一个瞬间。巴迪欧说,电影往往展现其“流失(loss)的力量”,因此通过在电影中并不是“看到”,而是通过“看过”某物从而得到真理。
李洋在其《电影美学的十个论题——阿兰·巴迪欧电影美学评述》中,对拜访作了相应的解释:巴迪欧用“拜访”这个词,是为了把电影描述为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也可以描述为两种陌生事物的短暂相遇。电影就是真理与感性配置的短暂相遇。
真理在电影中经过、拜访,两者有何区别?巴迪欧在提出电影是一种拜访时,同时揭示了拜访是将会听到或看到的事物在经过的程度上徘徊(linger)。因此,拜访强调的是短暂停留,且反复运动,而经过只是一次性运动,不作任何停留。
(阿兰.巴迪欧:《追寻消失的真实》,宋德超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这显然与黑格尔古典的命题“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不同。因为巴迪欧的真理对可感物拜访的结果并不是具体化为可感物,电影并不是真理的化身,真理在电影中只存在于其自身的经过中。独特的电影—真理自身就是一种拜访,它揭示了电影与其他艺术相区别的独特的运作方式。
过往、拜访作为真理存在于电影的方式,与电影是一种过程、时间化的艺术不无关系。真理在电影里是运动且仅作短暂停留的,正如救世主尼奥在母体中获得主体性的觉悟,身处母体中却能抽开身来,自如穿行在母体中一般,真理在电影中即便短暂拜访,仍不停下脚步,不被电影虚构的假象左右,保持纯粹的主体性。
真理在电影中拜访意味着真理高于电影且先于电影存在,这与电影在自身过程中产生独特的、专属的电影—真理似乎自相矛盾。笔者理解其实不然,拜访是建立在电影作为时空建构艺术的基础上,在此过程中保持真理的纯粹,减法则是建立在电影作为艺术的综合、复杂试听材料的基础上,在保持对真实激情的原则上提炼真理的纯粹。
拜访与减法在电影—真理生产的过程中是并存且循环往复的,如上文所述,无限配置是滚动的车轮,不断做圆周运动的同时向前运动着。电影内部事件的发生撕裂惯常的逻辑,通过减法去除旧有的冗杂达到电影—真理,电影—真理一旦生成就在电影建构的时空中拜访,保持真理的纯粹。
李双,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
主编:陈明
选题:任重
编辑:陆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