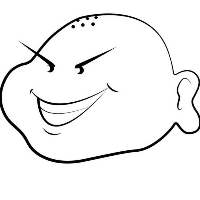绘画流派的演进,与生物进化非常相似,都同时受到外因和内因的驱动。在生物方面,比如一头鹿,狮子这一外因,使得鹿承受着自然选择的压力,它必须足够机敏和迅捷,才能生存下来。除了在奔跑中要赢过狮子,公鹿还有另一场比赛要参加——它必须长出比其他公鹿更大的角,才能获得交配机会,把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这,就是性选择。不同的是,自然选择是有节制的,对于鹿来说,只要跑得比狮子快,就足够了;而性选择却没有这样的节制,公鹿要长出比其他的公鹿更大的角才能赢,这样的竞赛规则,导致了“进化失衡”。
绘画流派也是这样。画家们的创作,总是不免受到当时的社会生活、政治、哲学和文学思潮的影响,这是外因。同时,绘画技术的进步、画家创作过程中的自发性,会形成一种新的风格。这种新的风格总是会被后人模仿、重复和夸大。这就是绘画的流派。
对于生物来说,进化的停止意味着适应,从此它可以稳定地生存繁衍。但是对于绘画流派来说,进化的停止却意味着死亡。当有一天,在一块帆布上涂抹油彩的所有可能性都被穷尽之后,新的流派不再产生,绘画作为一项艺术类别,也就宣告了自己的灭亡。

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 《秋千》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政坛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从吉伦特到雅各宾到督政府,再到1804年窃取革命果实的拿破仑,都深为统治的合法性不足所苦。所以无论谁上台,都极力强调理性、秩序,并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法国的画风因而大变,路易十五、十六时期纤柔的洛可可风格,被阳刚的新古典主义所取代。新古典主义的旗手雅克·大卫既是大革命时期的红人,又是拿破仑的首席宫廷画师,也就不足为奇了。
弗朗索瓦·布歇 《梳妆》
所谓新古典主义绘画,就是向文艺复兴的效仿与回归。相比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主义,法国新古典主义更加强调构图、透视和素描,颜色则进一步处于次要的地位。大卫的代表作《荷拉斯兄弟的誓言》,每一个线条、每一处比例,都经过严格的计算,以追求结构的严谨和稳定。背景的三个多利亚式的拱门把人物分为三组——儿子、父亲和妻女。儿子手上的长矛与父亲手上的剑,与人物张开的腿形成交叉,与垂直的拱门一起,为画面提供了稳定的结构。
雅克·大卫 《荷拉斯兄弟之誓》
类似的安排,也同样出现在他的《扈从送回布鲁图斯儿子的尸体》、《萨宾妇女的调解》等作品中。
雅克·大卫 《萨宾妇女的调解》
雅克·大卫 《扈从送回布鲁图斯儿子的尸体》
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惨败后,波旁王朝复辟,大卫流亡布鲁塞尔,并最终客死他乡。他的衣钵,由他最喜爱的弟子让·奥古斯特·安格尔继承。
雅克·大卫 《拿破仑·波拿巴穿越大圣伯纳德山口 》
安格尔的艺术天分极高,在学画前,曾在图卢兹剧院担任第二小提琴手。17岁进入大卫的画室学画,21岁就以《阿加门农的使者》荣获法兰西美术学院罗马奖,公费留学罗马。把法国最好的美术学生送到罗马去留学三年,这是路易十四国王在1663年就立下的老规矩。
安格尔《阿加门农的使者》
在意大利,安格尔深深地喜爱上了拉斐尔,并画了很多古典题材的作品,比如仿照拉斐尔的《雅典学院》创作的这幅《荷马的礼赞》。
拉斐尔《雅典学院》
安格尔《荷马的礼赞》
这一时期他画的女性肖像画,简直就是拉斐尔笔下的圣母换了身衣裳。老年时的安格尔坦承:“是拉斐尔打开了我艺术的眼界,使我顿开茅塞……”
安格尔《玛德琳·安格尔》
安格尔《赛诺内斯夫人》
安格尔也像他的老师大卫一样,做过政治投机。拿破仑1804年上台时他画拿破仑。
安格尔《拿破仑·波拿巴成为第一执政官》
拿破仑倒台后他又画《西班牙大使谒见亨利四世》、《路易十三的誓愿》等作品,向复辟的波旁王朝效忠。对此我们不必苛责,因为在大卫和安格尔的时代,还没有画廊,画家没有机会直接面对大众,绘画作品还没有二级市场,价格也就不具备投机性。他们只能靠主顾的订件过活。
安格尔《西班牙大使谒见亨利四世》
安格尔《路易十三的誓愿》
而不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还是19世纪初的法国,画家们最主要的主顾,就是天主教教堂、政府和王室贵族。安格尔向波旁王朝的效忠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次年便入选法兰西美术学院的院士。并在十年后,被七月王朝的菲利普国王——路易十三的后裔——任命为法兰西美术学院在罗马分支的掌门人,安络尔得以长期滞留意大利,直到61岁高龄才返回巴黎。
在意大利期间,安格尔的旨趣渐渐偏离了他的老师大卫。他过于强调素描和线条的准确,即便是《罗格拯救安吉莉卡》这样的主题,我们在画面上也找不到任何情感代入。这使得他的作品主题丧失了叙事性,像患了自闭症的鹿,全然漠视狮子的存在。这种与外界的隔绝,让他的作品产生了一种意义上的抽象性。
安格尔《罗格拯救安吉莉卡》
安格尔《奥松维尔伯爵夫人》
为了弥补主题的空洞,安格尔只能在作品中加入各种细节去填充画面,比如这幅《奥松维尔伯爵夫人》,衣物、发卡、镜前的小饰物,每一样东西都得到了与人物面部同等的细致处理。他说:“撇开绝对的准确性,就不可能有生动的表现。掌握大概的准确,就等于失去准确”。这样的理念,实际上也就限制了他处理宏大题材和复杂场面的能力。而这,正是他的老师大卫所擅长和喜爱的。
于是,安格尔将自己非凡的才华,全部用于探究和描摹女性胴体,从而远离了宏大叙事,他也非常乐于这样做。因为,只有美丽的女人,才能激发起他真正的创作热情。也正是在静态肖像这一题材上,安格尔超越了他所有的前辈,成为古典绘画的最后一位大师。
安格尔《维纳斯》
从1830年里,安格尔就开始构思《泉》,长久以来,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透过各式各样的胴体,女性美的深层次共性是什么,以及,如何去表达这种共性。起初,主题被设置为梳妆的维纳斯,但安格尔对这一主题反复修改,一直觉得不满意。直到1856年,这个主题才呈现为我们熟悉的样子——少女举着一只水罐。
安格尔《泉》
这幅画中充满了对比,使得整个画面生动而自洽:流淌的水与紧闭的双唇、夹紧的腿与正面的裸体。从构图上看,头、肩、胸、骨盆、腿和脚部的轴线指向不同的方向,却相互弥消,身体两端的轴线较短,越往中间轴线越长。动的感觉越来越弱,直至身体的中心——处女的阴户——达到完全的静止。女性肌肤的质感,只有安格尔才能表现得如此动人。他浸淫于此,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境地,以致于被人指责为流于色情和过于外露。但是,稳定的构图却让他的人物有一种安详和沉静的神情,二者形成奇妙的混合。安格尔笔下的女性,穿着衣服也仍然充满诱惑,裸着身体却显得十分无辜。这样的效果,实在是令人难以释怀。
温克尔曼曾说:“美就像在纯净的源头汲取清水,它越是没有味道就越是有益。” 这正是《泉》最好的注解。安格尔在技术上的尽善尽美,是古典绘画走向消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进化论有一句名言:成功是最大的失败——物种如此,绘画流派也是如此。
从1852年通过全民公决当上皇帝,到1870年普法战争惨败而下台,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的侄子,以拿破仑三世的称号为世人所熟知。在这18年间,皇帝陛下和他的臣民组织了两次世博会,并一同见证了洛克菲勒在俄亥俄州建起的首家炼油厂、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莫尼埃发明的钢筋混凝土、夏尔·柯罗发明的彩色照片,以及,玻马舍夫妇首创的百货商场。
弗朗兹·夏维尔·温特哈特 《拿破仑三世》
路易十八的总理大臣塔列朗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俏皮话:“谁没有在1789年之前生活过,他就根本没有生活过。”但是拿破仑三世时代的法国人显然不会同意这个说法。他们将会见识到内燃机、留声机、巴黎—圣日尔曼—芒特的长途电话开通。甚至汽车,只要他们比他们的皇帝多活上10年。
就这样,19世纪中叶的巴黎,生活中心从贵族的客厅被搬到了大街的橱窗里。如今,中产阶级成了这个城市的新主人。他们在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场里狂热消费,急切地想通过拥有什么而向别人证明他们是什么。仅手套一项,销量就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翻了三番。
面对这一切,法国美术界表面上一潭死水,水面下却暗流涌动。安格尔,大卫的学生,新古典主义绘画的最后一位大师,仍牢牢把控着法兰西美术学院。他恪守老师的教导——用精准的构图、含蓄的冷色,和完美的线条,来表现高超的技巧。
所谓新古典主义绘画,就是向文艺复兴时期的效仿与回归。希腊和罗马神话、圣经故事重新成为绘画主题。当时,拿破仑的失败仍然是法国人心头隐隐的疼痛,所以,圣女贞德、抗英将领、法国大革命,能够表现爱国主义的题材也广受欢迎。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这些意大利前辈们相比,法国新古典主义更加强调构图、透视关系和素描,颜色则处于进一步次要的地位。安格尔的名言就是:“在素描中包含着艺术的尽善尽美。”
但是,他的尽善尽美,并不包含真实。为了让画面具备罗马式的“理性美”,安格尔会毫不犹豫地篡改模特。比如《泉》,有好事者让模特儿摆出一模一样的姿式,发现模特的右臂根本够不着水罐。测量后发现,安格尔把模特的手臂加长了。又比如《大宫女》,被讥为“至少多长出三节腰椎”,评论家感慨道:“安格尔先生画活人就像几何学家画图形,为了线条和构图,他什么事情都干了……”
安格尔《大宫女》
轻视颜色,或用色含蓄,完全不代表安格尔在色彩能力上的缺陷。而只是怕颜色喧宾夺主,影响线条的准确和构图的效果。比如《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他仅靠光的运用,就将裙子的华美和肌肤的细腻表现得淋漓尽致。女性肌肤的质感,只有安格尔才能表现得如此动人。他浸淫于此,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境地,以致于被人指责为流于色情和过于外露。
安格尔《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
但是,严谨和稳定的构图却令他的人物有一种安详和沉静的神情,二者形成奇妙的混合。安格尔笔下的女性,穿着衣服也仍然充满诱惑,裸着身体却显得十分无辜。这样的效果,实在是令人难以释怀。他技术上的尽善尽美和难以企及,是古典绘画走向消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进化论有一句名言:成功是最大的失败——物种如此,绘画的风格亦是如此。
欧仁·德拉克洛瓦 《自由引导人民》
安格尔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手,就是以《自由引领人民》而闻诸后世的德拉克罗瓦。德拉克罗瓦虽然被雨果和波德莱尔等文人奉为“浪漫主义画派的旗手”,但他本人却非常厌恶这顶帽子。这位塔列朗——就是前面说俏皮话的那位——的私生子、18岁就考入美术学院并崭露头角的天才,心里想的可不是什么另立山头,而是取代安格尔,坐上学院派的头把交椅。他讥讽学院派绘画在安格尔的操控下,已经堕落成为“一门工艺流程十分成熟的手艺……作品丝毫不包含真实,那种内在的真实。他们教画画,就像是在教几何”。而安格尔则反唇相讥说,德拉克罗瓦的作品只是“不完美智慧的完美表现”。
这场美术学院象牙塔中的权力较量,以德拉克罗瓦的失败而告终,他六次候补法兰西学院院士的申请,均被拒绝。法兰西学院院士的身份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成为美术学院教授和两年一度官方沙龙评审委员会委员的前提。一直到60岁的高龄,德拉克罗瓦才得遂所愿。相比于他的才华,这个承认实在是来得太晚了。然而,皇帝拿破仑三世却十分喜爱德拉克罗瓦的作品。他因而得到了大量装饰市政公共建筑的订件。这令安格尔嫉妒不已。
欧仁·德拉克洛瓦 《萨尔丹纳帕勒之死》
我们比较德拉克罗瓦的《萨达纳帕拉之死》和安格尔的《奥松维尔伯爵夫人》这两幅作品,即可看出两位画家迥异的趣旨。
安格尔《奥松维尔伯爵夫人》
萨达纳帕拉是古亚述的国王,在城池即将被米底人攻破之际拒绝投降,而是将心爱的马匹和嫔妃尽数杀死,并将巴比伦付之一炬。疯狂的国王作为主角,出现在画面的左上角,视线沿着对角线投入右下角,让纷繁复杂的画面产生整体感。女人的胴体是鲁本斯式的,散发着不加掩饰的肉欲,色彩鲜艳而奔放,主题情绪激烈。更为重要的是,画面的中心是空白的床脚,这种不稳定的构图,使得观者产生画面中所有人物都向中心点跑的错觉。
而新古典主义的理念,是轮廓清晰的、色彩偏淡的,人物表情高冷,以情感外露为耻。而在构图方面,则极为强调稳定。这幅《奥松维尔伯爵夫人》是安格尔晚年的经典杰作。衣服的颜色十分素雅。作为观者注意力的中心,人物的脸部相当高,并不在画面的几何中心上。为了达到构图的稳定,即形成与人物的对视,安格尔就要靠明暗的处理来将观者的注意力向上提。为此,他将人物安排在一面镜子前,让镜子反射出光洁的后颈和鲜艳的红发卡,使得画面的上部有更多的亮色,从而获得更多的关注。
自从1855年巴黎世博会之后,两年一届的官方美术沙龙就一直在世博会的工业宫举行。每届沙龙,由40名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和法兰西美术学院的教授组成入选评审委员会和获奖委员会,对报名参展的作品进行筛选和评审。入选,对于画家来说几乎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因为沙龙几乎是作品惟一面向公众的机会。如果入选甚至获奖,即可身价鹊起。而如果落选,评审委员会会在画的内框上打上[落选]两个字,如此一来,画家就很难找到顾主了。
可想而知,因为学院派教学的高度程式化,参展作品在风格和技术上都是高度雷同的。尚弗勒里说:“我们的沙龙,是由一双可能的手从一个模型里翻出来的2000幅画。”把一幅画与另一幅画区分开来的,只有主题。另外,以前的画作必须提前订件,而沙龙里的作品是可以直接购买的。这直接导致了艺术界向腰包鼓鼓、脑袋空空的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媚俗。1856年的政府报告谴责了沙龙“肤浅的小作品适合于所有的公寓、所有的钱袋、所有的品味。” 甚至连安格尔也坦承:“沙龙窒息和腐化了对伟大和美丽的东西的感受,艺术家去参展会只是为了名利。”
1863年的沙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按步就班地举行了。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德拉克罗瓦在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仅仅五年后,就去世了。他的死,让美术学院又回到了安格尔及其信徒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是学院派枯燥、刻板、琐屑和程式化的教学,令学生们愈发的难以忍受;第二件事情是,有一个叫西约尔的评委,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拒绝像往年一样,与其他评委做默契的交易——你投我的学生一票,我则投你的学生一票。潜规则的失效让评委会方寸大乱。慌乱中,评委会应对失当,对参展作品采取了完全没有必要的苛刻标准,竟然导致了4000多幅作品落选。一时舆论汹汹,抗议声一片。
拿破仑三世,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展现自己亲民的一面。他来到工业宫,匆匆扫了一圈便得出结论:落选的画和入选的画,没什么区别。于是他降下谕旨:
1、在官方沙龙旁边再设一个展厅,展出这些落选的作品,让公众来做评判;
2、从明年起,沙龙改为每年举办一次;
3、废除法兰西学院对美术学院的监管,尤其是废除了前者对后者的教授任命权。美术学院独立了;
4、1/4的评审委会员委员由官方任命,3/4的委员由在历届沙龙中获得过奖章的画家选举产生。
皇帝一时兴起的这个决定,在第二年就见到了效果:安格尔,落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