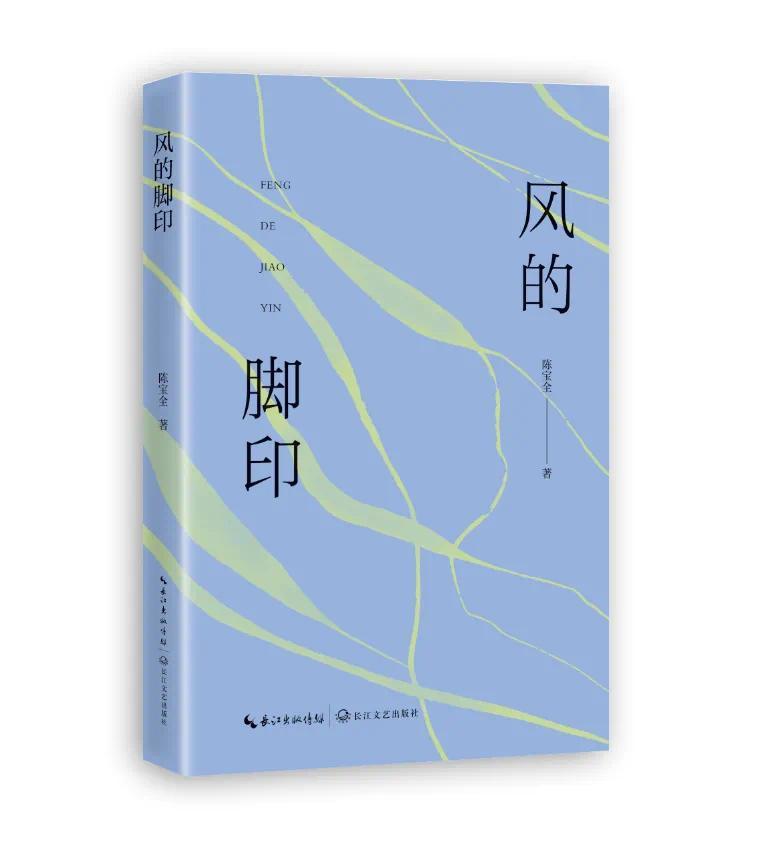
近日,市作协主席、静宁县文联主席陈宝全的诗集《风的脚印》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风的脚印》是陈宝全暌违四年之后的一部诚意之作,是一册向土地致敬,向父亲致敬,也向人类伟大情感真诚致敬的诗集。
诗集共分四辑:一场雪退回了天空、种在地里的父亲、像星辰落满夜空、阳光照在风的脸上,计有166首。整部诗集以一粒叫父亲的种子埋入大地,到意象中的归仓为线索,串连起了现实的别离与梦里的相遇、往事的回忆与瞬间的怅然,在松散无序的组合间暗含着人世间的温暖与凄冷,四季轮回的时光之河与隐隐可见的情绪起伏相互观照。诗人陈宝全就是以对亲人的朴素情感为经,以拙朴简单而富有张力的语言为纬,塑造出了一位西北大地普通平凡的农民父亲的鲜活形象,以其平实与恳切,将一幅真实而复杂的乡土中国实景呈现在读者眼前,亦为丰厚沉默的西北乡土赢得更多的荣誉和尊严。
《我在等待梦的降临》是这部诗集的后记文章。
“闭上眼,他就来了。睁开眼,他又走了”“梦真是一个奇妙的存在,它成了我和父亲相见的唯一所在”“因为父亲在天上,我开始关心一朵云、一滴雨、一片雪花的喜怒哀乐”“一本书的厚度,不足以表达我们对父亲的绵长思念”“我常想,他们像尘埃一样飘浮在大地上,我不写谁会写呢?”……
在这篇深情满满的文章里,陈宝全用诗一样的唯美语言,生动诠释弥散在字里行间关于父亲最真挚的爱。欣赏这篇美文,犹如聆听着席慕蓉作词、乌兰托嘎谱曲、腾格尔深情演唱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一种发自肺腑直抵灵魂深处的怀恋,一种穿越时空溢荡人间的思念,顺着汩汩流淌的岁月之河不断扩散延展,浸润着每一个游子的思绪,也扣动着每一个儿子的心弦,让人止不住会眼眶发热——
这部诗集是写给父亲的,也是写给天下所有父亲的;这篇后记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天下所有儿女们的。
且听风吟,且听心声——
我在等待梦的降临
陈宝全
1
闭上眼,他就来了。睁开眼,他又走了,眼角溢出眼泪。反反复复,像魇住的梦。
他是我可以在任何人面前夸耀的父亲——陈德荣,村子里的人都叫他风生。父亲去世时年届八十,尽管算是高寿了,但我接到二哥的电话,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整个人呆若木鸡,直愣愣地杵着,以为是梦——一个我不愿面对的梦。
这一切,似乎早有征兆。之前连续几个陪护父亲的晚上,在那无尽的黑暗里,我听到老鸹低沉的哀号,一波冷飕飕的风钻进了被窝。不管父亲还能活多久,我都不愿听到它的嘶叫。为了不让父亲听到,我大声地对他说话,却还是被他听到了。他说,老鸹在叫。
那天,小城的天空雾蒙蒙的,我起得很早,带着女儿去妇幼保健院配近视眼镜,打算配好了带她和她的哥哥一起去乡下看爷爷。我强烈地感觉到父亲剩下的日子不会太多——他连控制假牙的力气都没有,假牙在他空洞的口腔里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抬一下眼皮都很费力,上下眼皮黏在一起太久,出现了严重的炎症——想在他生命的最后,和孩子们见上一面。可父亲没有等到我们,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我从县城赶回家中,父亲身穿老衣——这大概是他穿过的最新的衣服,脸上苫着一张黄表纸,用麻绳束着,躺在了堂屋冰冷的地板上。趁人们不注意,我将手从父亲宽大的袖筒伸进去,摸到腋窝处,还是温热的。接着,我拉住了父亲的右手——儿时,耍社火、看戏、赶集,大概怕我丢了,父亲总是用这只手拉着我,或许他认为右手比左手更加有力、更加可靠——手已经冰凉。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我们父子一场,情深义重,这是最后一次握你的手了!”
2
父亲和大多数老年人一样,不会盘起腿坐下来享福。要是闲着无事可干,他会觉得哪里不对劲。
他把干活当成了对抗病痛的良方,遇到感冒或者别的什么病,吃上两三顿药就停下了。对他而言,如果再吃下去,药物反应比病本身还要严重。这时,他扛起农具到地里找活儿干,非干个汗流浃背不可。晚年,他患上了肾衰心衰、高血压,疾病困扰着他,但他还是希望通过体力劳动让病情有所好转。听我的母亲说,父亲一个人在地里干活,时常忘记了时间,过了饭点才回来。再后来,他连走路都变得吃力起来,遇到陡坡路就盘绕着走,很短的一截路得走很长时间。
面对病痛和死亡,他变得宿命起来,淡然置之。他深知,生老病死的进程不可逆,任谁都无法摆脱那个很确定的结局,那就是永远无法战胜死神。自始至终,他也没有以泪洗面,说一句灰心丧气的话。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他催促我们几个儿女去忙各自的事,并没打算得到什么临终关怀。当然,他没有放弃重新好起来的幻想,他不让母亲扔掉他用竹竿做的拄棍,也不让母亲把他亲手制作的旱烟送给别人,等他病好了还要抽。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父亲所能做的就是在炕上翻来覆去,通过大声或小声地呻吟来缓解身体的胀痛。外面有阳光,他晒不到;外面有风,吹不到他身上;苹果树上挂满了苹果,他看不到。他躺在炕上,透过东边的窗口,看着苔藓向埂子的高处慢慢爬去。鸟儿飞来啄食埂子上的野枸杞,还有几棵槐树巨大的树冠变换着四季,年龄比我都大。
3
你越来越像你的父亲了。这是我的母亲对我说的。父亲是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榜样式的存在,他和我的母亲都是我生命里的光。我从内心想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父亲有个好脾气,人们都这么说。从小到大,我很少听到他和别人闹矛盾或发生争执。我把父亲的待人温和和好脾气归结到他小时候放羊的经历上。他的整个少年时代,正是跟在羊屁股后边度过的。我想,如果当年他放的不是羊,而是别的什么家畜,他的脾气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
他一生信奉“顺情说好话,走过人不骂”的生存哲理,所以他很少得罪人。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生存哲理,与他做木匠的经历不无关系。他走村串户,与各种各样的主家打交道,在当年那个闭塞落后的小村庄,他算是出过远门,见过世面的人,为此,也造就了他性格中豁达、开朗、随和的部分。他常常用这句话教导我,但我终究不得要领,不会说顺情入耳的好话而招人生厌。
他没有上过学,只在扫盲班里待过几天,大字不识几个,更不要说懂乐理知识,可他对拉胡琴的痴迷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板胡二胡样样精通。在乡间,他是一个可以用音乐来表达情感和思想的人,也因此被人们高看一眼——大概受他的影响,我们家族的后生们,都特别喜欢摆弄乐器。
不干木活后,他在阳坡中学找到了一份看大门的差事,不但和老师来往密切,深得他们信赖,还能和学生打成一片。其间,他居然公私不分,除义务修理坏了的桌椅板凳外,还把我家的水泥拉到学校,修补学校的水泥院子。这些都为他挣下了好名声,多年之后,仍不时有熟悉他的人对他的赞赏传到我的耳朵里。几个已经退休了的老校长碰到我,不忘捎茶叶给他。
4
我的父亲把一生中百分之八十的力气和时间用在了修房子、打家具、给学校看大门上,我们父子待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
他干木活时,常年奔波在外,一年当中只在春播秋收最忙的季节,才回家帮母亲料理几天农事。多数时候,他回来我睡着了,走时我还在梦中,我大概已经忘记了父亲年轻时候的样子。但他把身上潮湿的锯末味留在了屋子里,也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父亲在中学看大门时看上去已经很老了,我已参加工作。那时,我还不懂“子欲孝而亲不待”的道理,很少回家。好在我们父子关系并不疏远,每次回到老家,我都会和两个老人睡在一起。他是一个可以坐下来和我闲聊的父亲,有时候我们会聊到第二天黎明,似乎要把以前的缺失补回来。半夜,母亲从梦中惊醒,催促着说,睡吧睡吧,你两个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和父亲朝夕相处的日子只有五年,那时,他和母亲来县城帮我带孩子,我们有过许多次印象深刻的对话。他不会直接说我做得对或者错,仍旧会绕很大的圈子给我讲做人做事的道理。有些我听进去了,有些没有,但总体,我在他那里得到了很多宽慰,为我的各种失败找到了合乎情理的借口。他的好多话将让我终身受益,时常还在耳际萦回。
尽管我做了情感上的恶补,但在我们几个孩子中,我还是非常羡慕二哥能和两个老人一起生活那么多年。二哥除了去兰州打工的半年,其余时间都和老人在一起。有次我和二哥喝多了酒说起孝道上的事,我敬了他,他做的我和大哥永远做不到。大哥高中毕业后在省城一家安装公司上班,只在春节回家一趟,几天时间又走了。好在他离职回乡种地后,有了和老人相处的机会。其实,我也羡慕我的姐姐,她嫁得近,和我们一个庄子,而且称得上是邻居,中间只隔着两户人家,得空她会去老人那里,说说话、洗洗衣物。
父亲被埋进了大哥家旁边的果园,我又羡慕起大哥来,一出门就能看见父亲的坟园。我在诗中也写到过,父亲只要一伸手,就能端上大哥家热气腾腾的面条。
5
父亲刚刚离开我们的时候,我陷入无尽的悲痛当中,那段时间,我关紧窗户,不让风吹走房子里本来的味道。也就是在那时,我决定要写一本悼念父亲的诗集。尽管每写一首与父亲有关的诗,都令我痛苦难挨,但我还是坚持写了下来。
写这些诗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想,父亲走路响动大,脚步声带着重重的尾音,但走得快,他会越走越远。我尽量多写分行的文字,它们不可能像一堵墙,拦住他,但至少会蜿蜒如长长陡陡的台阶,拖住他离去的脚步。
或许因为才华的缘故,有些诗作无法与阅读者达成共情,但请相信,我的表达足够真诚,并非矫情。我知道我们每个人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父亲,但愿这一刻,我们感同身受。
我不想说时间是一剂良药,但不得不承认,在我们因为悲伤而流泪的时候,时间陪着我们哭泣;可远方的时间在路上嘲笑我们的悲伤。果然,我后来不怎么难过了,居然无耻地平静下来,死亡成了我们嘴边很平常的词儿。
以后我也许不再写到父亲——每写一首诗怀念一次父亲,父亲就像雪人一样融化一点。现在,他只剩下了一个并不高大的背影——我担心再写下去,他会一点一点消失在视线尽头。
一本书的厚度,不足以表达我们对父亲的绵长思念。我只是想通过这些分行的文字,把躺下去的父亲扶起来,让他被黎明时分的阳光照到,被山野里的风吹着;让他笑,让他哭,就好像他不曾离开我们。
6
梦真是一个奇妙的存在,它成了我和父亲相见的唯一所在。
人都说男人的梦记不住,的确是这样,好多梦醒来就忘。不过,与父亲有关的梦,我都记下了:梦见他在梦中又死了一遍,醒来时枕巾洇湿了一大片;梦见他说他有炉子没有烟筒,我亲手为他用纸糊了几节,周年祭的时候在坟头烧了;前不久,又梦见和父亲视频,他在一个什么地方看大门,住的屋子像是一座坟墓,有着拱形的屋顶,屋顶上有一行字,他指着“穷”字说“到处有穷人”,我想父亲可能缺钱花,就去他的坟园烧了一摞纸钱。
我想,我还会再次梦到父亲,我希望做这样一个梦:这些文字变成小草小花,簇拥着他摇曳。这些诗行一如岭子梁的土台阶,他拾级而上,微笑着向我走来。我们站在高处,俯视晚霞下他曾经生活过的如梦如幻般的村庄,还有椿树边上我们的家。
因为父亲在天上,我开始关心一朵云、一滴雨、一片雪花的喜怒哀乐;因为父亲有时来梦里,我总想让夜晚加倍地长……
7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但我有时感觉他还在我们身边,看着我们生活。遇到难过的事,还有一种想打个电话说说话的冲动。我的孩子也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他们的爷爷,儿子时常回忆起爷爷戴着草帽、在下午的阳光下吹着哨子训练他跑步的情景。在我因想念父亲而忍不住流泪的时候,他会静静地握着我的手,陪在身边;女儿配的眼镜坏了舍不得扔,她说那是爷爷去世当天配的。爷爷的照片也被她偷偷夹在了日记本里。每次回乡下,她总背过我们去坟园给爷爷磕个头……
不过,相比于父亲刚走那会儿,情况好多了。我们开始接受父亲离去的现实,从悲伤的梦中走出来,在阳光下努力生活。这大概也是父亲愿意看到的。
这本诗集为怀念我的父亲而写,是我近三年来部分新诗的结集,分为四辑,以一粒叫父亲的种子埋入大地,到意象中的归仓组接成整部诗集的基础骨架,写到了现实的别离与梦里的相遇、往事的回忆与瞬间的怅然,看似松散无序的组合间暗含着凄冷与温暖、四季轮回与情绪起伏的相互观照。书中也写到了我的母亲,但并不多,她的故事以及她和父亲的过往,会在另一本书里有所表达,我也不确定何时讲给大家。我常想,他们像尘埃一样飘浮在大地上,我不写谁会写呢?
好吧,这本诗集就在这里了,我希望它是一本这样的书:捧起它,就能听见父亲敲门的声音;打开这本书,就像推开一扇门,看见父亲在田野里、在屋顶上、在云雾间、在一缕缕的风中;合上它贴在胸口,就能感受到父亲微弱的心跳;寒意袭人的夜晚,枕着它入睡,就能听见父亲的鼾声。那时,我在等待梦的再次降临,等着他剥开尘世的包浆,从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捡起三岁前的我,抱进怀里。
在诗集的整理出版期间,得到了许多跟我交往多年的老师和朋友随时而坚定的支持和鼓励,尤其牛庆国先生付出大量心力,为我的诗集作序;王发昌先生百忙之中,为诗集作画插图。殷殷之情,未敢少忘,在此,致以深挚的谢意!
作者简介
陈宝全,甘肃静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九届高研班学员,入选甘肃首届“散文八骏”。曾获“黄河文学奖”“崆峒文艺奖”等多种奖项。已出版诗歌集《看见》《心生繁花》《等于鸟鸣》3部,散文集《被一颗苹果喜欢过》1部。
(静宁县委宣传部官方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