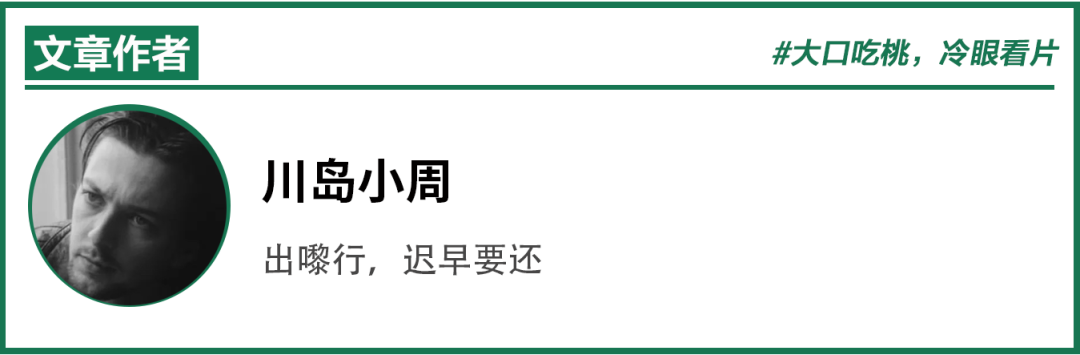
特别顾问:余得利
天寒地冻的夜晚,你叼着烟走进街角的黑网吧,两只冻裂的手伸进裤兜里摸出皱巴巴的二十块钱,说要包夜。
拿到上网卡之后,你穿过浊重的空气、呆滞的人群,一边偷瞄别人屏幕上激情四射的“战况”,一边物色比较遗世而独立的机位,然后坐下,熟练地打开浩瀚无垠的某某站,熟练地敲下酝酿了一个礼拜的两个字,搜索。
然而,只看完前20分钟,你就感到索然无味,关掉了视频,转头去豆瓣给这部电影打了两星。
这部电影叫《苹果》。甚至有人把短短三场连床都没有的床戏剪出来,丢到某站上。
没有人在乎这部电影讲了什么,感觉就像你堆了一个雪人,但是大家都说雪人的鼻子是一根j8。
《苹果》被当成毛片来看,可能是影视界最大的冤案之一。
这个海报很有迷惑性,冰冰的眼神和大为的裸背好像在暗示这是一部有番号的成人电影。而实际上,它讲的是一个洗脚妹在北京的生死疲劳。
这不是一部赤条条的pornography,而是一部赤裸裸的现实主义电影。
有人跟李玉说:上世纪80年代,你拿只铅笔在北京地图上随便一划,10家有8家是机关单位;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拿支铅笔一划,10家有8家是洗浴中心。
《苹果》就是讲当时最普通而普遍的一种人,洗脚妹。从洗脚妹身上去窥视底层女性受苦、受辱、受难。
受苦是生活的基调。电影一开头,一个好不容易接到单的street girl因为多说了两句话而得罪老板,这一天生意没有了。感觉就像打工人因为左脚先迈进公司而被开除。
镜头接着尾随这个趾高气昂的老板走进一家“金盆”洗脚城,一路偷瞄房间里的洗脚妹。老板并不是来做慰问工作,而是在豪华套房里跟猪朋狗友们打牌。
这一边大把的钞票撒来撒去,另一边成排的洗脚妹闷头赚辛苦钱,还要被有脚气嫌疑的老脚上脸调戏。
苹果在这样乌烟瘴气的环境里,一边为了给家里省下一笔水费而在洗脚城洗澡,一边跟小姐妹做着赚笔钱回老家买房的白日梦。
还讨论了一下用假的处女膜敲一笔卖春的钱
回到阴暗潮湿的老破小出租屋,房间小得支开一张床都费劲,你都分不清那些堆在墙角的杂物是废品还是衣服。
就连看起来应该是“享受”的激情戏,都挤在又臭又黑的土墙厕所里,像动物一样。
自己去看
苦吗?苦就对了。吃得苦中苦,未必能成为人上人,但一定会让你的耐击打能力值拉到最满,哪怕受辱。
受辱最极端的形式是被强奸。而当这个人是苹果的老板时,她其实遭受着权力和身体的双重强奸。
事情的起因是苹果唯一的知心闺蜜小妹因为不让客人乱摸而被开除了,两个郁闷的洗脚妹在路边大排档喝酒骂老板“傻逼”。苹果喝到东倒西歪还要接着上工,在休息室眯一会儿的工夫让老板扒了衣服,一边说不是故意的一边动手动脚。
更难受的是,让在擦玻璃的老公亲眼目睹了,场面堪称恐怖。
“贫贱夫妻百事哀”,苹果的老公安坤看到这件事的第一反应是打人,洗脚城的老板打不过,就回家追着苹果打。第二反应是要钱,老板不认账,他去找老板娘,老板娘主动提议要钱是不可能的,反手给老板一个绿帽还行。然后安坤居然就把老板娘睡了,这个剧情走向实在太诡异。
后来苹果怀孕了,洗脚妹变成"代孕妈妈",而安坤又有了全新的索赔动力,准确来说是跟老板对赌。孩子生下来是老板的,就让他买走;如果不是,安坤就闭麦。最荒谬的是两个男人蹲在天台讨价还价,跟卖猪肉似的。
受难是从生孩子开始的。
孩子生下来,安坤擅自改了血型,拿到十二万。
而苹果只能以保姆的身份照顾孩子,而且约定半年之后就彻底离开。与此同时,老板一直断不了对她的“性趣”,老板娘一直非常敌视,丈夫安坤一直怀疑苹果不忠,甚至大街上把她打了一顿。明明是受害者的苹果彻底变成了众矢之的。
后来安坤脑子一抽,觉得自己的孩子还是要自己养,就把苹果绑起来,偷走孩子。老板一顿操作,报警抓人,结果终于发现孩子不是自己的,瞬间猛男落泪。
东窗事发,苹果左右为难。在这个当口儿,被洗脚城炒掉之后沦为站街女的小妹被🐞客杀死。小妹冰冷的尸体就是给苹果的当头一棒,她终于意识到这是一座吃人的城市,匍匐在底层的她们一不留神就会被吃掉。也许某一天,躺在停尸房的就会变成苹果自己。
电影里,苹果最后还能及时止损,带着孩子离开了,而现实中有多少人能这样说走就走?
《苹果》不是一部精巧的电影,又脏又乱,灰蒙蒙一片,情绪比台词要丰富,手持镜头晃到头晕,一看就是禁片制作水准。
但是导演李玉对这部电影的定性是文艺片走商业制作的尝试,那两年正是所谓文艺片与商业片之争甚嚣尘上的时期,因为2006年《疯狂的石头》大赚了一笔票房,让很多导演看到了希望,独立电影出身的李玉就是其中之一。她试图调和文艺与商业的矛盾(在《苹果》之后还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体现在《苹果》上就是启用当时走偶像路线的佟大为,让他去演一个痞里痞气的民工,另外就是启用范冰冰。
进组前👆进组后👇
也不知道为啥,冰冰特别信任李玉。她为了演这个角色,在洗脚城待了一个月做临时工,和洗脚妹同吃同住,还每天早上一起唱《洗脚城之歌》。
“演洗脚工很尴尬,我自己去泡脚都很少让洗脚工洗脚,看她们蹲在那里很不舒服。我曾问过洗脚妹,她们说刚开始干的时候都只按摩客人的身体,直到一个星期之后才开始为客人捏脚。我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为了克服这个心理障碍,我几乎把剧组人的脚都洗遍了。”
电影的拍摄说得上是十分顺畅,只花了一个多月,但争取上映却是漫长又艰难。《苹果》原名叫《迷失北京》,但是领导认为“迷失北京”带有政治意味,影响不好,所以改名。
部分dvd还保留了英文Lost in Beijing
改了片名,电影局还有一条审查意见写着:不应容许这部电影对时代有侮辱性的描写。
什么叫“侮辱性的描写”?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李玉对这部电影最初的设想是“生死北京”。千禧年前后的三里屯跟现在的样子天差地别,因为靠近大使馆,所以这里聚集了最早的一批酒吧,十块钱左右一杯酒。在昏暗的酒吧里,又聚集了最早的一批独立音乐人,比如崔健。
Shadow酒吧,1996
现在的三里屯整洁、时髦、光鲜,而当时涌动在平房小巷里的人群有买醉的青年、卖花的小女孩、发臭的乞丐、严肃的作家、疲惫的脏摊儿小贩、大打出手的情侣、拽里拽气的摇滚歌手。大概有十年的时间,这里几乎没有任何规则,人们毫无顾忌,有时像天堂,有时像地狱。
2004年传出整改计划之后,罗大佑特地在“乡谣”酒吧举办了最后一场酒会,向这个地方告别。随后很多人宣布,三里屯“死于2005年开始的拆迁”。混乱但自由的时代结束了,人们缓缓滑入一个有序却冷酷的时代。
罗大佑是“乡谣”的老熟人
在追踪这个房屋与精神双重拆迁的过程中,李玉很快就在破墙烂瓦之间发现了北京的另一副面孔,感觉就像电影里,苹果走进胡同深处才能看到满墙的小广告。所以《苹果》捕获到的北京影像是肮脏污秽的,像从下水道流出来的,却又十分真实。
尽管导演李玉认为“《苹果》跟时代有关系,它能够拓展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认识”,但最后还是修改了五次,删减了二十几分钟才拿到龙标。
李玉说:“我以前也有很多愣头青式的‘坚持’,但是在中国,如果你在你的有生之年还要做电影,懂得有智慧地迂回,不放弃自己的表达,比什么都重要。”
《苹果》在香港公映时被定为三级片。2007年11月,恰好也撞上了《色,戒》上映。大家都拿这两部电影对比,对比什么呢?床戏。而且只对比床戏,有人说《色,戒》的比较唯美,《苹果》看起来很脏,说得好像两部电影所有镜头都在滚床单似的。
而且当时的媒体也非常“敏锐”地揪住了《苹果》的激情戏大肆渲染,影片想要表达的对底层人士的关怀被彻底忽视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苹果》和《色,戒》在大众的认知里都变成了撸管用的毛片。
早期的李玉在拍边缘女性的方面是有天赋的,比如《红颜》,讲一个小镇上名声不太好的川剧花旦和一段复杂的母子关系,很多人说这是华语最好的女性电影之一。
后来拍《苹果》把镜头转向了城市。某种程度上,城市比小镇要残酷,因为这些在“生物链”最底端的人群长期处于失语的状态,尤其是女性。
在城市里挣扎的底层女性,这类题材的电影非常少。《海鲜》算一部,最后一段的剧情是一个无良嫖客把钱塞在站街女的私处里,取出来之后发现是假钞。《万箭穿心》也算一部,拍的是一个武汉挑扁担的女工。武汉曾经有十万个扁担工,却只有这一部电影。
《苹果》有一条本应该非常显眼的副线,就是沦为站街女的小妹。删减之后,这条线没头没尾,小妹变成幽灵一样的角色,突然出现,突然消失,最后暴毙。这样的叙事恰恰照应了这类人群、这类电影的命运,被藏在主流视线之外,这是华语影史的遗憾。
这样一部现实主义佳片,如今只能在某站里回味,实在太难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