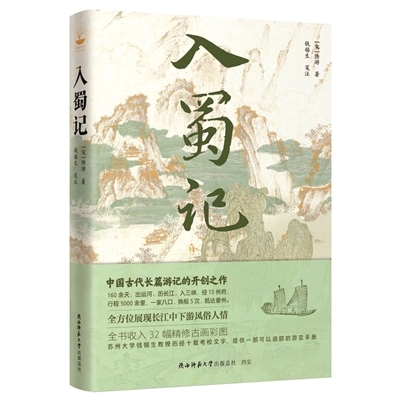
◎唐山
1171年7月3日,45岁的陆游携家眷出发,作别家乡绍兴江阴(今属浙江省绍兴市),去夔州(今属重庆市)当官。
陆游没意识到,这将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时刻:此后160天,行程5000余里,换船5次,一次遇险,一次搁浅,穿越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七省市,经吴越、荆楚、巴蜀等文化区,最终写出了《入蜀记》(陆游著,钱锡生笺注,陕西师范大学总社出版,2024年10月),它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游记”。
此时,陆游更纠结于两个问题:
首先,自认年迈,已惧远行,即“少年亦慕宦游乐,投老方知行路难”,这次旅行真有必要吗?
其次,仕途多艰,陆游少年科举屡败,后得推举,36岁受赐“同进士出身”,38岁被排挤出朝,得张浚提拔,40岁当上八品通判,又因张浚失势,不久被罢官,在家赋闲4年后,终于等来再被征召,却还是八品通判,且远在夔州,倍感“但忧死无闻,功不挂青史”。
其实前一年的12月25日,陆游便收到了任命,因生病,拖了半年多才上路。
只看《入蜀记》,如老僧入定,波澜不兴,明末萧士玮称“随笔所到,如空中之雨,小大萧散,出于自然”,编《四库全书》的馆臣也称其“雅洁”。可陆游同时期写了数十首诗,每首都很情绪化,比如出发前给好友梁克家写的《投梁参政》:
流离鬓成丝,悲吒泪如洗。
残年走巴峡,辛苦为斗米。
《入蜀记》是一个悲愤者写下的安静文字,只是少有人能明白:陆游为什么要这么写。
千年演化才有了行游日记
“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说:“陆放翁《入蜀记》,有酷好者。夫无意为文,文之至也。状物适状其物而止,叙事适叙其事而止。不增不减,自尔错落,然是通神明、类万物,古今称谓,信笔淋漓,乃能物如物、事如事,而成至文耳。”
方以智这么说,是基于文学史视角:从日记到行游文学,经历了上千年演化,至《入蜀记》始有大成。
日记出自起居注,史官逐日记录帝王言行,一是作为撰修国史的基本材料,二是存留帝王嘉言,以教化后人。此传统始于周代,现存最早文本是东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记录了建武三十二年(56年)正月,汉武帝刘秀至泰山封禅的全过程。
《封禅仪记》体现出早期日记的特点:它是写给别人看的,有强烈的舞台感,“我”被排斥在外……这使它无法成为文学。
唐代李翱的《来南录》是日记发展的另一个里程碑,从写君主变成写“我”,由此带来的困境是:“我”有什么可写的?《来南录》记录了李翱在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全家从洛阳到广州的行程,历时半年,仅1000多字,所记皆治病、宴饮之类生活琐事,胜在文笔典雅、从容不迫,让人看到:“我”其实也可以成为叙述对象,也能写得有趣。
接下来是北宋欧阳修的《于役志》、张舜民的《郴行录》等,陆游在写《入蜀记》时,受到了这两部作品的影响。《于役志》记录欧阳修被贬官后,从汴京到夷陵(今属湖北省宜昌市)的旅途见闻,即“行虽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亲旧留连”,但记录自己参加宴饮的内容太多,被讥为“酒肉账簿”。《郴行录》记录了从汴梁到郴州的沿途风光,“凡风景佳胜处,几游历殆”。与李翱的《来南录》不同,这两部作品不再纠结于“我的行程”,聚焦于“行程中的我”。但《于役志》《郴行录》未彻底解决“我有什么可写的”的困境,为避重复、单调之病,篇幅均不长。
《入蜀记》能成为里程碑,因文本上有突破。
宋代行游类日记作家大多有治史背景,如欧阳修、张舜民、黄庭坚、范成大、吕祖谦等,陆游也三任史官,修过《两朝实录》《三朝史》,并著有《南唐书》,熟悉当时日记体的文本规范,即必须呈现出“日记的史学传统”,在此镣铐下,陆游依然能“把‘我’讲丰富”。
陆游找到了新的平衡点——让“我”来讲历史。行游日记由此从客观走向主观,从记事走向文学。
真正想写清的是“我是谁”
陆游对《入蜀记》相当看重,嘱其子:“如《入蜀记》、《牡丹谱》、乐府词本当别行,而异时或至散失,宜用庐陵所刊欧阳公集例,附于集后。”《入蜀记》不是完全的文学作品,不能只看文学价值,它真正关切在:转型时代中,人该如何找到“我”。
宋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
一方面,经济空前繁荣,如史家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的作者)说:“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另一方面,富裕未转化为强大,反成诅咒,“贫穷却强大”与“富裕却弱小”俨然只能二选一,即文天祥所说:“闻古今天下能免于弱者,必不能免于贫。”
陆游生于北宋灭亡之际,即“我生学步逢丧乱,家在中原厌奔窜”,少年时“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可他们的忠诚不被理解,他们的努力皆付东流。陆游的老师曾几主战,长期遭排斥,晚年赠诗给陆游:“问我家居谁暖眼,为言忧国只寒心。”至于陆游自己,蹉跎至40多岁,仍一事无成。
如果注定无法融入现实,“我”还是真实的吗?我存在的意义何在?通过《入蜀记》,陆游传达出三种声音。
其一,山水的本质是人文,江山如画,是因前辈将生命融入其中,此外无风景。故至池州思北宋由此灭南唐,见北固山“狠石”念蜀吴在此结盟抗曹,游天庆观寻岳飞父子画像……《入蜀记》记人文景观100种,自然风光仅16种,穿行于“残山剩水”,成为陆游串联英雄传奇、为自然附魅的过程。
其二,坚守文明,在真山真水中读懂诗意。《入蜀记》引前代诗文180多处,116处有评价和考证,几乎是打着游记幌子的诗论。其中隐含着陆游的立场:文明屡遭挫折、羞辱后,仍应坚信其力量。在陆游看来,宋人工稳、精致不逊于唐,却乏李白的张扬、豪迈,所以全书引证唐诗64处,李白诗占34处,杜甫诗占12处。由此突破“宋人诗话,传者如林,大抵陈陈相因,辗转援引”之弊。
其三,开阔视野,以山水养气。陆游曾说:“文以气为主,出处无愧,气乃不挠。”“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在《入蜀记》中,颇录奇物、奇俗、奇景,如“物长数尺,色正赤,类大蜈蚣,奋首逆水而上,激水高二三尺,殊可畏也”,不知何物;另记木排托起的水上城市,“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鸡犬臼碓皆具,中为阡陌相往来,亦有神祠”,有“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况味。
三种声音相加,“我是谁”之问豁然开朗。
两个陆游谁为真?
雅各布·布克哈特在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称“文艺复兴之父”彼得拉克的游记开启了“人的发现”——站在古代建筑面前,我们会意识到,一切不全由上帝创造,历史也是创造者。此论有争议,但呈现了一个事实:近代转型从旅游开始,旅游使人靠近“我”,对人生苦短有了紧迫感,从而在逃与冲之间做出选择。
宋代的富裕也推动了旅游,宋人赵季仁说:“某平生有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
值得关注的是,《入蜀记》中的陆游,与入蜀之路上诗篇中的陆游,反差惊人。在归州(今属湖北省宜昌市),陆游拜谒了寇准当年修的秋风亭,写下诗句:
江上秋风宋玉悲,长官手自葺茅茨。
人生穷达谁能料,蜡泪成堆又一时。
以古托今,痛彻骨髓。可在《入蜀记》中,陆游却淡淡地写道:“谒寇莱公(寇准)祠堂,登秋风亭,下临江山。是日重阴微雪,天气飂飃,复观亭名,使人怅然,始有流落天涯之叹。”
宋制,官员赴任需先到吏部领告身(古代授官的凭信)、官印等,还需向皇帝、宰执、御史台辞谢,陆游在临安(今杭州)待了10天,仅记290字,可见办事不顺畅。在离开临安的船上,陆游突然记下:
是日便风,击鼓挂帆而行。有两大舟东下者,阻风泊浦溆,见之大怒,顿足诟骂不已。舟人不答,但抚掌大笑,鸣鼓愈厉,作得意之状。江行淹速,常也,得风者矜,而阻风者怒,可谓两失之矣。
如此有趣的细节,全书仅两三篇,不是陆游不会写生动,而是诗可以兴观群怨,行游日记在当时属于史,受记史文体所限。只能暗藏褒贬。
《入蜀记》中,陆游还记录了他和秦桧孙子秦埙的交往,秦埙甚至送药到陆游的船上。《宋史》称陆游早年因科举成绩高于秦埙,被秦桧所恨,致名落孙山,此说不确,秦埙科举只得探花(第三名)。但陆游的爷爷陆佃主战,因秦桧而断送仕途。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对秦桧一家极尽讽刺,在《入蜀记》中,却无丝毫情绪。
古代文体丰富,不同体例的行文方式完全不同,如今统一称为散文,文体间的差别被掩盖,随着形式消失,“思想内容”成了唯一标准,可“思想有深度”不等于“文体美”,哲学判断压倒文学判断,揣摩古人之意趣便成难事,我们反被自身传统关在门外,甚至已读不出《入蜀记》之妙。
于是,阅读《入蜀记》的意义就在于:让人文江山之美,带我们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