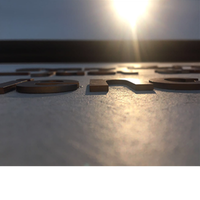人人有个大观园,芥子须弥一念间
《禅解红楼梦》
陈嘉许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年4月1日出版
青少年时代看《红楼梦》,常常有很深的代入感,对葬花、撕扇、焚稿这类小儿女情事印象深刻,甚至不忍心细看后四十回,只想沉迷于纯净的大观园世界里。
时到中年再读《红楼梦》,会在熟悉中感到前所未有的陌生与茫然,若将小说里的“世情”与人生经历参合,顿觉悲剧意味清淡了很多,比如“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这类词句,明显不如《好了歌》来得亲切,而书中出现的“一僧一道”,拥有决定贾、林、薛命运走向的能力,却能忍住不插手,眼看着贾府在不断增熵中走向崩溃,这份定力是很让人佩服的。
视《红楼梦》为“悲剧中之悲剧”,始于王国维先生,他审视《红楼梦》的理论框架,源自德国近代美学,站在中西文化交轨的角度看,“悲剧说”无疑是一项了不起的成绩,也因此成为百年红学的起点之一,我们每个人,有形无形之中,都曾受到过这种观念的熏陶和浸润。
然而,这也给《红楼梦》刷上了厚厚一层暗色的漆,让读者一点都轻松不起来。假如换个超脱的思路,将《红楼梦》理解为“红尘一梦”,观感会迥然有别。
陈嘉许《禅解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一书,就是从这里生发开来,别辟蹊径,以禅理解读全书,提供了另外一种阐释《红楼梦》的可能性,也让我们再次见识了这一经典文本的深厚底蕴。
《禅解红楼梦》引证佛家之说,认为整部书都是曹雪芹“修行悟道”的体验,在传统索引派的基础上,做了堪称颠覆性的工作。在陈嘉许笔下,《红楼梦》中的人名、物名,乃至关键情节、整体构架,无一不是曹雪芹体悟世间的见证。如此一来,所谓《红楼梦》的悲剧内涵,纷纷融入修行人的主观设定之中,就好像是精心安排好的一场游戏、一场棋局:
“《红楼梦》写的其实就是一个人,一个修行人,他盖起了红楼,他玩了一系列的修行游戏,最后红楼也不要了,在修道这条路上,他终于得到了无数修行人梦寐以求的‘成就’,其实是什么都没有得到,因为有得有证无非半路风景。”
这样来解读《红楼梦》,或许让人感觉离经叛道,但回到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路径上,“禅解说”并非无源之水,来自释道两家的劝善、警世思想,几乎就是传统小说必不可少的盐分。尽管我们一度目之为庸俗,终归不能否认它们在古人精神世界里植根极深,当时的人离开这一思想土壤,几乎寸步难行。
明清之际,通俗文学蔚为大观,士大夫们主动投身创作,以当时禅风之盛,他们对释道思想的理解无疑更为高蹈,汤显祖以进士身份写下“临川四梦”,其中《南柯记》和《邯郸记》就源自脍炙人口的“南柯一梦”、“黄粱一梦”。仙佛入戏,虽然难免“戏不够,神来凑”的差评,却由此意外生成间离效果,且给通俗文学框定了先忧后乐大团圆的固定套路。
另外一个著名案例来自清初的金圣叹,他硬生生将《水浒》截为七十回,改成“梁山泊英雄惊恶梦”的大结局,还把传世《西厢记》第五本去掉,同样以“惊梦”收尾,可见在金圣叹的创作意识中,“梦”其实是出世与入世之间的一道传送门。
曹雪芹家族世居江南,流风所被,他对禅理的了解必定不逊于时辈,小说中主要人物,无不具夙世善根,与推崇老成厚重的儒家主流相去甚远,在第二十二回中,贾宝玉“听曲悟禅机”,继而和宝钗、黛玉、湘云讨论禅宗六祖故事,按照《红楼梦》的设定,几位主人公不过十几岁年龄,居然能像老僧一样立偈语、解公案,实在匪夷所思,只能说是曹雪芹寄托所在,刻意为之了。
回到《禅解红楼梦》一书,这样大胆抉疑,对《红楼梦》进行全方位解构和结构的,确实少见。如是读红楼,无异于换个角度观照作品,也观照人生。人人有个大观园,芥子须弥一念间,曹雪芹的苦心孤诣,想必不全在“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于俗世的厚重压力与变幻无常中,记录下明心见性的灵光,又何尝不是文学的价值呢?
本文首发于《新民晚报》2019年07月21日 星期日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