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江先生的《钱锺书传》按时间顺序将钱锺书的一生划分为早年生活和求学、意园神楼、沧浪之水、槎通碧汉、群峰之颠五个阶段,将经历与著作交织考索,做出自己的解读,尤其从结构系统的角度分析了《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著作,本文是关于钱先生著名的“围城”意象的解读,澎湃新闻经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发布。
钱锺书一生有着多方面的成就,其大类有二:作家与学者。如果作为学者的钱锺书可以用《管锥编》《谈艺录》为代表的话,那么作为作家的钱锺书只能以《围城》为代表了。《围城》是作者一生写成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其地位无可替代。钱锺书在写作《围城》前,还有散文随笔和短篇小说的创作,这些创作都可以看成写作《围城》的准备。它们包含的创作信息,至《围城》初步成象。钱锺书写完《围城》就感到不满意,则这一形象应当有所变化,那就是第二部长篇小说《百合心》了。
钱锺书写完《围城》后,还不满四十岁,还有足够的创作冲动和能力,以钱锺书“不断叩向更上一关”的精神,第二部应该胜过第一部。钱锺书评论《百合心》时说:“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象它酸,也很可能想象它是分外地甜。”《百合心》应当符合作者“分外地甜”的信念。不仅如此,《百合心》还未必达到高峰,钱锺书还有创作其他长篇的可能,大致延续至1957 年与完成《宋诗选注》的时间相齐———也许钱锺书这时才会真正转移兴趣———那才会是钱锺书小说的真正高峰。然而,钱锺书在完成《围城》后,1949年在搬家的忙乱中遗失《百合心》手稿,以此为契机,钱锺书“由省心进而收心”,就此中断了小说创作,这极为可惜。但也因为如此,反而使本来多少具有实验性质的《围城》就此保存了创作方面的全部信息,在钱锺书著作系统中屹立不变,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钱锺书开始写作《围城》,是在1944年的上海。那一年钱锺书和杨绛同看杨绛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钱锺书突然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很高兴,催他快写。当时钱锺书在修订《谈艺录》,又在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于是杨绛在多方面给予帮助:她让钱锺书减少授课时间,进一步节省本来已经节省的生活,并且自己兼任女佣的工作,甘心情愿地做“灶下婢”。这样,钱锺书才得以集中精力,在1944年至1946年两年之内,“锱铢积累”地写成了《围城》。《围城》最初在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上连载,之后在1947年出版单行本,1948年、1949年重印,大受社会的欢迎。
杨绛指出:“锺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题材全属虚构。”钱锺书观剧回来发兴写《围城》,只是具体的触发。而小说的种因,却相当久远。如果以钱锺书1938年夏的归国为界,对此远因的追溯,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后两部分的接续是长期的打底,而后一部分则渐渐成熟为小说。如果没有对社会和人性(作者所谓“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的长期观察,如果没有对婚姻恋爱的体悟和观照以及对大学生活的体验,《围城》的写作就不可能顺利。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极长期也极复杂,难以言说,这里的交织和相合,来自一点一滴的积累,绝无速成之理,然而也能稍稍找到一些早年因素。
正如钱锺书在大学时代遍读宋以后集部,是他以后撰写《谈艺录》的前导;钱锺书在大学时代对大学生活的体验以及对婚姻恋爱的观照,也应该是后来《围城》小说的前导。1933年,钱锺书从清华大学毕业,他在毕业年刊上写了一篇《后记》,其中说:“真正直接描写中国大学生活的小说至今还没有出现”,这里是不是有点微微透露《围城》的先声呢?而如果把钱锺书归国后的经历和小说对照,可以看出两者基本相合:
1938年,钱锺书和杨绛同船回国,船上的情形和《围城》里写的很像。那是小说的第一章。
钱锺书出国以前在上海的经历,辅之以1939年夏、秋的自昆明回沪探亲,可以相关小说的第二、三、四章。
1939年秋,钱锺书未回昆明而到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去了。他把从上海到湘西的旅途所经写进了《围城》。那是小说的第五章。
钱锺书在湘西教书两年,所遇到的一部分丑恶的人和事,构成了《围城》的素材,真实地进入到角色中去。那是小说的第六、七、八章。
在湘西的两年中,主要是写作《谈艺录》的时期,也是完成《围城》构思布局的时期。而钱锺书1941年回沪探亲后困顿于上海沦陷区的经历和情绪,对于完成小说第九章并且最后确定书名为《围城》,有着重要关系。有此一笔,以贯通小说的题旨,则全盘皆活。
钱锺书归国后,没有回上海,直接到西南联大去了,这是作者经历和小说不对应的一段。论者也指出:在《围城》中找不到联大人物的形象。西南联大真的和小说完全无关吗?联大的一些人和事是不是也化入“国师”得到了描述呢?钱锺书在离开联大时一度不很愉快,也许将来会有人揭示这里的关系吧。
钱锺书晚年在谈到《围城》时引用康德的话:“知识必自经验始,而不尽自经验出”,断然否定了关于《围城》是“自传”的猜测。但是,钱锺书的生活经历还是和小说密切相关,唯其积累丰厚,所以能在两年时间内“锱铢积累” 地写成,基本属一气呵成。从生活经历到小说,必须有长期的酝酿过程,其中不知道经过了多少难以追溯复原的转变。所以尽管《围城》包含着许许多多和作者相关的人和事(杨绛指出过一部分,应该还有其他部分),它还是一部虚构的小说,一部复合型的虚构小说。
《围城》有其丰富的内涵,以男女主人公的恋爱为主线展开,但它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部从婚姻反观爱情的小说。从人类性爱、情爱的全过程来看,“爱情小说”实际上仅仅是“半截子”小说。爱情小说往往以婚姻的成败为结束,无论其结局是悲剧还是喜剧,对平常的实际人生来说,总是简单化的。而从婚姻反观爱情,所包含的内容自然要复杂得多,在《围城》中则不得不显出一种困境。这种困境,如果和社会文化结合,则更为丰实。而在《围城》中,这种困境处处出现,成为小说发展的推动力。这种困境在小说中有其中心意象,就是作者最后用书名来点题的“围城”。“围城”意象,后来被总结成以下一段话:
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在《围城》小说中,这一意象点出在第三章。最初是借小说人物褚慎明之口带出罗素(Bertie)称引的英国古语:
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小说随即又借苏小姐之口引述法国成语“forteresse assiégée”点出了这一中心意象:
结婚如同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这就是作者借小说人物在客厅议论中点出的“围城”意象,所述尚以婚姻为主。而在第五章,又借离开上海的主人公方鸿渐之口对这一意象作了呼应:
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
这就从婚姻扩展到人生万事了。从婚姻到人生万事,从人生万事到婚姻,范围虽有变化,仍然契合。在小说中,经过反复铺垫已然厚实的“围城”意象尚属空间,但冲进冲出,永不停歇,又蕴含时间。而这一时间变化在小说中,以第九章的祖传怪钟来点题,这只走时落伍的计时机和实际时间竟相差五个钟头,它在小说结尾中出现:
无意中包涵了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的语言,一切啼笑。
由此“围城” 意象和怪钟结合,完成了小说的卒章显志。怪钟的时间错乱,也是时代错乱,反映了作者杜门寂处、蛰居于沦陷区时,观察种种世相而忧生伤世的心境。
从“围城”意象观察整部小说,小说的实际情形和那句法国成语表面似乎并不一致:方鸿渐想逃避冲入苏小姐的城(“围城”比喻在小说中出自苏小姐之口),却在无意中不知不觉地冲入孙小姐的城,情景似乎反了一反。但是从摆脱一个困境始,到落入另一个困境终,在更高的层次仍然被那句比喻套住,这也说明了“围城”意象的涵盖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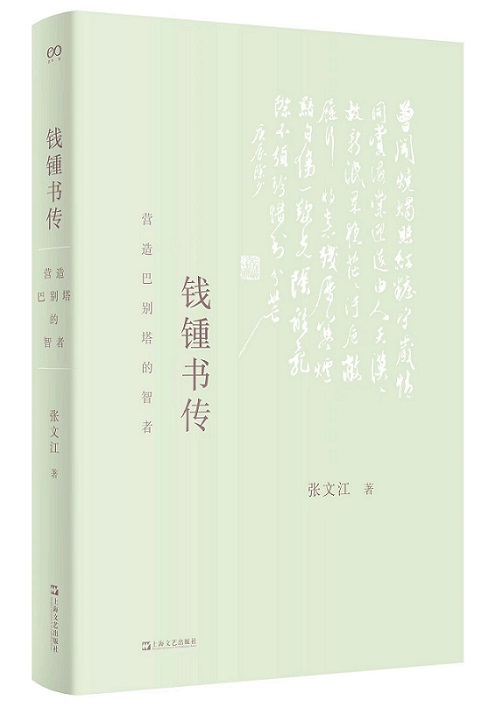
《钱锺书传:营造巴别塔的智者》,张文江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