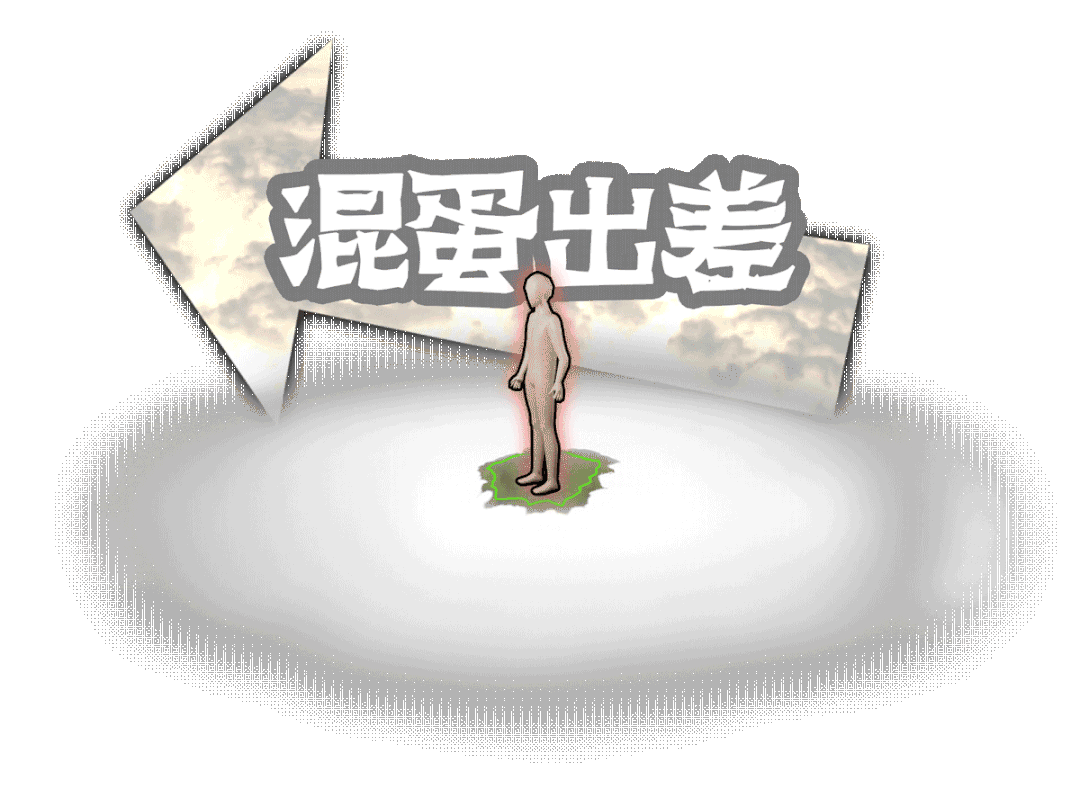
从潮汕坐动车沿海而上,不出一个小时就到了闽南。
现代人说闽南,大多指厦漳泉三地,其中漳州最南。漳州南部云霄县的山谷中,种有大片的枇杷树。为防日晒虫咬,人们把枇杷果用锡纸包起来。火车飞速掠过,满山的银树流成一条银带,奇异而梦幻。
火车太快,银色的枇杷树拍不清楚,但能远远拍下云霄县的将军山。这个县曾以擅长制造假烟闻名全国
当然,漳州山民的智慧,绝不止于让枇杷树反光和制造假烟。来此地游览的人,大多是为了这里的先民们修建的、大名鼎鼎的土楼。
——如果你本着休闲放松的宗旨寻找旅行目的地,那你大可不必前往土楼:
和你小时候在天气预报里看到的一样,土楼就是深山里几座土黄色的圆房子。一如游览任何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景点,除了一头臭汗、一条带定位的朋友圈和一件廉价的义乌纪念品,你很有可能一无所获。
但是,如果你爱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或者想象力足够丰富,又或者,你对我们民族的文化有足够强烈的好奇心,你倒确实应该去土楼看看:
汉族人被赶到这山与海逼夹中的弹丸之地,绝境之中,他们缩成一个个精美的圆。圆的外面,是瘴疠和猛兽,蛮族与倭寇;圆的里面,自成一方小小天地,囊括一族的秩序人伦。
——那是我族人最后的堡垒,也是我们北方人,尝试去理解闽南人、客家人这些千百年前南下避祸的同胞民系时,一道必经的关隘。
在南靖的一些土楼,宛如中原故里般庄严的宗祠会立在中心,它的雕梁画栋被敦实而粗粝的夯土墙严严包围,
俯瞰起来就像一座曼达拉坛城。
说了这么多,但今次我们其实并未在漳州下车。高铁票上的目的地是泉州,王画虎正携未婚妻在泉州站迎接我们。
王画虎是我的朋友,也是同行。作为一个青年文化媒体从业者,王画虎的一年却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呆在他的家乡,——一座叫做南安的闽南县级市。在我所认识的北漂中,他无疑与故乡拥有最强的粘性。
说起南安,和北方的县域很是不同,这里大概从来不存在高大的城墙和防御工事,县城的治所溪美镇,一百年前也不过三四条街巷。晋江的上游西溪穿过南安县,许多的村落被串联起来,这种村落间若即若离的联合,原是这座“县城”的本来面目。
不过,行走在南安的街面上,你会发现,这里看上去和大部分的中国富裕县城别无二致:街道宽阔,绿化有序,商业繁荣。
西溪穿过南安市,两旁是不少新建的商品房
——但你千万不要被这里的表象蒙蔽,以宗族为纽带维系的古老村落从未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消失,宗族势力的象征物:一座座祠堂家庙,就藏街面上一排排现代化门面的身后。
以一座或几座宗祠为核心向外发散几百米的半径,便是一座同姓村落。当地人的归属感,也牢牢地落实在“村”这个范围内:
对内,一村的族人们往往表现出惊人的团结。他们大多从事同一类的营生:你生产马桶,我就生产水箱;你生产大锣,我就生产棒槌。遇到什么问题,大家会互相帮扶,乃至于县城的中学里同学们之间闹矛盾,最后找来的帮手的也往往是同校的本村族人。
而对外,每一座村落,似乎都拥有一套微妙的人格化的形象:这个村彪悍,那个村斯文,这个村义气,那个村狡猾,这些标签被牢牢刻印在当地人的集体记忆之中,成为在这里安身立命的每一个个体的盔甲和名片。
在县城里开车,每路过一个地方,王画虎都会给我们讲述发生在那里的宗族械斗往事
——基于此,我与陈只三一在南安落脚,王画虎便特地驱车载我们去一个叫英都的地方吃晚餐。这是因为,一方面,英都有一家十分有水准的烹饪甲鱼的餐厅;另一方面,英都人在本地的口碑,就是温柔、讲礼义、好读书。毕竟,没有人会招待客人去一个随时可能发生械斗的片区用餐。
闽南人和潮汕人的烹饪方式有相似之处,但相比潮汕人,闽南人的烹饪调味更复杂,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与其他文化有更多的交流
英都是一个镇,但这个镇很特殊,整个镇几乎全部是姓洪的人。因此,英都镇的中心,是由几座洪氏家庙共同组成的祠宇建筑群。
英都的洪氏家庙全景。这张图片之所以从“水暖阀门网”下载下来,是因为英都在中国水暖阀门界拥有非常高的地位,——事实上,整个英都镇都是水暖洁具阀门厂,这里甚至被称为“中国水暖城”
虽然是家庙,但这里是个开放的公共空间,人人皆可进入参观。比起祭祀场所,这里倒更像是一座小广场。——和此地大部分的宗祠一样,宗祠附属的广场承担了族人们休闲聚会的功能。我们去的时候正值春节,不少本地的儿童成群结队地在广场上燃放烟花,好不热闹。
有趣的是,祠堂的一厢,竟建有一方专供族人读书的公共图书馆。这座图书馆相当大,里面的读物也不少,图书馆墙壁上挂着许多洪氏祖先画像,以及各位祖先拟定的家训,我们晚上八九点钟进去看,不少小孩子竟还在祖宗们的凝视下写着他们的寒假作业。
——如此看,我们实在不难理解,此门洪氏为何曾创造过“四代十进士”的光荣战绩,并至今仍给当地人留下“重视教育”的形象。
洪氏大宗祠中,写着“祖孙四代十进士名扬明室,父子一博双翰林誉满清廷”的对联
说到教育,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泉州是外来务工大市,比如英都作为中国生产水暖阀门的重镇,和许多泉州下属的乡镇一样,生活着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根据资料,仅英都中学,就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学生是外来务工者的子女。
而在今年初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中,在“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评估”这一方面,泉州市在六十个城市中排名第一。
这项评估中,北京市以28分的成绩垫底
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数据让人很有好感。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泉州虽然拥有如此强大的宗族势力,但却并不封闭和排外。
——这可能是此地气运蒸蒸日上的秘诀之一,如果你来泉州旅行,从街巷的细节、食物的热气、人脸上的表情,你一定能隐隐感觉到一种向上的能量,这种能量会让你对这个城市的前景有乐观的估计,让你想在这儿投资买房。
泉州是个非常棒的旅行目的地,这里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港口,拥有丰盛的文化和众多古迹。可惜这次时间仓促,我们只在泉州城游览了一个下午,这是泉州的清真古寺清净寺的大门,
我们前来参观时已经关闭。
说起来,虽然我们着重参观了洪氏家庙,王画虎自己的家族在闽南的历史其实更为悠久。他是大名鼎鼎的“开闽三王”中闽王王审知的后裔。他家族所在贵峰村的始祖应寿公,是王审知的十八世孙,明朝初年由漳州迁来南安,其后裔六百年来便一直在此定居。
王画虎家中有一本大书,详细记录着本村有名望的族人在各地的情况。饭桌上和他们家的长辈聊到什么,长辈们常常会借势聊起族中的某某,如今在何处如何如何,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去年回家,王画虎给族中祖厝捐了五千块。今年,他即将举办婚礼,成为族谱上一个完成婚配的男丁。他的未婚妻豆豆也是南安人。在他拜会豆豆年近百岁的外曾祖母时,老人对他说,她们的家族,六十年大起,六十年大落,我熬了六十年的大落,现在该大起了。
好一个六十年大起,六十年大落。在这里,个人的命运,与家族的气运牢牢嵌套,密不可分。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大概也只有闽南人,有这样的底气,以如此宏大的叙事框架去展望自己的家族的命运了吧。
面线糊,一种泉州特色小吃,作为一种早餐,
这样扎实的用料确实有点儿过分了
在南安住了一夜,第二天晚上我们就驱车来到了厦门。
厦门是名副其实的大城市,之前因为各种原因我也来过不少次了。这里舒适宜人,干净便捷,找个海滨步道吹吹风散散步,大排档里点一份酱油水,一罐青橄榄排骨汤,找棵大榕树坐下来看着大海发呆一下午。——北漂实在不易在此久留,不然很容易为自己日常生活的质量感到自卑。
而厦门对于闽南人,就像方糖之于工蚁。泉州老板们生意做得再大、老家的豪宅修得再富丽,也一定要在厦门拥有自己的资产和门面。这份执着,使得整个闽南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厦门:
从好的方面看,这使厦门变成了一个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备、商业越来越繁荣的“大都市”;从坏的方面看,这也让厦门的房价涨得越来越离谱。
——像休闲公司的小皖,把自己的房子卖掉去开一家酒吧,回头发现卖掉的房子翻了两倍。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像他一样开始因为高房价而感到困扰,这个城市某些隐患可能就开始酝酿了。
公路商店的编辑们来厦门,当然要去休闲公司。与其说休闲公司是一间酒吧,它倒更像是厦门青年文化群体的聚集地。这意味着在这里,你总能找到臭味相投的、不甘于淹没在实用主义泡沫中的年轻人,——在重宗族、擅营商的闽南,这样的品质似乎格外可贵。另外,据说这里的苦艾酒也非常值得尝试。
休闲公司里的涂鸦
在厦门的最后一个晚上,
我们慕名去了臭迪歌厅秀。
原则上,臭迪歌厅秀应该算是一个ktv,但它完全不私密。来此的每一桌都必须要按照主持人的安排轮流公开唱歌(如果不唱会被主持人反复催促或羞辱),在这儿饮酒的人,耳边歌声不断,歌者却又都是素不相识的路人,你要是喜欢谁的歌,可以送上花篮彩炮,或者上前攀谈,饮酒跳舞;遇到鬼哭狼嚎的,你也只能礼貌地忍着。
为了防止所有客人唱的都很难听,每一轮客人演唱后,两位驻场姐姐会送上一次专业的闽南歌表演
我们来此的期待,本是想看到许多厦门本地的叔叔阿姨,因为歌厅秀这种地方,原本是中年人来得多,他们唱的也往往是那种风味十足的闽南歌。
——说起来,厦门算是闽南歌的发源地。闽南歌的歌词,往往像古典的诗歌一样,使用一套安全又暧昧的规范:男子与宿命,女子与相思,其中有哀婉屈曲,有豁达洒脱,兜兜转转又绕不开“欢喜”两个字。这些歌中的温柔,也许是闽南人最外显的浪漫。
没想到我们去的那天,台下坐着的最多的竟都是年轻人,上台唱的都是周杰伦和萧敬腾。可能正值新年,中年人还在忙着迎来送往;也可能是随着网路消息的传播,臭迪歌厅秀确实成了年轻人爱来的场所。无论如何,看到这里的好生意,来客总归会感到开心。
倒是我这个东北人,率先上台演唱了一首闽南歌《流浪到淡水》。主持人姐姐显然对我并不放心,一开始非要给我开着原唱,不过,三句以后她就关掉了。
“人生浮沉起起落落毋免来烦恼
有时月圆有时也昧平
趁着今晚欢欢喜喜斗阵来作伙
你来跳舞我来念歌诗
有缘,无缘,大家来作伙
烧酒饮一杯乎乾啦乎乾啦”
烧酒饮一杯,乎干啦!飞机从高崎机场盘旋起飞,我又回到了北京。谢谢陈只三、王画虎、谢正义和小郭的热情招待,让我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新年。这篇稿子写完,我给王画虎过目,他说:
特此申明。世界上可能再没有第二个新媒体编辑对自己家乡行政名称的细节如此关切了。
撰文:大蹦驴
编辑:大蹦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