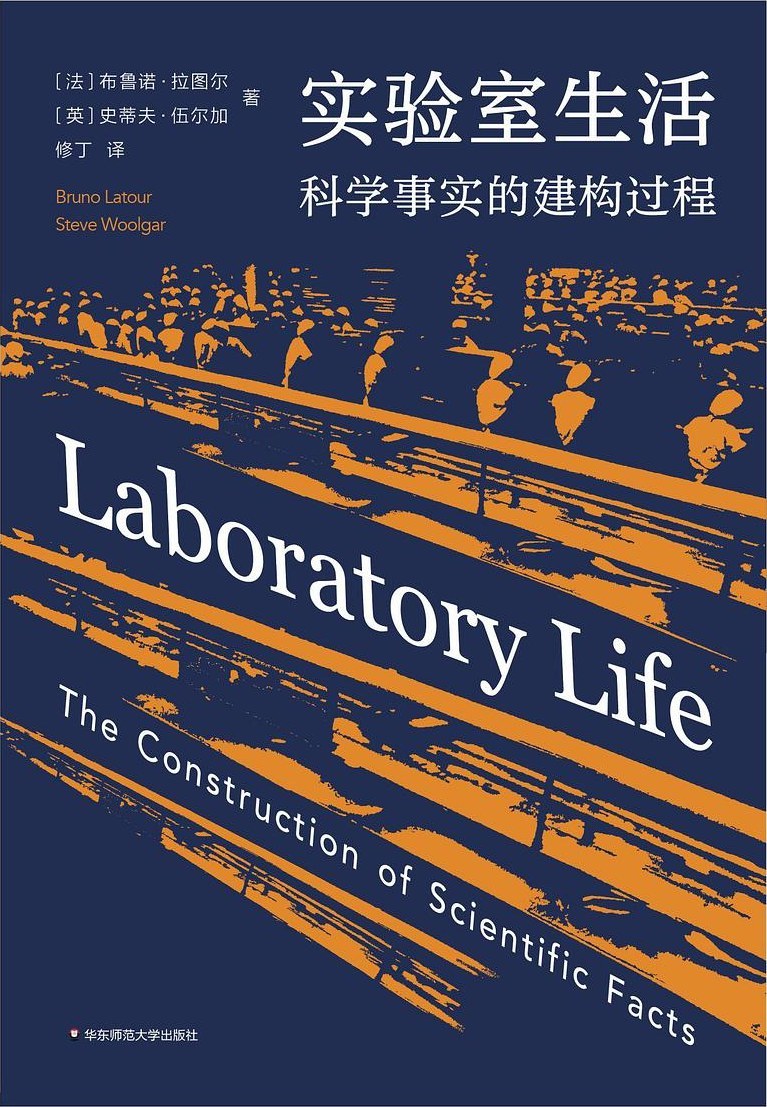
《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法]布鲁诺·拉图尔、[英]史蒂夫·伍尔加著,修丁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2023年6月出版,352页,75.00元
去年10月,法国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 1947-2022)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五岁。身为霍尔伯格奖(Holberg Prize, 2013)和京都奖(Kyoto Prize, 2021)两项世界级人文社会科学重要奖项的得主,拉图尔甚至从未申请到过巴黎高师这样的法国精英大学的教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他的祖国相对不为人知,甚至是一些学术敌意的目标。”(Steve Woolgar, Bruno Latour [1947–2022], Nature, 2022, 611 [7937], p.661)
但他所处的时代却被这样一个人和他的后继者们不可逆转地改变了:长久以来,科学社会学曾对实验室中的日常科学实践视而不见。今天,这种近距离地“用社会学家的显微镜观察”(J. Salk, Introduction, B. Latour, S. Woolgar,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2)实验设备、记录、纸张痕迹、材料样本、引文、研究资助,以及实验室里“灵长类动物”的科学人类学进路,毋庸置疑地成为了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特别是“实验室研究”(laboratory studies)的“权力的新源头”(B. Latour,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40, 133)——宛若他笔下的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科学家可以被“围观”,甚至可用研究“前现代人”的方式来“冷眼审视”他们(A. Kofman, Bruno Latour, the Post-Truth Philosopher, Mounts a Defense of Science, New York Times, 2018)。我们需要的,只是走进实验室去勇敢地跟随曾拥有着无比光环的他们。一切变化的起点,便是拉图尔的《实验室生活》(以下简称《生活》)。
年轻时的拉图尔
初识《生活》
“实验室研究”在西方世界如火如荼地开展之时,刚刚打开大门的中国学术界却对此一无所知。大部分的人还要依靠《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79-1989)、《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1979-1986),或是更通俗的“走向未来”丛书的译介,才能够稍微了解到波普尔、库恩等科学哲学家的思想。直到1987年,情况才稍微有了变化。
当年10月31日至11月13日,《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杂志的创刊副主编、历史学家麦克劳德(Roy MacLeod, 1941-)应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的邀请到北京访问。在11月4日下午和10日两天,麦克劳德教授向中国同行介绍了后库恩时代“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新进展。根据后来整理的“学术动态”报道,麦克劳德教授在讲座中提到了爱丁堡学派“重视对实验室科研步骤的实地体验”的做法。他甚至还在推荐书目中明确提到了《实验室生活》(王德禄、郑宇建:《澳大利亚科学社会学家麦克劳德来华访问》,《自然辩证法通讯》, 1988年第一期,70-72页)。这也是这本书,连同拉图尔的名字第一次进入中国学术界的视野。
麦克劳德教授的访问为当时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研究打开了局面。国内学者开始大量仿照使用“科学的社会研究”这类表述(陈光:《科学社会学的新转向》,《科学》, 1989年第四期,288-292页)。值得注意的是,沿着麦克劳德报告的传统,南开大学的刘珺珺专门发文介绍了“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流派——爱丁堡学派。按照她的解释,爱丁堡学派是:
在库恩的哲学思想影响下,在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之后,研究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和社会内容的学派。(刘珺珺:《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和现状》,《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四期,21页)
但不同于麦克劳德(或其转述者)错误地将拉图尔归入爱丁堡学派,刘珺珺认为:
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都尔(Bruno Latour)代表着另一种发展路线……以法国为代表的、从微观角度研究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的研究方法,有人称之为微观倾向发生学方法或建构主义纲领。(同前)
也是在这篇文章里,《生活》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披露。刘珺珺重点关注了《生活》的两部分内容(分别是原书的第二、第五章):第一,注意到实验室的本质是“由机器、仪器和实验技术人员综合在一起的装置组成”,而这些装置存在的意义在于“进行文学标记(literary inscription)”。第二,科学家从事科学的目的并非默顿学派所言的奖励(rewards),而是“可信用性或借贷能力(credibility,即信用)”的一种投资。
尽管刘珺珺自谦,上述文字只是“个人的学习所得,并不是全面的综述”。但她还是尖锐地将矛头指向了第一版《生活》中的建构主义色彩,认为拉图尔的信用“循环仍然在认识的循环之外”,从而未能履行并碰触到其“研究科学的最重要的内容——科学知识”的承诺。殊不知早在1986年,《生活》就已经出了改版。新版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将副标题中的“社会建构”明确地改为了“建构”。刘珺珺的综述性工作影响是深远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拉图尔都被延续地译为拉都尔(见施雁飞:《西方科学哲学的现状和趋向(上)》,《哲学动态》,1990年第九期,33-35页;方卫华:《科学知识社会学评述——对建构主义的分析》,《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年第一期,34-39页;樊春良:《科学知识的制造——谢廷娜的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学研究》,1992年第一期,18-23页;张锦志:《两种形而上学标准之争——对布鲁尔与拉都尔论战的哲学考察》,《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七期,21-24、72页)。
实际上早在1987年,刘珺珺就打算写一本科学社会学的书(而并非仅仅是一篇介绍性的文章)。但没想到:
书籍和论文资料……远远不够,不得不请求外国朋友或在国外的中国朋友寄来……再加上教学任务缠身,竟使这本书写写停停达三年之久尚未完成。(刘珺珺:《科学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页)
作为“新学科丛书”(1986-1990)的最后一本,刘珺珺在《科学社会学》中系统性地介绍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历史发展以及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但如她本人坦陈,囿于资料等方面的限制,全书的后半部分还是使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了默顿学派的工作,包括科学社会体制、科学家的行为规范以及科学奖励制度和权威结构等。仅仅在最后一章“科学知识社会学”中提到了爱丁堡学派和拉图尔的内容。特别是后者——
主张通过对科学实验室的人类学研究看穿这些“黑箱”。(《科学社会学》,258页)
尽管只是1988年文章的扩展,刘珺珺第一次明确地将拉图尔的工作归结为人类学方法,并单独给了拉图尔一个小节的篇幅。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人类学方法。拉都尔”中,刘珺珺进一步介绍了《生活》第一、第三两章的部分内容——特别是促甲状腺释放因子的案例,作为“文学标记的功能就在于说服读者”观点的补充。考虑到只有这部分才“是主要的社会学内容”,扩展最多的部分是“可信用性”。她甚至还不惜篇幅,将《生活》中的信用循环图片(B. Latour, S. Woolgar, 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9, p.201)照搬了过来(却将“资助”误译成了“赠款”,《科学社会学》,282页)。不过她也在后记中坦言:
这个学派的基本思想和若干观点,目前还很难接受……对于要以科学技术推动工业化而奋力直追的中国人民来说,恐怕是完全不合时宜的思潮。(同前,291-292页)
无论如何,这大概都构成了《生活》在中国的第一个“粗糙和仓促”的部分译本。
《实验室生活》初版本
法文译本
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了“哲学与文化研究室”。刚刚调任到研究室的霍桂桓决定和同事鲁旭东一起策划一套“知识与社会译丛”,系统性地介绍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工作。彼时,江西教育等部分出版社已经开始零星地译介SSK的作品。刘华杰评价,这“中国首次全面引入SSK……在中国学术出版史上应当记上一笔”(刘华杰:《浅谈近几年SSK在中国的传播》,《中华读书报》2002年6月26日)。
按照鲁旭东的说法,“SSK代表了国外学术界在认识论、社会哲学以及科学社会学等方面研究的新方向”(鲁旭东:《“科学社会学:理论与争论”编者按》,《哲学译丛》2000年第一期,第5页)。但和刘珺珺的《科学社会学》情况类似,系统性地译介SSK的经典并不容易。如鲁旭东在受访中所言,
科学社会学在中国刚刚起步,国内相关的学术资料很少,翻译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翻译类似这种在国内刚刚开始建设的学科领域的学术著作时……经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有时候甚至会被一句话或者一个术语困扰很长时间。(陈菁霞:《鲁旭东:学术翻译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华读书报》2021年5月26日第七版)
事实上,《生活》(以及拉图尔的另一本书《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是这套译丛里出版最晚的一批。可能正是由于对SSK整体上的不熟悉,在发现《生活》存在英、法两个语种的版本后,张伯霖、刁小英两位译者选择了后者,尽管很牵强,但其原因是:
拉图尔是法国人,所以我们最后决定由法文译为中文。(张伯霖、刁小英:《译后记》,[法]布鲁诺·拉图尔、[英]史蒂夫·伍尔加:《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东方出版社, 2004年,299页)
《实验室生活》2004年译本
根据拉图尔在“致读者”中的陈述,他“意译第一章,并删去了英文第二版中的序言和跋”。然而两个版本的细节方面仍存在着些许的不一致,比如题献的部分法文版就只提到了索尔克研究所和吉耶曼教授,全然没有提到富布莱特和北约奖学金对研究工作的资助。第二版序言实际上也是索尔克本人为《生活》专门撰写的。跋则更多展示了他对本书理论定位的反思,以及对维斯特鲁姆等人批评(R. Westrum, 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by Bruno Latour and Steve Woolgar [Book Review], Knowledge, 1982, 3 [3], p.437)的回应。显然在拉图尔看来,这些节外生枝的信息并非法国的读者要知道的。
对于法国读者而言,异域情调的美国本身就有足够的吸引力:
作为哲学家,我以合作的方式在法国服兵役……有幸……遇到了……人类学家。我来到萨尔克(原文如此,通常译为索尔克)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看起来像个掩体,除了宽敞的水泥掩蔽所外,附近别无他物……我从他(索尔克)的办公室走出来。在海岸边的峭壁前,一艘巡洋舰已离开锚地圣迭戈。(2004年译本,第4-5页)
显然,这种写作方式非常的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如同列氏名著《忧郁的热带》,拉图尔希望给法国读者展示的就是他某种意义上的游记。
尽管不忘提到实验室里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人(拉图尔坦陈读科学论文简直就像读中文)和“红棕色头发的……矮胖子”,拉图尔却并没有将全部笔墨浪费在投喂猎奇上。相反,他尖锐地指出以巴什拉尔(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为代表的法国哲学已经被英国同行所超越——SSK正以一种对称性的方式同等地对待科学史中的成功和失败者,这与巴什拉尔“不断地嘲笑十八世纪伪科学家”(2004年译本,14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他自己做的,正是为法国人扳回一局:英国的科学社会史家“拘泥于档案(文献、文章、谈话纪要)”;他,一个法国人,不但去现场记录了“对科学家工作的直接观察”,还编纂了“实验室的第一部人类文化学志”(同前,第9、13、15页),而且最关键的是:
在我们结束调查后的一年以后,R·吉耶曼由于阐明TRF的特征而荣获诺贝尔奖。对,这是正规科学,不是边缘科学。(同前,23页)
而且他所运用的方法正是法国人所熟悉的人类学方法(他甚至还在《生活》中引用了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
如果承认一个25岁的年轻的男人和女人能够深入地了解他们所陌生的实践和世界,那么……[这种方法也]完全适用于萨(索)尔克研究所。(同前,17-18页)
法文版《生活》出版之时,拉图尔的《法国的巴斯德化》——他职业生涯中第二部标志性的作品已经付梓。也许是经历了改版和多年来对批评的回应让他的思想更加成熟,拉图尔果断地放弃了英文版中“盎格鲁-萨克逊的论战风格”。甚至在很多时候,拉图尔的论证是简单粗暴的。比如上面一段文字在英文版中被更明确地表述为陌生化策略,即“尽可能让实验室活动显得陌生”(Latour and Woolgar, 1979, p.30)。相比之下,法文版里只是在字面意义上稍微提到了作为陌生化理论来源的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原译“人类文化学方法论”有误)。
可惜囿于各方面的限制,《生活》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译著类似,翻译质量并不是太高。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会引发误解。比如:
这样,我们人类学家观察者就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部落,这个部落正度过自己编码、做标记、读与写的最光辉的时代。从表面看, 这些活动与做标记、书写、编码和修订并无关系,那么,这些活动有什么意义呢?例如,我们在照片4上看到两位照管老鼠的年轻妇女。(2004年译本,34页)
对照英文版,正确的表述应该是:
因此,我们的人类学观察家所面对的是一个奇怪的部落,部落里的人们每天要花费大部分的时间来编码、标记、修改、纠正、阅读和书写。那么,那些显然与标记、书写、编码和纠正无关的活动,比如照片4中显示的两名年轻女性正在处理大鼠,其意义又是什么呢?(Latour and Woolgar, 1979, p.49)
无论如何,法文版《生活》的译介为中国学术界打开了一扇大门。学生和学者们如饥似渴地从中寻找着概念和理论资源。渐渐地,“拉都尔”的译法被历史遗忘,“拉图尔”的正统译名取而代之。
重译《生活》的意义与遗憾
2023年,《生活》依照英文第二版得到了重译(这无疑是目前最好的一个译本)。读者终于可以一睹它的全貌,包括此前被法文版删去的索尔克题写的序言和反身性色彩浓厚的跋。尤其是前者,索尔克用精炼的语言勾勒出整本书的重点:
他们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并非社会世界存在于一边,而科学世界则存在于另一边……他们声称的主要成就是揭示了“人类的诸方面”被排除在“事实生产”最后阶段的那种方式。(J. Salk, Introduction, p.13)
《实验室生活》英文第二版
尽管从对称性的角度出发,两位作者承认“未来对其陈述进行重新评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Latour and Woolgar, 1986, p.88),尽管索尔克本人还是对这种思维方式仍心存疑虑,但他还是认为,《生活》始终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迈进”,即消除了“被认为围绕着我们(科学)活动的神秘感”(J. Salk, Introduction, p.14)。
的确,和人类学家一样,科学的成员们所面临的难题也是:
说服论文(以及组成它的图表和图形)的读者,其陈述应被接受为事实。为此,大鼠才被放血和砍头,青蛙才被剥皮,化学品才被消耗,时间才被花费,职业发展之路才被筑起或是破坏,inscription devices才在实验室中被制造出来并积累下去。事实上,这正是实验室存在的理由。(Latour and Woolgar, 1986, p.88)
作为全书的一个核心概念,inscription devices在新版中被翻译成“铭文装置”。这大体沿用了赵万里在其博士论文(导师为刘珺珺)中“铭写装置”的译法(赵万里:《建构论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南开大学, 2000年)。有趣的是,在三个版本中,这个词分别被译为“(标记)装置”“记录器”和“铭文装置”。尽管“翻译即背叛”的情况在所难免,究竟哪一个译法更接近《生活》的本意呢?
按照两位作者的说法,inscription devices本质上依赖于apparatus或是apparatus的特定组合。从实验室中A、B两个区介绍的情况来看,apparatus的含义更接近通常意义上的仪器而非福柯意义上的装置——或可统称为机器。其作用是“将物质实体转化为办公空间的成员可以直接使用的图形或图表”。有了这些图形或图表,
中间的物质活动,以及通常漫长而昂贵的这个转化过程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闭口不谈。(Latour and Woolgar, 1986, p.51)
这实际上也是实验室研究的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在科学家共同体中传播(科学计量学通常关注的部分),并实现陈述类型转换——甚至最终成为科学事实的前置条件。
因此如法文版译文所言,inscription的核心含义是(书面地)记录。如两位作者所言,“文字记录(literary inscription)的功能是成功地说服读者,但只有当所有的说服来源(即说话者)都看似消失时,读者才会完全信服”(Latour and Woolgar, 1986, p.76)。
与记录相对的是说话者必须在场的表达(expression,参见第二章注释2)。《生活》的第四章实际上展现了实验室中的各种表达,比如:
史密斯:你有信心她(实验室中的一位年轻的博士后)能做五只(更多的动物)吗?
瑞克特:是说她的诚实吗?
史密斯:不是诚实……她做其他工作,你有信心吗?
瑞克特:哦,没有,在诚实的意义上,她倒是十分可靠的。(Latour and Woolgar, 1986, p.163)
为避免“得不偿失”,史密斯和瑞克特最终决定不继续发表他们的摘要。但除非进入信用循环,比如写进这位博士后的推荐信,上述表达是永远不需要被记录的。
考虑到全书并没有单独使用devices的例证,这个概念绝不是apparatus的同义反复。《生活》的第二章使用了大量的篇幅证明科学文本(除了标注参考文献)几乎和文学文本并无二致,我们最好也从文学的对称性角度去尝试理解。如同索尔克也这样认为并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的:非科学家写科学批评,同非小说家或诗人写文学批评本质上是一回事。
在文学的语境下,literary devices通常被译作“文学手法”,是指用来传达文章内容的结构和技巧。因此当两位作者使用inscription devices这个概念时,他们试图传达的含义也是记录手段(或按照法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译为“策略”)——无论是科学家(或者其实验员助手)用来总结的痕迹、斑、点、柱状图、录入的数字、光谱、峰值等,还是人类学家在民族志中所援引的(田野)笔记,所呈现的实境照片。
除了一些小瑕疵,关键概念上的“背叛”恐怕是包括新译本在内的全部三个译本共同的遗憾。但如同在科学研究中有时不得不使用间接证据的怪物(monster,Latour and Woolgar, 1986, p.116),对科学知识本身的研究也不得不使用“既能使怪物得到遏制,又能在我们的事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文字表达诸形式”(B. Latour, Postscript to Second Edition, Latour and Woolgar, 1986, p.283)。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可以被“重新评估”的新概念本身也只能是一种权衡。
作者、译者退场。未来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