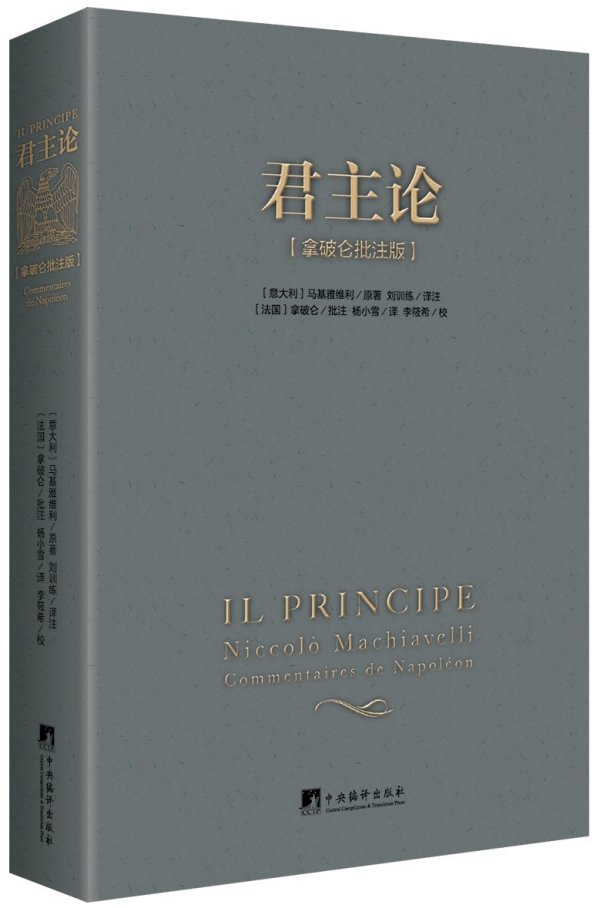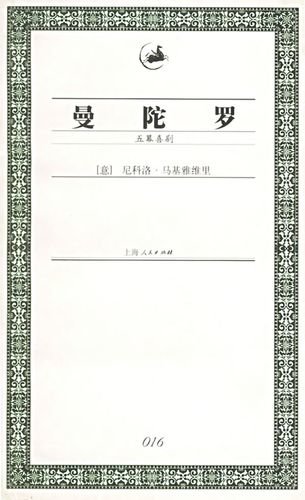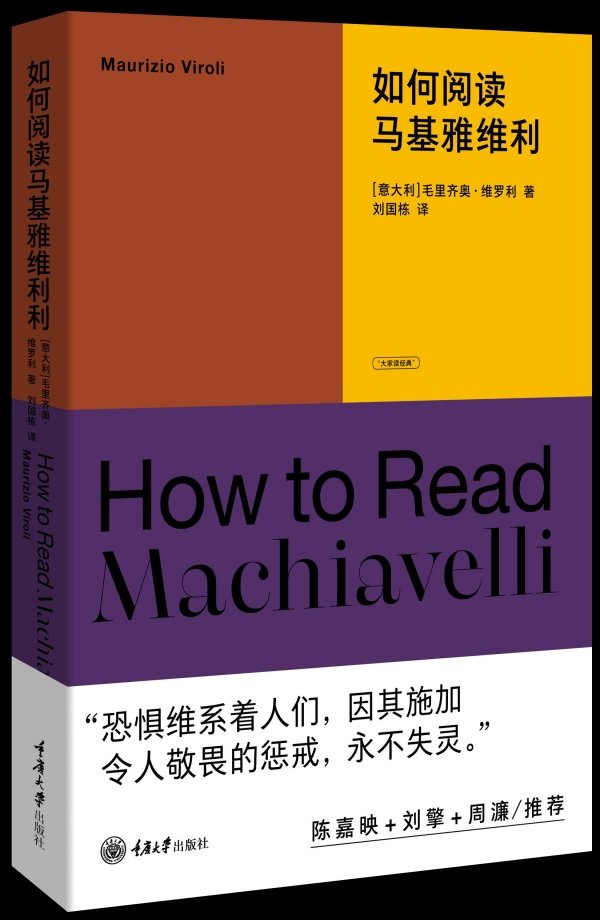如果想要真正了解马基雅维利的著作,那就必须暂时搁置——甚至质疑——长期以来学者和大众形成的关于其著作的一系列流行观点。其实,它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反映的是政治思想史晚近时期才形成的一些观念。如果要对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有一个正确的解读,那就必须首先考察其政治和知识背景。

马基雅维利
1469年5月3日,马基雅维利出生于佛罗伦萨,当时强大的梅迪奇家族掌控着该城市的政局。1494年,他目睹了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入侵,该事件使意大利从此逐渐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与此同时,在多明我会修道士热罗尼莫·萨沃纳罗拉——其本人在1498年被当作宗教异端审判处死——的道德和政治教义的鼓吹下,佛罗伦萨建立起了一个共和政府。共和政府时期,作为政府的高级官员,马基雅维利负责国家的外交事务。然而,1512年,在西班牙和教皇军队的联合入侵下,共和政府覆灭了,佛罗伦萨又重新落入梅迪奇家族的掌控之中。马基雅维利不仅被解雇,很快还因阴谋推翻新政府的罪名被逮捕入狱,并遭受了残酷的刑罚。直到1527年去世前,马基雅维利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政治和历史论文的创作之中,写下了众多的著作,比如 《君主论》(1513年)《论李维》(1513-1519年)《用兵之道》(1521年)和《佛罗伦萨史》;同时他还完成了多部喜剧和诗歌著作,尤其是《曼陀罗》(1518年)和《金驴记》。他在世的时候,只有《用兵之道》一部重要论著于1521年出版,《君主论》和《论李维》都是在他死后分别于1532年和1531年才出版的。1512年后到逝世前,马基雅维利再也没有担任过任何重要的政治职务,他试图做了一些防止意大利被外国奴役的工作,但大都是徒劳。虽然大部分学者把马基雅维利视为一位纯粹的政治理论家,但他本人还提出了一种强有力的道德哲学理论,即人类悲惨的境遇可以通过献身于一些伟大的观念而得到规避。他强调人性的恶,但对人类的弱点却持一种善意的揶揄态度。在此意义上,马基雅维利关于人性的看法反映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哲学的精神。
尽管马基雅维利本人拥有一颗无比诚挚的灵魂,还满怀热忱地投身于自己的共和国和整个意大利的公共事业,但是人们仍然把他视为政治诈术的导师和鼓吹者:“目的正确即手段正当”;不能以适用于普通个人的正义和正直的道德原则为依据来评判一项政治行动,它只能建立在成功与否这唯一的法则之上。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个基本的事实,即马基雅维利从来没有写下上面的文字,也没有表示过为了征服或保持政治权力,残暴、欺骗和不忠就都是合理的。他在专制国、君主国与共和国之间做了区分,坚定地认为暴君是最邪恶的人。“在受到赞美的人中间,享有赞美最多的首推宗教首领和创立者,次为共和国或王国的创建者……相反,毁坏宗教者,挖王国或共和国墙脚的人,同给人类带来便利与光荣的美德、文学和各种技艺为敌的人,譬如不敬神明者、愚顽无知者、暴徒、懦夫、懒汉、下贱坯,都是可耻可憎之人。没有人疯癫或聪慧到无以复加,达于至善或至恶,当人类的两种品性摆在面前供他选择时,他竟然不去赞美理当赞美之事,羞辱理当羞辱之人。”(D,Ⅰ.10)
即便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事业,比如建立一个良好的王国或共和国,不道德的手段顶多算是一种借口,而根本不能成为合理的理由。建立新的国家的时候,避免使用非道德和暴力的手段,才是最光荣的事情。“那些运用法律和制度对王国和共和国进行改革的人们,没有什么人的什么行为能够获得比他们更多的赞誉了;除了诸神明之外,他们就是首先要被赞美的对象。”(OW,ⅰ.115)即便一件事本身是光荣的,那也无法洗刷它达成目标前所犯下的罪行,相反,通过正当手段达成好的政治目标才是最值得赞扬的。
马基雅维利并不建议君主和共和国的首领“使用一切手段夺取和保有权力”。相反,他敦促政治首领们通过恰当的手段来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从而追求真正的光荣。杀害自己的公民同胞、出卖同盟、缺乏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一个人通过这些手段“可以赢得统治权,但是不能赢得光荣。”(P,Ⅷ)马基雅维利的这些论述相当重要。他认为光荣是君主和政治首领应该追求的目标。不讲光荣,依靠罪恶手段去谋求权力,这仅仅是君主的最后选择。因此马基雅维利说,像叙拉古的暴君阿加索克勒斯那样的人只拥有“邪恶的野蛮残忍和不人道,不允许他跻身于大名鼎鼎的最卓越的人物之列。”(P,Ⅷ)政治首领们只有在缺乏合适的手段去完成伟大政治行为的时候,才可以诉诸于罪恶,但也应该尽快回到正确的道路上。马基雅维利最崇尚的英雄是摩西,说他“不得不除掉无数仅仅出于嫉妒而反对他的人。”(D,Ⅲ.30)然而,上帝始终是摩西的朋友,并在摩西杀人的时候仍然站在他那一边。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教义是,当一个良好的政治目标使残暴、邪恶或欺诈行为成为必要的时候,上帝本人已经准备好原谅这些行为了。这种政治伦理——马基雅维利认为是一个好人应该提出的良好建议——比老生常谈的“目的正确即手段正当”必定会更加令很多读者不适,然而它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君主论》(拿破仑批注版)
人们还有一个流行的误解,即把马基雅维利的著作视为对政治生活的客观的研究结果,并把马基雅维利本人视为当代政治科学的先驱者之一。恩斯特·卡西尔说:“伽利略的《对话》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确实都是‘新科学’”。正如伽利略力学成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马基雅维利也开创了政治科学的新路径。但是,卡西尔和其他的分析者都忽略了马基雅维利自己的意图:在创作全部政治和历史著作的时候,马基雅维利不仅像科学家那样去描述和解释事实,最重要的是他还像演说家那样去劝说读者采取行动。如果仅把《君主论》和其他的著作当作一种科学研究的文本去阅读,那么我们可能根本无法理解这些著作的意义,也无法读懂作者的意图。
通过触动读者的心灵、调动读者的情感,马基雅维利试图敦促他们能有所行动。像当时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那样,他在创作著作原稿的时候遵循了古典修辞学的原则。佛罗伦萨将雄辩术视为自由的政治生活的最高点缀,也是优秀公民必备的素养。马基雅维利生于斯,也在这里接受了教育,因此他彻底养成了这种思考和写作的方式。此外,他曾经担任过佛罗伦萨共和政府第二秘书厅的秘书长,还接受过当时的著名学者马尔切洛·阿德里亚尼的学术训练。因为工作的需要,马基雅维利一直从事着政治修辞术的实践,尤其是在内政外交政策事务上,他要给共和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写信,或者时时要为共和政府的最高执政者们撰写演说稿件。他的信件和演说稿件必须要迎合那些乐于欣赏优雅文风和论说文章的人群,因为他们都熟练地掌握着各种修辞术。
很多读者把《君主论》视为一本政治科学手册,但实际上它是一篇长演说词。正如文艺复兴时期很多其他的演说词一样,《君主论》开篇附有一篇恰如其分的序言。“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上洛伦佐·梅迪奇殿下书”的献词应该足以引起读者的兴趣。马基雅维利必须要非常谨慎,因为他曾经是前共和政府的秘书长,而现在人微言轻的他竟然敢对新政权的事务指手画脚。这在当时是非常出位的行为,因此他必须用一篇短短的序言来努力消除梅迪奇对自己的敌意。马基雅维利倒是收获了读者的好感,他在序言中展现了自己的善良品质、为国履职的服务经历,以及处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同时他还历数了苦难和恶意带给自己的厄运。他坚信恰恰是自己的身份,才使他最适宜来讨论国家的事务。“我想,一个身居卑位的人,敢于讨论和指点君主的政务,不应被当作僭妄,因为正如那些绘风景画的工匠,为了考察山峦和高地的性质便侧身于平原,而为了考察平原便高距山顶,同理,深知人民的人应该是君主,而深知君主的人应属于人民。”
将《君主论》视为一份演说词的最清晰证据在其最后一章“奉劝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这一章,马基雅维利整部书可能无法引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从而让他们有所行动。他撰写这一章的目的就是要激发读者的愤慨和同情,这很明显不是一位科学家应该做的事。通过突出蛮族施加于意大利之上的残暴和傲慢,马基雅维利向读者传递了愤慨的情感;通过指出意大利的孱弱和无助,他又向读者传递了同情的情感:“比希伯来人更受奴役,比波斯人更受压迫,比希腊人更加分散流离,既没有首领,也没有秩序,受到打击,遭到劫掠,被分裂,被蹂躏,并且忍受了种种破坏。”(P,XXVI)很多马基雅维利的评论者认为最后一章与《君主论》前面的内容存在冲突,但事实是“奉劝章”才是整部著作最恰当的结尾。
马基雅维利在自己所有的著作当中无数次地提到了古典和现代的历史人物,他的目的就是要使自己的论证更加生动清晰和具有说服力,从而激发人们产生热情去效仿伟大的政治和军事首领。“当论述君主和政府都是全新的君主国的时候,我援引最伟大的榜样,任何人都不应该感到惊异”,因为一个理智的人必须要效法伟大人物的足迹,即便“能力有限无法像他们那样强大,但至少会带有几分气派。”(P,VI)基于同样的原因,马基雅维利大量使用了明喻、象征和隐喻。在解释君主必须能够运用诈术和暴力的时候,他借用了狮子和狐狸的象征。在论述君主绝不应该依赖援军的时候,他在《圣经》当中找到了一个“特别合适的人物形象”来说明问题。“大卫请求扫罗王让自己同非利士人的挑战者歌利亚战斗。于是扫罗为着使他壮胆,把自己的铠甲给他穿戴,可是当大卫试了一下之后就立即谢绝了。他说,铠甲限制了自己的力量,他宁愿使用自己的投石器和刀同敌人周旋。”(P,XIII)
把马基雅维利视作一位演说家而非政治科学家,这个判断可能会削弱他在一些读者和学者心中的地位,因为他们认为政治学应该通过类似其他社会科学甚至是数学的方式,来加以研究。但是我认为,基于历史知识的政治学研究要比18世纪开始就取得智识霸权地位的科学路径,来得更加有效。我强调马基雅维利的演说家身份,这将使他居于当代学者之上,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恢复了事情本来的面目。
另外一个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流行看法是把他视为政治男权主义的始作俑者。马基雅维利坚信自主、理性的男性价值优于依赖、非理性的女性价值,因此他的政治活动就像是一个充满焦虑感的男人誓死捍卫某些男性气质。但是,撇开当时的历史环境,马基雅维利在评论现实中的女性时,使用了平等的语言。马基雅维利曾经与一位妓女里恰保持了多年的情人关系,他称呼她为“女性朋友”(amica)。他平等地对待女性,有时甚至甘愿沦为她们的附庸。里恰小姐跟马基雅维利对话的时候,则把他当成一位男性朋友。一旦她厌烦了贫困潦倒的马基雅维利,就直接称呼他为“家里的害虫”,正像马基雅维利的老朋友多纳托·德尔·科尔诺叫他“店里的害虫”一样(L,278)。在颇具自我幻想色彩的诗歌《金驴记》(Ⅵ,25-7)当中,马基雅维利讲述了对待女性的平等态度和他们之间的友谊。故事的主人公说:“过了片刻,她(喀耳刻女巫的侍女) 还有我,便一起絮叨了许多许多的事,就像一个朋友与另一个朋友在对话。”马基雅维利这里写“另一个”的时候,使用的是阳性的意大利语单词l'altro,表示的是一个男人与另外一个平等的男性朋友之间的对话。
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和他的个人生活充分证明,他乐于牺牲自主的男性价值而换取依赖的女性价值,并且他也十分乐意委身于激情。1515年1月16日,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写信给马基雅维利说,“再也没有比性爱更幸福的事情了。男人可以按照喜好发表各种高谈阔论,但这是一个纯正的真理。”(L,311)马基雅维利则在回信中附了一首十四行诗来表达爱的力量,他说即便自己知道如何挣脱爱情的锁链,他也不会那样做,因为“这些镣铐甜蜜,时轻时重;它们把我重重绑缚,以致使我认为,没有这种生活,我会活得毫无乐趣可言。”(L,312)他知道爱情会给自己带来痛苦,但是美妙的女性则太过强大和诱人。“我在其中享受了如此的甜美,既因为那美好和温柔的容颜,又因为它使我忘掉了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这世间我最不想要的就是那些痛苦的回忆,而我得到了解脱。”(L,293)如果捍卫自主是男权主义的典型特点,那么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确是名不副实的。
几个世纪以来,马基雅维利被视为暴君的导师、狂热的共和主义者,或者一个为了权力而愿意委身于任何主子的人。但是,1521年当佛罗伦萨前共和政府的正义旗手,同时也是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庇护人皮耶罗·索德里尼,要为其提供一个为雇佣兵首领普罗斯佩罗·科隆纳担任秘书的高薪职位的时候,马基雅维利拒绝了,尽管当时他基本赋闲在家,唯一的工作是以微薄的收入受枢机主教朱利奥·德·梅迪奇的委托在编纂佛罗伦萨的历史。早些时候,马基雅维利还拒绝了出任拉古萨共和国的高级行政职位的邀请。由此可见,马基雅维利并不是一个愿意攀附权贵的人。
与其去追求权力,马基雅维利更愿意展示自己的治国才干和正直品格。在1513年12月10日写给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著名信件中,他流露了希望梅迪奇雇用自己的强烈愿望,哪怕是能够出任最微不足道的职务。马基雅维利通晓治国之术,并且对共和政府怀有无可置疑的忠诚。他希望梅迪奇能够阅读自己写就的“这小小的一卷书”,并认真考虑自己曾经对佛罗伦萨所做的一切。“到时候,我若不能获得他们的眷顾,我就只好怨自己了。他们读了这本书(《君主论》的手稿)就会发现,十五年来我既没有睡大觉,也没有混日子,而是一直在钻研治国的技艺,谁都会乐于接受一个能从他人失败的代价中汲取丰富经验之人的服务。至于我的诚实,应该没问题吧!因为我一直保持着诚实,所以现在也不会去毁掉它,况且像我这样一个四十三年来一直保持诚实的好人,是不会改变自己的本性的;能够见证我的诚实与善良的,正是我的贫穷。”这绝不是一位热衷于向任何形式的政权乞食的人能够说出来的话,而更像出自一位愿意献身国家,并渴望成就伟大功绩的公民之口。
由于梅迪奇家族持续的敌意,除了一些十分卑微的差使之外,马基雅维利再也没有能够担任任何高级的职位。1521年,作为佛罗伦萨任命的使节,当马基雅维利被派往摩德纳附近的卡尔皮去参加方济各会修士大会的时候,他还要为梅迪奇处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马基雅维利到达卡尔皮后,在佛罗伦萨羊毛业行会的一位官员的请求下,他甚至还要去处理一件更加不光彩事务——找一位四旬斋节的布道者。即便这件事对自己的才干和名誉是一种侮辱,马基雅维利仍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为共和国服务。“无论何时只要能为共和国排忧解难——若无法以行动,便以言辞,若无法以言辞,便以表情——我都不曾让她失望,所以现在我也不打算让她失望。”马基雅维利亲身实践了自己宣扬的教义。在《论李维》当中,他还说“地位尊贵的公民,不可蔑视人微言轻的公民。”(D,Ⅰ.36)
《论李维》
马基雅维利最有意义的工作是其关于政治自由的共和主义理论著述。他创作《论李维》来复兴古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智慧,并以其为摹本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政府形式,以及何种精神伦理最适于维持自由和伟大共和国的重要思想。他认为良好的政治制度需要合理的军事规范,因此,他还创作了《用兵之道》来复兴和实践古罗马传统的军事制度(AW,Preface,4-5)。在他最后的一部重要著作《佛罗伦萨史》中,他敦促人们吸取先辈们的沉痛教训,避免他们曾犯下的错误,使自由丧失,城市腐化,同时,他希望人们能够遵循共和国政治那些真正的原则,最终过上一种自由的公共生活。
后世的政治理论家承认,马基雅维利是共和主义传统的一个分水岭。共和主义发端于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政治观念,在数世纪的时间里发展出了关于政治自由及其制度和道德条件的一系列观念。但是只有到了马基雅维利的时候,共和主义政治观念才开始面对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意大利社会的所有问题。基于这个原因,当然也因为马基雅维利的优雅文风,所有现代的共和主义思想家都能够从他的著作中得到启发和教诲,即便他们也提出了不少的批评。
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与他个人真正的政治信仰,无法画上绝对的等号。正如两位著名学者最近指出的那样,他从来都不属于梅迪奇政权的一份子。梅迪奇政权(1512-1527年)本质上是君主制的,它的重要家族成员控制着城市的政治。因此马基雅维利从未赞扬过该政权,梅迪奇也从未认为马基雅维利是其朋友。马基雅维利曾明确地表示共和制政府优于君主制。“说到做事的精明和持之以恒,我以为人民比君主更精明、更稳健,判断力更出色。人民也许在大事上、或在有益的事情上出错,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但是,君主不是也经常因为自己的欲望而栽跟头,并且次数大大多于人民。还可以看到,在推选官员上,他们的选择远胜过君主;人民也从来不会惑于言辞,把荣誉授予声名狼藉、腐化堕落之徒;而劝说君主不但容易,手法又何止千万。”除此以外,他还说,“可以看到,在人民担任统治者的城邦,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超乎寻常的扩张,比一直受君主统治的城邦大得多。例如驱逐了国王后的罗马,以及摆脱了皮西斯特拉图斯后的雅典。民治优于君主统治使然,除此而外,再无其他原因。”(D,Ⅰ.58)
另外还有一份关于马基雅维利共和主义立场的强大证据,那就是1521年他在枢机主教朱利奥·德·梅迪奇的一再要求下,谋划了一份佛罗伦萨宪制改革的建议书。在这份文本中,马基雅维利公开建议这位权高位重的枢机主教恢复城市的共和政治。他解释说,佛罗伦萨的平等传统使人民无法容忍一位君主,如果硬要给这个城市安排一位君主,那就是残暴和令人憎恨的行为。不满足人民的需求,城市就不可能拥有一个稳定的共和国。唯一让人民满意的办法就是“重新敞开政府的大门”,也就是恢复共和制政府。除了共和主义,马基雅维利再也不可能有其他更明白、更重要的立场了,因为这份建议书的直接呈送对象是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枢机主教梅迪奇。
《曼陀罗》(五幕喜剧)
除了重要的政治和历史著作,马基雅维利还创作了意大利最优秀的戏剧之一的《曼陀罗》。他完成该作品的时间大概是在1518年前后,或许他当时正处于人生最难过的时期。那时他已经六年没有任何工作了,也完全没有可能得到一份来自于佛罗伦萨或罗马的新工作。他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朋友,与家人仅靠着乡下的一点薄产而苦苦挣扎。他甚至曾经幻想过抛弃佛罗伦萨和家人而去外地教小孩子读书写字。然而,他还是选择留在了佛罗伦萨,并创作了一部让观众捧腹大笑的著作。如果有人觉得写这样的故事会使一位睿智和严肃的人显得不甚得体,那么马基雅维利说:“请找这样的借口吧,为了让他痛苦的人生变得好受一点,他不得不进行琐碎的思考;否则他又能做什么呢?真可谓英雄无用武之地,一文不名了。”既不是什么军官上校,也不是什么立法者、君主,这部戏剧的主人公们包括了“一位忧郁的情郎,一位无论怎么看也不精明的法官,一位邪恶的修士,还有一位无恶不作的食客”。整部作品都不是要激励人们去效法高尚的道德模范,而仅仅是为了博人们一笑。马基雅维利说,“如果你不笑,我愿意替你出酒钱。”(OW,Ⅱ.776-7)
马基雅维利既能写严肃的政治著作,也能写一些短小、诙谐和自嘲的作品。他生活在这种哲学精神之下,甚至还做过一番理论上的总结。马基雅维利在一封写给韦托里的信中说:“任何人要是看到我们的书信,我敬爱的同道啊,看到它们的丰富多彩,必定会大为惊讶。乍一看,我们似乎都是严肃的人,注意力完全集中于重大事务,头脑中流过的任何想法,无不关乎庄重、笃实。不过翻到下一页,读者就会发现,我们——仍是同一个我们——猥琐、轻浮、好色,专爱干些荒诞不经的事。这种行为若在有些人看来是可鄙的,在我看来则是值得称道的,因为我们是在效法自然,多变的自然。任何效法自然的人都不应当受到非难。”(L,961-2)。很少政治理论家能够像马基雅维利这样把不同的思想维度调和在一起,严肃与琐碎、寻常与宏大、相对与绝对。正是因为他表现出的独特的智慧和深邃的人性特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在今天仍是值得认真阅读的。
本文为“大家读经典”系列之《如何阅读马基雅维利》的导论,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如何阅读马基雅维利》,【意大利】毛里齐奥‧维罗利/著 刘国栋/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22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