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网站近期载文称,共和党内部在外交政策上可以划分为三派,随着特朗普连任失败,共和党内围绕外交政策的辩论将进一步被激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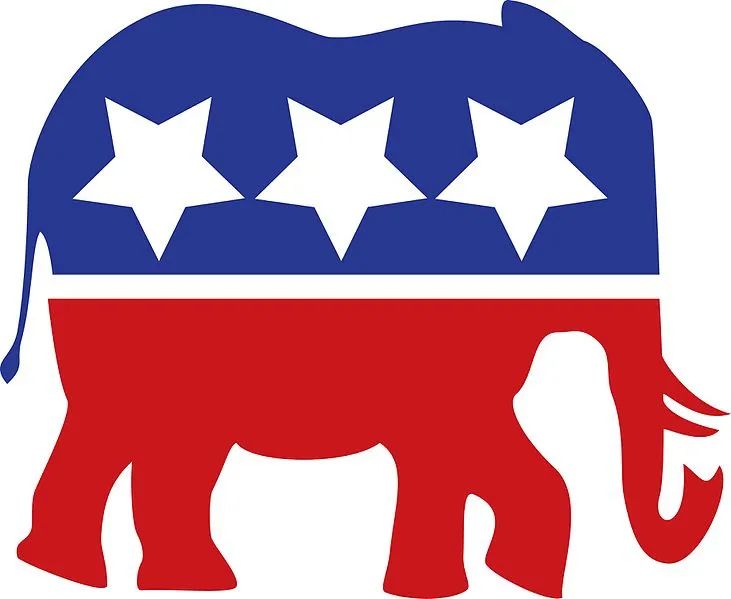
文章摘要如下:
在听到拜登组建外交政策团队的消息后,有的共和党人批评他们是“礼貌而有序地看着美国衰落的人”,有的则把这个团队贬为一群“战争狂热分子”。之所以出现不同声音,是因为共和党内部在外交政策上存在分歧。没有了特朗普这位起到凝聚作用的共和党总统,这些分歧将浮出水面。
共和党围绕外交政策分为三派
全美范围内的保守派和共和党人可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群体:外交政策行动主义者(foreign-policy activists)、外交政策强硬派(foreign-policy hardliners)和外交政策不干涉主义者(foreign-policy non-interventionists)。
共和党外交政策行动主义者支持美国建设海外基地、实施对外援助计划和打造强大军队。他们认为,美国在其主导的海外伙伴关系秩序中是领袖;他们愿意支持国际组织,面对美国的对手通常不会让步;他们倾向于与美国盟友达成开放的贸易协议。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四五年前,共和党外交政策行动主义者在党派内部的外交政策辩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目前,这群人在参议院中的代表人物包括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犹他州联邦参议员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Nikki Haley)也是主要人物。
共和党外交政策不干涉主义者反对在海外进行武装活动,认为美国的军事联盟带来的麻烦多过好处,并对向特定对手作出外交妥协持开放态度。他们呼吁撤销美国在海外的军事承诺,削减国防开支。这一群体虽未构成共和党选民的多数,但却是少数中的多数,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大流派: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和民粹主义者(Populist)。
自由意志主义者热衷于自由贸易,认为美国广泛的军事承诺是对公民自由和国内有限政府的破坏;民粹主义者更有可能是保护主义者,对针对美国特定竞争对手的强硬政策持开放态度。不过,双方都对“无休止的战争”表示担忧。前者的代表人物有肯塔基州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后者的代表人物除了特朗普外,还有福克斯新闻的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不过华盛顿大多数外交政策建制派并不重视塔克。
然而,大多数观察人士未注意到的是,多数基层共和党选民既不是严格的行动主义者,也不是严格的不干涉主义者,更确切地说,大多数共和党选民属于第三个群体:共和党或保守主义强硬派。
共和党外交政策强硬派倾向于建立强大的美军、实行强有力的总统领导、制定有攻击性的反恐政策。他们认为,危险的国际环境需要美国对众多威胁采取惩罚性态度。同时,他们对全球治理项目、多边主义协定和海外国家建设任务避而远之。
生活在美国农村、远郊和小城镇的保守派中,强硬派是最多的。他们在参议院的代表人物包括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得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和密苏里州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不过,该群体内部也存在分歧。例如,科顿在中东问题上比霍利更强硬;与克鲁兹相比,霍利对向美国各贸易伙伴征收保护性关税持更开放的态度。
近年来发生的变化
特朗普在2016年取得的政治成就是,他察觉到共和党可能会形成二战前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新联盟。他并不是通过重申自由意志主义的外交政策偏好,而是把不干涉主义者和强硬派团结在一起,反对自1940年以来主导共和党的行动主义政策。建制派共和党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革命性的,这确实如此。
普通共和党选民绝不是“孤立主义者”。根据过去四年的民意调查,大多数共和党人仍然支持北约等美国在海外的关键联盟,大多数共和党选民对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没有好感,并没有突然从纯粹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变成纯粹的保护主义者。更确切地说,与整个美国一样,在共和党选民中对经济全球化有一种长期存在的矛盾心理,特朗普承认并反映了这种矛盾心理。
话虽如此,共和党的外交政策观最近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而这些都建立在共和党内部的长期变化之上。与冷战时期相比,今天的共和党更依赖于工薪阶层和未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的支持。随着时间推移,它已经成为一个更加民粹主义和文化保守的政党。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今年9月的民调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大多数共和党人认为,美国最好是“自给自足,无需依赖他人”。
未来会怎样?
共和党的不干涉主义者处于有利位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废除美国的海外战略承诺方面,特朗普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走得那么远。与此同时,自由意志主义者将继续艰难地争取大多数共和党人对其外交政策偏好的支持。
未来可能出现不干涉主义者和强硬派的联盟。当然,这一联盟包含某些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但至少特朗普最近建立了这样一个联盟,而且他丝毫没有打算隐退,将继续在所有与共和党有关的事情上大声发表意见,甚至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这一前景,再加上特朗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受欢迎程度,意味着2024年的总统竞选人在制定议程时会考虑特朗普因素,这也可能对共和党的外交政策辩论产生影响。
共和党国家安全行动主义者可能会通过在各方具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与强硬派联手而东山再起。最明显的问题是中国。事实上,在国会层面上,共和党强硬派和外交政策行动主义者之间的工作联盟已经形成。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随着特朗普即将卸任总统,过去的四、五年可能会被视为共和党外交政策传统中的一次反常,现在可以当这些年从未发生过,回到正常轨道上。然而,这可能是妄想。从一开始,格外强烈的美国民族主义就一直是共和党的核心特征。展望未来时,这一特征产生的具体政策影响肯定值得讨论,但这种现象远比特朗普个人严重,它会继续存在。
本文编译自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文章The GOP’s foreign-policy tribes prepare for battle,作者为乔治梅森大学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柯林·杜克(Colin Dueck)。译者:沈凯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