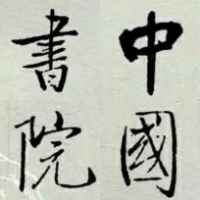范广欣||从“大书院”到“大学”:近代中国对university的翻译
范广欣 江海学刊
本文发表于《江海学刊》2019年第4期

作者简介:范广欣,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
近代以来university的主要汉译及其升降起伏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意涵,揭示了中国人认识西方大学、探索大学理念的不同心态和视角。从1866到1895年是无可争议的“大书院时代”,尽管多种翻译并存乃至竞争,“大书院”却处于一种绝对的优势地位。从1895到1911年,“大学堂”逐渐取代“大书院”成为官方认可的翻译。直到民国以后,“大学”作为university的标准翻译最后确立。甲午战前中国人对西方和日本多种大学模式均有观察和体验,他们往往重视书院与英美大学的比较,甚至认为英美大学与当时的书院相比更好体现了书院的理想,这是他们多用“大书院”翻译university的理由。甲午战败之后,日本模式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但是,最后确定的标准翻译“大学”,虽然直接来源是日本,却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含义,在全盘西化、日化的时代,承载着民族的教育理想。
关键词
书院 太学 大学 学院 大学理念
从1895年开始,中国最早的一批公立大学逐渐创办,标志着中国大学理念已经初步走向成熟。本文期望梳理汉文文献对university或college等相关词汇的翻译过程,尤其注重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创办前后的变化,发掘不同汉译及其兴衰替代的历史和文化涵义,以探索中国大学理念的萌芽和演变。
关于中国大学创立以前汉文文献对university等西式高等学府的翻译,在本文之前尚无专门研究。从少数学者的相关叙述可以发现:当时曾经出现过各式各样的翻译,西方传教士在翻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对university或college等相关词汇的汉译迅速在中国流传,并取得支配地位。本文梳理了从明末清初耶稣会开始的对西方university的翻译到民国初年“大学”成为固定翻译的全过程,揭示主要汉译及其更替的文化意涵,以及不同汉译蕴含的中国人认识西方大学、探索大学理念的不同心态和视角。从方法上说,观点的推进主要得益于对传教士、出洋中国人乃至国内官员士大夫、洋务知识分子涉及西方以及日本教育制度的基本文献的整体把握和具体解读。此外也运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全文检索数据库(1830~1930)作为补充资料,并对不同翻译在不同时期的升降替代作了统计。具体而言,本文最重要的发现是从1866年到1895年是中国大学理念史上无可争议的“大书院时代”,这一时期尽管多种翻译并存乃至竞争,“大书院”却处于一种绝对的优势地位,人们往往是从书院的理想出发观察西方和日本的university或其他高等院校。甲午战争失败和北洋大学堂建立是“大书院”这个翻译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是,实际上其优势地位直到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官方政策以学堂全面取代书院才受到真正的挑战。
最早的翻译
西方的university在中国最早的翻译就目前所见,应该是出自明清之际传教士艾儒略(J.Aleni,1582~1649)的地理学著作《职方外纪》,这是汉文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对欧洲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校制度的介绍,而且就是用我们今天习惯的称呼。后来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的《坤舆图说》也有大致相同的介绍。《职方外纪》里提到欧洲的各所university还普遍使用“共学”的说法,也用过“公学”指欧洲现存最古老的意大利博乐业(Bologna)大学。这两个称呼后来并没有广泛流传。《职方外纪》中也提到“书院”,不过看起来并不是指教学场所,而是指图书馆。
尽管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已经用“大学”翻译university,我认为今天将university普遍翻译成大学,是借用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作法,而不是受到明清之际传教士文献的直接影响。因为从《四库全书》的编者以来,中国读书人便对这些文献中所介绍的世界地理特别是欧洲的文明,持相当怀疑的态度,雍正以后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更是受到官方的限制,所以这些文献在中国相当长时间内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不过,当晚清读书人越来越有兴趣了解西方的时候,这些收入《四库全书》的文献很可能被重新发现,充当一部分读书人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准备。
大书院时代
1“大书院”的由来
晚清传教士再次进入中国时,跟先辈不一样,他们把西方的学校,甚至他们自己在中国办的西式学校都称为书院,因为他们了解到书院是当时中国最普遍的中高等教育的学校形式,希望这么做可以促进中西文化的沟通。顺理成章university或提供高等教育的college也就获得大书院的称呼,原意即规模较大、级别较高的书院。
一般认为,书院兴起于唐代,逐渐发展出一系列私人办学的特点,比如自由创办、师生互择、自由讲学,渐取代官学系统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流。南宋以来书院更与理学结合起来,不仅强调自主研修学问、奖掖后学,还变成读书人试图转移人心风俗、改造社会与政治的基地。明朝后期围绕东林书院更形成了士大夫抗议运动的中心。书院的理想发展到顶峰,也因此遭到专制皇权的一再打压。清中叶以后,书院接受了官学化的改造而再度兴盛,其代价是受到政府严格的控制,失去了许多传统的自由,与科举考试的关系变得紧密,乃至和官学一样成为科举附庸,书院的理想和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差距。不过,许多著名的书院仍保留一定的自主性,仍为传统学术的中心,有志之士创建或领导的书院为学风向纯学问或经世致用再次扭转做了积极的努力。总而言之,书院的理想直到晚清仍然是士大夫珍视的价值。
从1866年到1895年,无论是中国派到海外的官员和其他出洋人士的游记日记,还是在华传教士的介绍文字,乃至国内主要官员给朝廷的奏折均普遍以书院称呼西方学校,并采用大书院作为university或提供高等教育的college的通用译法。这段时期我称为中国大学理念史上的“大书院时代”。其特点是:出洋的中国人观察西方大学,多以中西文明交流为基本出发点,他们对包括书院在内的中国文明的基本信心尚未动摇,所以一般都比较重视传统书院与西方式大学的比较,希望能够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中国固有的书院制度而不是对其全盘否定。随着时间流逝,中国有识之士的态度也发生变化,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起初人们多强调西方大学与传统书院的共通之处,肯定在遥远的欧美也存在发达而完善的学校制度,可以与中国媲美。逐渐西方大学独特的优点越来越得到肯定,相比之下,现实中书院的许多缺点越来越暴露出来,但是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传统书院的理想被放弃,有些人宣称西方的大学比当时中国的书院更符合传统书院的理想。最后,越来越多人得出结论,传统书院的理想不能涵盖西方大学的所有优点,如果两者不可得兼,为了国家的生存必须引进西方的学校制度,书院的理想便不得不放弃,这样“大书院时代”也就终结了。1895年盛宣怀创办了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很快就改称北洋大学堂,更重要的是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立,不仅以“大学堂”作为university的官式翻译,而且朝廷要求在全国范围内以学堂取代书院。这样“大学堂”便取代“大书院”成为university最常见的汉译。
中国外交官和洋务知识分子使用大书院这个名词翻译university,我认为是受到徐继畬(1795~1873)《瀛寰志略》的影响,因为徐继畬曾经任职总理衙门,他的《瀛寰志略》是外交官必备的参考书,包括各种出使日记在内的大量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徐继畬在介绍欧美各国的时候,多次用大书院指当地的著名高等学府。徐氏在福建当官时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1804~1846)过从甚密,一般认为《瀛寰志略》得以成书,不少资料来源于他。关于university的知识和大书院的译法,多半也是从传教士来,但是笔者目前并没有证据。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全文检索数据库(1830~1930)中,最早出现的用“大书院”翻译西方高等学府的例子就是来自1843年版《瀛寰志略》。事实上,“大书院”当时在汉文里已经形成一个专有名词,而不仅仅是“大”和“书院”的随机组合:经过明清之际的萧条,雍正以后清朝政府重新对书院采取了扶持的态度,特别是有计划地在各省主要城市建立官办书院,成为“国子监”以下各省的最高学府,俗称省会大书院或大书院,著名的有长沙岳麓书院、保定莲池书院和江宁钟山书院等。因此,把西方的university或者提供高等教育的college统称为大书院,在华夏中心观念较强的时代,其实是承认它们相当于中国各省的最高学府,是对这些学校能提供高水准教育的肯定。
2中国人的其他译法:“大学院”和“太学”
可是,在大书院时代对university或提供高等教育的college也存在其他译法。比如张德彝(1847~1918)的有关出使笔记就用“大学院”。张氏是同文馆的毕业生,懂英文,从1866年起先后担任斌椿、志刚、郭嵩焘、曾纪泽等人的出使随员,最后获委派为驻外公使。他的译法笔者想并非来源于徐继畬的中文著作和同文馆的师训,或者是他本人从英文直接翻译出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名词与“大书院”结构基本相同,用它来称呼西方的高等学校,很可能也是从“书院”或“大书院”演变过来。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今天采用的标准翻译“大学”两个字已经包含在“大学院”这个名词里,“大学院”可以理解为提供“大学”教育的场所。这说明中国人虽然一开始不是用“大学”称呼西方的高等学校,但是最后采用它是有一定基础的,因为在我国经典的传统里一直用“大学”(与“小学”相对)来描述高级教育。1876年代表中国海关到美国参加博览会的李圭(1842~1903),在其日记中虽然沿用“大书院”称呼英美的高等学校,却同时指出这些学校提供的教育相当于中国传统所说的“大学”阶段,学生要经过“小学”阶段,考试成绩优异才能升学。
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1818~1891)除了用“大书院”称呼牛津、剑桥等校,这很可能是受到张德彝的影响,还用“学院”来称呼牛津、剑桥的成员college(后来“学院”成为college的标准翻译之一,一直沿用至今)、用“大学院”称呼他在苏格兰见到的university。此外他还用过“大学馆”或者“上学馆”的称呼(“学馆”是当时对教育场所的统称之一,早期学习西方语言及技术的机构曾经用过这一名称,比如“同文馆”和“广方言馆”),但是比较少见,其他人也不用。他参观牛津时更指出:相比之下,在英国,牛津、剑桥是“大学”,而其他一般学校是“小学”,强调牛、剑在英国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其副使刘锡鸿,虽然对新鲜事物的态度比较保守,与郭氏诸多意见不合,但在日记中也承认牛、剑是“大学之处”。
有趣的是,郭氏在瑞士参观时甚至第一次用“大学”来称呼当地的university。曾国藩的门人之一黎庶昌(1837~1897)曾担任驻法公使的随员,也用过“大学”一词,但是所指不详。一直到19世纪末,外出使节或其他读书人都很少用“大学”来称呼他们在欧美看到的university。
必须再三强调,从李圭到郭嵩焘、刘锡鸿等人用“大学”这个称呼都是与“小学”相对,代表教育的两个不同阶段,他们没有大、中、小学三级制的概念。根据儒家的传统观念,教育包括“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前者是普及教育,后者是精英教育,虽然这个分类并不一定与特定学校制度或教育场所相联系。理学认为“大学”阶段的目标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此儒家经典《大学》有详细的阐述,“小学”阶段则强调学习洒扫应对等基本礼仪,也包括识字和基本道德教育。清朝汉学把“小学”理解为文字训诂等考据学的基本功,认为只有通过这些基本功,才能探讨经典中的精深学问。虽然对“小学”的理解有差异,不过无论理学还是汉学都承认“大学”代表学习的高级阶段,而且必须以“小学”为根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中学”这样一个中间阶段。
另外,除了“大书院”,王韬(1828~1897)和刘锡鸿都曾经把university称为“太学”。办洋务出身的驻德公使李凤苞(1834~1887)更是基本上用“太学”来称呼university。“太学”是中国传统的最高国立教育机构,也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不同的时代名称有差别,清朝称为“国子监”,一直存在到1905年,才被京师大学堂取代。太学的基本特点是官僚化、等级化,教学的目的不在学术创新,而在巩固正统、培养官员。而书院虽然在清朝后期日益官学化,省会大书院财政上更依赖地方政府,但是毕竟仍然保留了许多私人办学的特点,比如密切的师生关系、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在科举应试之外兼容多样化的学术兴趣(包括理学、考据学和经世之学)等。把university称为“太学”其实含义与“大书院”相当不同。
王韬是否有意识地选择“太学”作为university的另一汉译呢?让我们一起来梳理他使用这一称呼的不同情况。王韬应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之邀访问牛津的时候曾经写诗留念:“尝观典籍于太学,品瑰奇于名院。”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文学修辞,不一定反映他理性的认识,因为在王韬留下的文字中,一般把西式学校称为“书院”,而把高等学校称为“大书院”,如英国的牛、剑和法国的索邦(Sorbonne)。但是,我们发现王韬记载他在牛津用中文发表演讲时提到:“尔众子弟读书国塾,肆业成均。”“国塾”很明显指的是国立学校,“成均”源于《周礼》“掌成钧之法典,以治建国之学政”,习惯上作为“太学”和“国子监”的代称,朝鲜王朝的最高学府便称为“成钧馆”。所以,他用“太学”来称呼牛津并非一时偶然。他敏感地发现了两者的共同点:(1)都是大规模提供高级教育的学校;(2)与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学生毕业要进入仕途,为国家服务。根据他的记载,牛津许多毕业生都由国家铨选为官员,学习东方语言文字的则被派遣到印度和中国担任翻译人员。
但是当李凤苞介绍柏林大学的时候,却称其为“太学”。尽管有证据表明李凤苞也以《瀛寰志略》为基本指南,但他仍然以“书院”为学校的统称,与其他外交官没什么不同。我们觉得他采用这个翻译有三种可能:其一,因为柏林大学是建在德国首都的国立大学,德国一向比较强调大学与国家力量的互相支持,因此符合中国人对“太学”地位和作用的理解;其二,可能是受日本人的影响。李凤苞曾经记载与日本人笔谈,有日本人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指出英国只有牛津是“太学”,但是只收英国国教徒,后来才添设伦敦太学(London University),兼收其他宗教的学生,所以作为日本人在德国拿博士比英国容易。很可能“太学”这个说法是反映了日本人对university的理解,下文再仔细讨论。第三,李凤苞是洋务知识分子出身,与科学家徐寿(1818~1884)过从甚密,参与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兴办格知书院的工作,而下文将会指出太学/太学院之类的翻译正反映了一部分传教士的偏好。
1895年以后中国人曾经采用大学堂作university的正式译名,在1895年之前,虽然“大学堂”这个词已经出现,但是用来指涉university的并不多见。祁兆熙(?~1891)曾奉清政府之命送幼童赴美国留学,他在《游美洲日记》提到“大学堂”“小学堂”“总学堂”的说法,但是前二者中“大”“小”是描述学校的规模,而非教育的等级,后者是指公立学校,他在同一段文字中还是用“大书院”称呼分专业教学的高等学府。黎庶昌在《西洋杂志》中介绍法国和西班牙的高等教育,则用“总官学堂”翻译法国拿破仑以来形成的imperial university (Université de France),实际上这套中央集权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并没有综合大学的位置,他也用“学堂”翻译西班牙的高等专业学校,如农务学堂。目前所见,只有郑观应在1884年写作的《考试》一文(收入《盛世危言》)兼用“大书院”和“大学堂”称呼外国的高等学府。
事实上,当时中国国内也是用“学堂”来称呼同治中兴以后新办的教授西方语言和技术的专业学校。1895年以前在出洋中国人的记录中,“学堂”作为学校的统称开始出现,并且逐渐变得普遍,但是,“学堂”尚未取代“书院”的地位。一般还是用“书院”翻译综合多科学校,用“学堂”翻译专业学校。从自强运动到戊戌维新,中国国内书院与学堂并存,书院作为包括理学、考据学、经世学和科举应试之学在内的士大夫之学的场所占据主流地位,学堂作为培养与西学有关的洋务专门人才的场所,则是日益壮大的支流。书院在国内的优势地位决定了“书院”和“大书院”作为西方学校汉译的优势地位。
尽管有一些变数,但是总而言之,到欧美国家去的中国人一般都用“书院”来统称西方的学校,而用“大书院”指高等院校,对应的英文包括university、college和institute。到日本去的人,因为日本用汉字,不需要翻译,全都采用日本的用法“大学校”或“大学”而不用“大书院”,他们观察的主要对象是东京大学或者是后来的东京帝国大学。然而,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驻日外交官的记录,比如黄遵宪(1848~1905)的《日本杂事诗》和《日本书记》都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才受到人们重视,所以“大学”以及“大学校”直到1895年以后才在中国国内流行起来,并旋即压倒长期使用的“大书院”和官方比较倾向的“大学堂”,成为日常语言中最常见的译名。
3传教士的其他译法:“太学院”“太学”和“普书院”
在华传教士除了采用“大书院”以外,还曾经用过“太学院”和“太学”的说法。1873年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的《德国学校论略》(又称《西国学校》)出版,介绍德国发达而全面的学校制度,对郑观应(1842~1922)、梁启超(1873~1929)等人的教育改革思想影响甚巨。花之安以“书院”为基础,发明了一系列学校的名称,比如“郡学院”“实学院”“武学院”“仕学院”等,他把university翻成“太学院”,跟张德彝用的“大学院”非常接近,像是“太学”跟“书院”结合到一起的产物。1883年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考察西方和日本教育的报告,由总理衙门出版,命名为《西学考略》,提到university时“大书院”和“太学”两个称呼都使用。从中国传统习惯来看,“太学”全国只能有一所,而西方国家往往有多所university,所以并不很妥当。他想强调的是国家与大学的互相依靠:国家支持高等教育,大学为国家服务。“太学院”或“太学”作为university汉译的兴起,很可能是反映了德国和日本大学模式的影响。一部分传教士认为,普法战争以后统一的德国和明治维新以后国力上升的日本,成为说服中国官员和朝廷采用西式学校制度以挽救衰亡的最佳范例。
1889年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讨论西方和日本新学的文章,并于1892年以单行本出版,这就是著名的《七国新学备要》,在这些介绍文字中他用“大书院”和“普书院”称呼西方的高等学校。据笔者考察,“大书院”是指college,而“普书院”是指university,也许是强调综合大学对不同专业的相容并包。“普书院”从“大书院”里面分化出来,并不难理解,差不多就是这段时间,伴随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先前的许多college逐渐升格为university。李提摩太的用法能够代表当时的潮流,许多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文章都是这么用。甚至到1896年“大书院”时代由盛转衰以后,还有传教士继续使用“大书院”和“普书院”来称呼西方的高等学校,林乐知(Young J.Allen,1836~1907)找人翻译的《文学兴国策》就是这么做的。
“大书院时代”的结束
1“大学堂”取代“大书院”
“大书院时代”的衰落现在看来非常突然,几乎全无征兆。1895年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建立,又称为天津大学堂,第二年便正式改名为北洋大学堂。大书院时代为中国大学理念的起源作了准备,但是中国的第一所大学,却以“大学堂”命名。其中的原委目前尚不清楚,但是意义非常明显:“学堂”长期以来只是教授西方语言和技术的专门学校,只作为“书院”的补充,在甲午战争惨败的刺激下,却突然取代了“书院”的地位,成为中国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新宠。战事平息以后,人们迅速得出结论:自强运动以来形成的以书院为主、学堂为辅的教育格局须为失败负责。书院的存废立刻成为问题,激进的意见要求改以中学为主的书院为以西学为主的学堂,温和的意见要求书院的课程做出重大改革,越来越多兼容西学,其实就是以学堂为标准改造书院。从另一个角度说,书院和学堂的升降,也反映了中学和西学、传统士绅和新学知识分子之间地位的转换。到1898年,康有为(1858~1927)上书光绪皇帝,建议改全国书院为学堂,迅即获得首肯。戊戌政变以后虽然有短期的反复,但是改书院为学堂还是变成了清朝的国策。“书院”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何况“大书院”呢?
当中国人已经在“书院”和“学堂”之间做了选择,在华传教士很快便顺应形势做出改变。《万国公报》是传教士鼓吹教育改革的重要基地,所刊登文章大多是关于“对整个教育系统进行全面改革的宏观决策”。梳理有关文献,可以发现,19世纪80年代以来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曾用不同的译法称呼university,包括“总学”“普书院”“大书院”,但是到1896~1897年,李佳白(Gibert Reid,1857~1927)建议中国朝廷建立“大学堂”或“总学堂”,而不再提“大书院”或“普书院”了。其中“大学堂”是university的通称,尤其指今天所谓综合大学,而“总学堂”则是特指设立于首都的最高学府,还是有现代化的太学的意思。李佳白明确指出他的建议是响应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的上谕,并且受到盛宣怀兴办北洋“大学堂”的鼓舞。
“大学堂”取代“大书院”带来最重要的新意是,大中小三级学校制度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终于得到确立。之前提到,明清之际耶稣会已经将三级学校制度介绍给中国人,而长期以来并未深入人心。一个标志是,在“大书院”时代,目前所见,只有各种关于“大书院”的介绍,却不存在“中书院”和“小书院”的说法,因此也不会强调“大书院”与“中书院”与“小书院”的联系与区别。“大书院”这个说法本身来自省会大书院,后者与一般书院相比资源更多,名声更好,教学内容却并不一定有本质的差别。但是,当“大学堂”成为university的标准汉译时,“中学堂”和“小学堂”也几乎同时出现了,分别对应的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大学、中学和小学。
2“大学校”和“大学”取代“大学堂”
然而,几乎在“大学堂”(在官方文献中)代替“大书院”的同时,便开始了从日本引进的“大学校”和“大学”取代“大学堂”的过程。康有为与梁启超流亡到海外时的笔记提到university的时候,都称为“大学”;连清朝派出去考察立宪的载泽和戴鸿慈(1853~1910)都将“大学堂”与“大学”乃至“大学校”并用。盛宣怀1895年、1898年先后宣称以“大学堂”的标准创办北洋中西学堂,仿照法国“国政学堂”(今译巴黎政治学院)创办“南洋公学”,在1902年的两封奏折中却把university称为“大学校”。
这里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全文检索数据库(1830~1930)做一个简单统计,考察1895年以后数年各种university汉译的升降起伏。需要指出的是,用“大学”作为关键词搜索数据库,可以发现大量不属于用“大学”翻译university的例子,比如“大学士”“大学堂”“大学院”“大学馆”等包含“大学”两字的复合词,以及儒家经典《大学》《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等,在统计时均已删去。具体统计结果可参见文后附表。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大学校”的使用率并不高,不仅远远比不上“大书院”、“大学堂”和“大学”,甚至与“太学”比也有若干距离。其中原因,下文会做一些解释。
我们暂时先把注意力放在“大学堂”和“大学”何时在实际运用中取代“大书院”的优势地位上。1895年前后,各种对西方university的介绍纷纷涌现,所以几个主要汉译的使用频率都增加了。到1896年,“大书院”仍居压倒性的第一位,在数据库中累计出现163次;随后“太学”累计76次;“大学”累计64次;“大学堂”只有18次。到1897年,“大书院”增加到197次;“大学”上升为第2位,累计120次;“太学”89次,“大学堂”61次。“大学”超过“太学”,不能不说是甲午战争后果的体现,向战胜者学习,学习他们的教育制度,也学习他们对西方词汇的翻译,逐渐成为风气。不过,至此“大书院”相比“大学堂”仍处于绝对优势。到1898年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改书院为学堂的建议,双方统计数据终于接近:“大书院”累计246次,而“大学堂”则猛增到累计200次(“大学”累计183次,略降为第三位)。到1902年,“大书院”累计336次,“大学堂”累计332次,“大学”则以331次紧随其后,呈现三足鼎立之势。直到1903年,随着庚子新政,书院改学堂运动展开,“大学堂”才在累计总数上首次超过“大书院”,前者419次,后者356次,不过,“大学”的升幅更大,以累计461次占据榜首。很明显,“大学堂”的突然崛起得益于官方政策的倾斜,而“大学”的持续上升则源于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对日本高等教育模式的认可。
到民国初期,政府正式规定所有“学堂”改称“学校”,“大学堂”便短暂地改为“大学校”,再改为“大学”。比如,北洋大学堂就在1912年1月改名为北洋大学校,1913年再改成国立北洋大学;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后来又正名为北京大学。以下分别考察“大学”及“大学校”的由来。
“大学”在中国传统文献里,有三层含义:首先,是指周朝的天子之学,后来发展为太学或国子监等,是设立在首都的最高学府,具有很强的儒家官学性质。其次,是指四书之一的《大学》。第三,是由《大学》所揭橥的君子之学,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与“小学”相对的学问和教育的高级阶段。
一般高等教育史的著作认为日本把university翻成“大学”是直接从中国古籍中“大学”的第一层含义即太学而来。我查了一些资料,似乎不是这样。直接来源应该是日本中古时期相当于中国太学的大学寮,略称为大学,另外大学寮别曹中的劝学院也俗称大学,所以日本人用大学译university有自身的传统,中国人把它拿过来却不知道。从语言的发展看,对最高学府的称呼既然从大学发展为太学,没有特别理由似乎也不会再变回去。其实,德川幕府任命的总管学术的官职名为“大学头”。头即是长官的意思。这个职务一直由林氏一族世袭。明治前后日本有昌平学校,这是东京大学的前身,负责的也是大学头。“大学”一词自然被用来指称最高一级的学府,而将“大学”与university联系起来是源自明治19年(1886)的帝国大学令。
至于“大学校”的来源则有不同的看法。沈国威先生指出东京大学发展史上,曾经有“大学南校”“大学东校”的说法,从这些名称中可以知道,这里的“大学”还是“太学”的意思,“大学南校”即最高学府的南校,校仅指场所。“大学校”也就是大学的校,后来成为专有名词,在明治19年以后有些单位也没有改正。现在日本有国防大学校、航海大学校等。他认为“大学堂”也是从“大学的堂”演变而来。依据这个说法,“大学校”和“大学堂”指的都是提供“大学”(最高水平)教育的场所,所以都是从“大学”发展出来的词汇。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笔者再提供另一个思路:“学堂”在古文里就有连用,前文指出,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专指教授西方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的专门学校,所以在“大学堂”(以及“总学堂”)之前“学堂”已经固定化,“大学堂”看来除了大学的堂,还可以理解为大的或高级的学堂。至于“大学校”,我查了东京大学的历史,在大学校这个说法产生之前,昌平坂学问所已经改成昌平学校,还有开成学校、医学校等,似乎学校也已经固定为school的意思。学校这个词源自经典中的庠序学校,学和校是两个同义词的连用,用来作为school,尤其是官学的泛称由来已久,但是在中文中很少指具体某一间school的名称,令人怀疑是在日文中首先有这个用法。所以我揣测,虽然并不如“大学堂”肯定,“大学校”也可以理解为大的学校、高级的学校,而不一定是大学的校。所谓大的学校也许是指原来三间学校,即昌平学校、开成学校和医学校合并为一家,因此便“大”(不仅是空间大,而且更高级,更综合)了起来,也许是强调这一学校享有超出其他的特殊地位。因此,在日文中“大学校”和“大学”可能来源不同。但是,不得不承认,至少在中文的语境中“大学堂”乃至“大学校”的确令人联想到实行“大学”教育的场所,而与前述“大学”的三重含义联系起来。从这个思路出发,“大学”作为对这一场所的更简便的称呼最终取代“大学堂”和“大学校”并不难于理解。
无论如何,以“大学”或者“大学校”来翻译university都是日本传统或者近代日本学校沿革的产物。如果说“大学堂”取代“大书院”意味着自强运动以来兴办新式学校的传统从支流上升为主流,书院的理想遭到抛弃,那么“大学”或者“大学校”取代“大学堂”便意味着中国人对自己理想和经验的进一步否定。这样,不仅在大书院的框架下中国人对西方以及日本多种大学模式的观察和思考被隐没,从自强运动到晚清新政中国人仿造西方或日本创办新式教育的努力也遭到唾弃。当然,这两个术语毕竟不是一回事,“大学校”对中国人来讲完全是陌生的,因此很快便不再使用。而“大学”则因为能使人联想到太学(日本人用“大学”来翻译university的时候,的确有很强的“太学”意识,后来所谓“帝国大学”则更像是“太学”一词的现代化)和高深学术、高层次教育而受到欢迎,成为university的标准译法。接受了这个翻译,便意味着中国人理解、观察、移植西方university的最主要的本土资源发生了转移,即从书院转为太学,从私学转为官学。
转移的一个标志是整个“大书院时代”被忘却了。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一种中国高等教育史或大学史的著作注意到中国人曾经普遍使用“大书院”作为university等西方高等学府的译名,曾经以书院为参照观察西方的高等教育,并借助西方的经验重新反思书院的理想。在追述中国大学的起源时,比较实际的会认为是1862年创办的同文馆,比较怀旧的则一直上溯到周代以来的太学、国子监等。个别名校的自我定位也是如此,北京大学以太学传统的继承者自居,这是北大招生广告上,一度自称“上承太学正统,下立新学祖庭”的深层次原因。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也认为自己是继承了明朝的太学。唯一的例外也许是湖南大学,在主要大学中只有这一所将自己的起源与书院联系在一起。
总体而言,尽管书院曾经长期作为中国人观察西方大学的参照物,在近代学制确立的时候,书院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和私人讲学传统却是作为对立面存在而不被看作是需要继承和吸收的资源。从物质基础乃至精神渊源上,近代中国大学制度与太学的关系可能都比书院更深。无论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还是湖南大学,都是国立大学,靠国家支持,由国家统一管理。私立大学(教会大学除外)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个别教育家和实业家所能动员的力量,再也不能与国家竞争,这是私立大学中比较有名的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后来都改为国立的内在原因。
另一方面,当university和“大学”建立起固定联系的时候,除了太学中国人往往还会想到“四书”之一的《大学》,选取其中词句描绘他们对高等学府的认识:不少大学的校训都是从中得到灵感,比如香港大学的“明德格物”和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止于至善”。这样,传统的教育理想至少在现代大学里面还能够保留一点痕迹。
结 论
近代对university/college的翻译,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从晚清传教士再次进入中国到1895年,“大书院”在各方面均占据主导地位,这个翻译将西式高等学府和中国书院自唐宋以来千年的传统联系起来。这个阶段,我称为“大书院”时代,中国人基本上是从本国的学校制度,尤其是书院的现实和理想来观察西方的大学,虽然注意取长补短,却没有完全失去自信心。
第二个阶段,从1895到1911年,“大学堂”逐渐取代“大书院”成为官方认可的标准翻译。1895年以后,甲午战争惨败动摇了中国精英对书院教育的信心,“大书院”这个译法因而越来越受到挑战,有力竞争者是“太学”和“大学堂”。“太学”有比“大书院”更久远的渊源,作为翻译强调的是国家与高等教育的互相依靠。“大学堂”则是有意继承自强/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官方培养西学专门人才的新传统。“大学堂”的取胜,不仅是由于“太学”这个翻译的内在缺陷(太学是首都的最高学府,而一个国家university往往不只一所,也不一定位于首都),更重要的是学堂在人们的心目中与西学、新学联系在一起,而太学则不可避免地与传统相连。“大学堂”这个翻译与自强运动相连,代表了王朝自我更新、与时俱进的期许。然而,“大学堂”在体制中取代“大书院”的同时,从日本而来的“大学”和“大学校”也开始了在民间取代“大学堂”的过程。
民国以后是第三个阶段,“大学”迅速确定成为university的标准翻译。1912年1月,临时政府教育部迫不及待地改“学堂”为“学校”,因此“大学堂”便一度改为“大学校”。但是,原定的《大学校令》却在1912年9月正式颁布之前改为《大学令》,主要学校的名称也从“大学校”改为“大学”。不接受“大学堂”这个称呼,反映了革命者要否定晚清王朝改革(从自强运动到新政)的合法性。在他们看来,学堂教授的西学只是皮毛,而不是真学问,学堂宣称要保留的中学是要维护旧王朝而与共和制度格格不入。用“大学校”替代“大学堂”则表现了主事者对日本模式的推崇。不过,用“大学”替代“大学校”,我觉得倒是反映了不同的思路:“大学校”完全是日本历史文化的产物,在中国缺少根基,“大学”却可与本国悠久的经典传统联系起来。一个外来的观念如果要在本国的土壤里生根,似乎都要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对应物。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和日本多种大学模式均有观察和体验,而主要注意力是放在英美模式上,他们往往重视书院与英美大学的比较,有些人甚至认为英美大学与当时的书院相比更好地体现了书院的教育理想。甲午战败之后,日本模式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本土的理想和本土的经验,包括对日本以外的模式的观察,包括自强运动以来创办新式学堂的努力,先后被否定。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激进的自我否定的时代,原本多种的可能、多样的选择,变得趋于单一。但是,最后确定的标准翻译“大学”,虽然直接来源是日本,却在本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含义,在全盘西化、日化的时代,承载着民族的教育理想。
附表:1896~903年主要university汉译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全文检索数据库中的累计出现次数
年份 大书院 大学 太学 大学堂 大学校 1896 163 64 76 18 15 1897 197 120 89 61 22 1898 246 183 119 200 34 1899 276 215 121 224 37 1900 279 219 122 231 38 1901 315 264 148 256 49 1902 336 331 162 332 66 1903 356 461 177 419 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