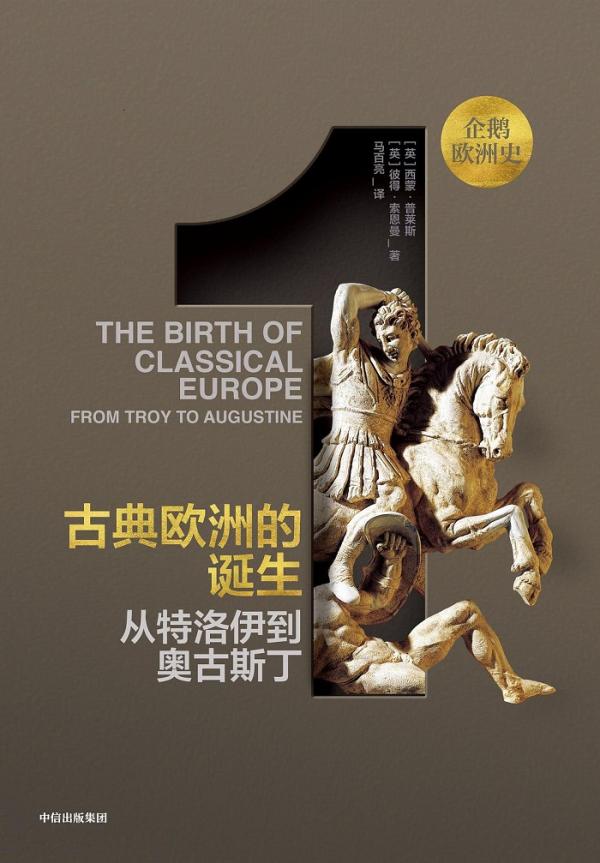欧洲的“古典时代”(classical antiquity,一般是指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六世纪)在汉语阅读圈中常常被赋予两种意义。在第一种意义的情境下,人们根据近代建构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框架,认为希腊的光荣和罗马的伟大意味着特定民族的天然优越性;第二种意义恰恰相反,梁启超“四大文明古国”理论的信徒们强调:古希腊—罗马文明是比古中国年轻太多的次生文明,甚至不过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学者创造的“伪史”。这两种意义立场全然相反,但其实都是现代人出于各自的私心和偏见给古典世界蒙上的阴影。中信出版社近期引进的
《企鹅欧洲史·古典欧洲的诞生》
(西蒙·普莱斯、彼得·索恩曼合著),是对这两重阴影的同时廓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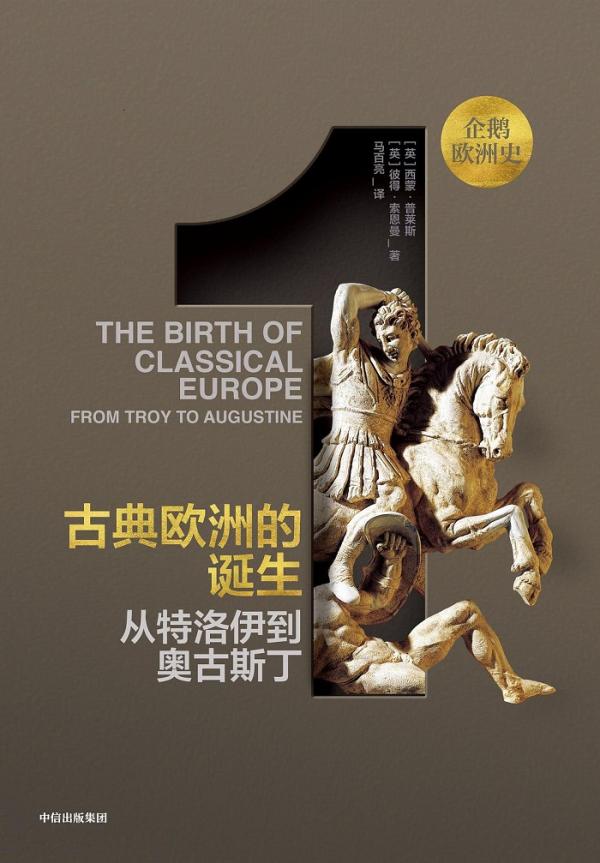
在这两种阴影中,希腊罗马伪史说虽说近年来在中国风生水起,其实不过是弱势文化少部分人的圈内自嗨。某些以古典时代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张目的思潮,自一战前到法西斯,在西方历史中盘根错节已久,为害甚烈,这才是作者们眼中值得认真对付的对手——其实说到底,希腊罗马伪史说也不过是这些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潮在东土的变种而已。
作者们显然是有意识地以这些思潮为假想敌,因此在一部以古典时代为主题的历史著作中,先后提及现代德国纳粹党对斯巴达意识形态的利用 (第四章)和二十世纪大希腊主义造成的悲剧 (第五章)。在前一个例子中,希特勒赞美斯巴达人“将有生理缺陷的后代遗弃,从而保留他们纯粹而基本的种族特征”的做法,并且摭拾古典传统中的只言片语,鼓动德国人为了征服其他民族奉献他们的生命;在后一个例子中,对古希腊的辉煌的追忆,虽然也曾鼓舞现代希腊人和不朽的拜伦勋爵为希腊民族从奥斯曼帝国的缰绳中解放而奋斗,但同样也导致了现代希腊人以“伟大理想”(megalēidea)为名,在一战后展开盲目血腥的对外扩张战争,其结果是百万希腊人流离失所,被赶出了他们时代居住三千五百年的小亚细亚半岛。
古典欧洲和现代人想象的民族国家世界不同,在普莱斯和索恩曼的笔下,它具备更强的国际性质。不同的民族、共同体、语言和方言同时并存,互相借鉴交流,为古典传统作出贡献。爱琴海的冶铁技术,可能是公元前11世纪和公元前10世纪从塞浦路斯传来的。18世纪的英国显贵们竞相追逐,对英国早期新古典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伊特鲁里亚”陶瓶,大多源于雅典,并且刻有希腊文。在公元前8世纪到前7世纪,在建设地中海商业贸易网络方面,腓尼基人的贡献至少不弱于希腊人。关于罗马城建立者之一的罗慕路斯的一则故事告诉我们,罗慕路斯建立了罗马的庇护所,政治难民和奴隶们都能够在此寻求庇护,这也成了罗马的显著特征(这和古罗马独特的授予被释放的奴隶以公民权的实践相对应)。即使是到了帝国时代,罗马也是一个宗教多元化的世界,“帝国的行省内部地方崇拜之多令人咋舌,其中大部分受到罗马统治者的宽容” (第八章)。
更重要的是,早期古典时代的人们并没有现代人那样强大的民族和国家观念。斯巴达人主要以两种方式来定义他们的集体认同,其中前一种即斯巴达身份,更多基于对宗教、地域和英雄人物的认同——“他们可以选择强调他们特殊的斯巴达身份,斯巴达人是一个植根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特定区域的共同体。作为斯巴达的居民,他们是英雄时代珀罗普斯王朝的继承者,向当地参与特洛伊战争的英雄如墨涅拉俄斯和俄瑞斯忒斯献祭。”第二种认同即多利安人身份接近种族认同,但并不伴有作为希腊人的意识。荷马史诗也没有多少内容展示“希腊人”这一确定的种族认同。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古希腊文明并没有产生较广泛的希腊自我意识,而到公元前6世纪之后,这种“泛希腊”认同主要源于国际性的竞技比赛——我们非常熟悉的奥林匹克竞赛,也源出于此。 (第三章)总而言之:古希腊文明的真相更接近于一个国际文明体系,而不是贴着种族或是地域标签的自我封闭的文明。
作者们同时非常适当地评价了古典欧洲从近东和埃及那里受到的积极影响。除了前文提到的几种,这个列表还可以包括:希腊字母表(大约公元前8世纪自腓尼基传入)、人形雕像(公元前7世纪中叶开始出现在希腊神庙的大量男性雕像“kouroi”,以其假发般的发型、正面的形态,以及阔步的站姿,显然是对同时期埃及石雕人像的直接模仿),甚至还有我们熟悉的希腊神话。例如,长大后的宙斯击败生性残暴、吞噬自己子女的父亲克洛诺斯的故事,源于赫西俄德的《神谱》(成书于公元前700年前后)。但“这个故事中的几乎每一个情节都可以(在赫梯人公元前13世纪的神话《库马比之歌》中)找到密切的对应” (第三章)。正如柏拉图指出的那样,“每当希腊人向非希腊人借鉴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总是会把它做得更加完美”。根源在古埃及的希腊人体雕塑在艺术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它的前辈——学习借鉴不足为耻,只要能后出转精,就是文明活力充沛的证据。在这个问题上,古希腊人足以让仍然絮叨着“日本文明只会学习效仿,不会原创,算不得本事”的部分现代国人感到脸红。
但作者们也并没有为了凸显文化多元的政治正确,矫枉过正地扭转历史事实,形成所谓的“逆向歧视”。作者们的写作重心非常明确:“我们探讨的焦点是地中海盆地北部的古老民族,即希腊人和罗马人。对此,我们无须为偏向性道歉,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推动古典时期发展的主要是爱琴海、巴尔干南部和意大利半岛的民族” (本书《前言》)。作者们同样直率地指出了流行历史读物《黑色雅典娜》中部分观点和依据的粗疏。《黑色雅典娜》声称埃及是希腊文明的根源,文风和举证不无情绪化之处,但这类著作往往得到汉语圈选择性的引入和追捧。
考虑到汉语圈选择性引入的问题,阅读《古典欧洲的诞生》,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类似大部分关于古典时代的西方著作,这部书最初面向的是西方读者。作者们多少已经默认了:这本书的读者们已经对古典时代,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们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但这个条件在中国不一定成立。例如,作者们在第三章中提到,将其他竞争对手排除在外的“僭主政治”(tyranny)的负面含义,是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才开始产生的,“古人认为僭主政治标志着朝向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体的一大进步,这是有定道理的,因为僭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更加广泛的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和支持”。这个表述无疑大致正确,但要正确理解这个表述,还需要读者们对在此之后古希腊传统中僭主政治的负面含义有所了解。凡是阅读过柏拉图《理想国》或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人们都知道,僭主制度是绝对平等导致的绝对专制,因此广泛受到希腊古典时代思想家们的拒斥(原文“tyranny marked a step towards true democratic government”其实也没有“进步”的含义——因为古希腊思想家们往往并不赞成绝对民主的制度)。
在充分了解了作者们的话语语境之后,《古典欧洲的诞生》显然有助于中国读者大大扩展自身的文明视野。即使对古典西方了解不多的读者,这部书也是相当具备可读性的世界史入门资料。说到这里,不免补问一句:为什么作为现代东亚人的我们,要去了解古典时代的欧洲历史?我不禁联想到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在他主编的“哈佛中国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这部书也由中信引进)中引述的朱维铮教授的精巧比喻:
“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
朱维铮用这个比喻说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必要性。但要了解东亚文明这个房间所处的位置,其实还需要了解世界文明的坐标系。因此中国读者对世界历史的了解,可能比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更加重要。我们有必要相信:在流俗理解的成王败寇的帝王成功学之外,在现代思潮建构的民族国家的生死竞争之外,文明还有其他的内涵和可能性。
从这个角度来讲,作者们在本书中对公元前1900年的克诺索斯遗址、公元前1750年的线形文字B的着力介绍(尽管这些努力多少过度,占据了太多篇幅),可以让许多人对“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天下第一”的说法产生怀疑(现有甲骨文一般可以推至武丁时代即公元前1200年);而作者们在本书中揭示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多元性,则可以让我们对现代以来源于西方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产生反思。为什么作为现代东亚人的我们,要去了解古典时代的欧洲历史?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东亚人,所以我们更有了解欧洲史的必要;正因为我们是现代人,所以更有了解古典时代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