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美)塞思·勒若
从一开始,孩子们就阅读带插画的书。在一片来自拜占庭的埃及、描写了赫拉克勒斯功绩的莎草纸残片上,就完好无损地画着这位英雄与狮子的画面。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早期的插图文本流传了下来。中世纪出现的泰伦提乌斯戏剧手抄本(他的戏剧是古典时代和中世纪学校的主要教材之一),也带有角色和场景图。《诗篇》作为千年来基督教儿童学习阅读的诗集,常常以精心修饰的首字母为装饰,描绘出诗人大卫王及其诗歌的主题。还有两份16世纪初,可能用于贵族儿童教育的英文手抄本,它们以丰富的色彩,极为生动地呈现了野兽与花朵的形象,其水准超越了先前中世纪动物寓言和药草书中插图的水准,达到了教学艺术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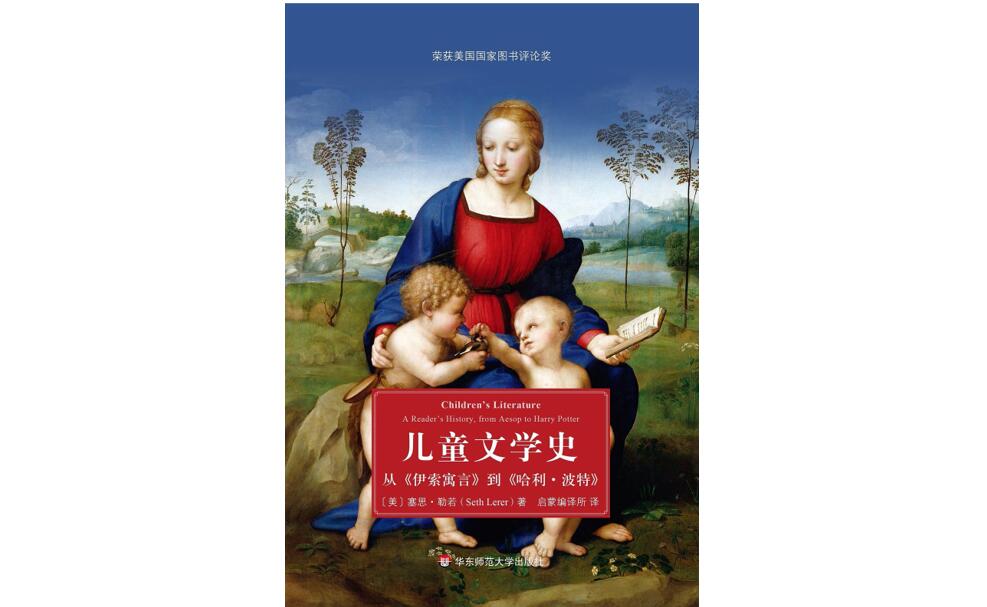
本文出处:《儿童文学史:从〈伊索寓言〉到〈哈利·波特〉》,(美)塞思·勒若著,启蒙编译所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2009年获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2010年获杜鲁门·卡波特文学批评奖。
作为欧洲最早出版的书之一,《伊索寓言》常配以精致的卷首插画,画中是伊索和故事中的各种动物。在早期清教徒的出版物中,包括詹姆斯·詹韦的《儿童的榜样》《新英格兰初级读本》和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里面都有许多插画。(前面提过,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少年时期曾见过一本“附有铜版插图”的《天路历程》,并对其大加赞扬。)约翰·洛克明确表示,带插画的教科书能使教学达到最佳效果,并将这条原则运用到了他的插图版《伊索寓言》中。的确,对于许多现代读者来说,“儿童文学”,尤其是“童书”,本身便意味着图画重于文字。童书的历史,往往也被认为是插画的历史。
《伊索寓言》,1489年,博洛尼亚大学图书馆
近年来对儿童阅读习惯的研究,极好地验证了图画对于想象力的作用。对埃伦·汉德勒·斯皮茨(Ellen Handler Spitz)而言,学习阅读与学习观察密不可分。文字与图像,都是理解事物的元素。20世纪的经典绘本“通过运用图像与文字,牢固地扎根于记忆的博物馆,极大地丰富了儿童的内心世界”。而对于《诺顿儿童文学选集》的编辑来说,书的外观与内容同等重要。此书不仅复制了原书装饰文本用的黑白插画,还设置了整整一章,收录从霍夫曼的《蓬蓬头彼得》到谢斯卡的《臭起司小子》等各类故事,并全部以全彩光面印制。插画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图书行业的认可。其中,尤以1938年美国图书馆协会设立的凯迪克奖为最,它颁发给“美国最出色的儿童图画书”。借用2007年凯迪克奖为大卫·威斯纳(David Wiesner)的《海底的秘密》所写的颁奖词,“长久以来,人们一直通过图像来叙说故事”。
我个人的儿童文学阅读史,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关于小说和诗歌的故事。故事通过文字唤醒想象中的世界,但它也强调文学想象的巨大力量,用这种力量去创造冒险、平和、接纳、激情、成长与理解的空间。可以看到,我先前提到的那些最生动的故事,是不需要插画的。我们难道不能自己想象出《鲁滨孙漂流记》中星期五的脸庞,《秘密花园》中美丽的风景,或《金银岛》中那条神秘的船只吗?单凭文字便足以创造想象。然而,某些书与插画一道成为儿童文学的经典,如今那些插画已与它们密不可分。我们如何想象没有约翰·坦尼尔(John Tenniel)标志性插画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有些书虽然一开始并未配上插画,但是最终与后加的插画产生了紧密的联系。比如,假设 《柳林风声》没有欧内斯特·H. 谢泼德的素描,或没有亚瑟·拉克姆色彩明亮的水彩画,我们会是什么感觉?(尽管两者都是在该书出版几十年后创作的。)我们如何想象我们最初读到的“儿童版”名著,比如荷马的《奥德赛》、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或是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没有插画的样子?
Boston: Lothrop Publishing Company, 1898. John Tenniel.
儿童文学的历史,不仅是文字与图像的历史,也是工艺品的历史。书本被当作贵重的物品,因制作精巧而被收藏,与人们相伴相依,得到细心呵护。因此,童书历史研究与书籍史完美契合,后者被法国学者称为“书本的历史”(l’histoire du livre)。书籍史兴起于20世纪末,整合了目录学、图书馆学、古文书学及社会学的传统,以求恢复图书阅读的物质文化。一本书的外貌、触感,甚至气味,都与它的内容一样会影响阅读体验。书的内涵包括它的介质。而对于儿童文学研究来说,一本书的内涵不仅在于插画,还包括孩子所能理解的所有内容。
图画装饰童书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它们往往以木版画或金属蚀刻版画的方式呈现。约翰·纽伯瑞的《给小先生与小女士的漂亮的图画书》,也许是最早的插画重于文字的书之一。这一本,以及纽伯瑞出版的其他书,都非常注意让图画与文字相符,而其他许多早期的出版商却并未如此细心。很多情况下,童书的插画是用印厂四处堆放的木版画拼凑起来的,或是借用了其他作品中的插画。有关自然科学或是字母学习的书更是如此,其中的图画往往来自早先的书。(事实上,即使是纽伯瑞的那本图画书,当中的图片也有部分源于爱德华·托普塞尔的《四足野兽史》中的动物插画。《四足野兽史》出版于1608年,在后来的一个世纪中,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动物图书之一。)在德国,约翰·夸美纽斯的《世界图解》(1658)影响了之后两个世纪的教材编写,也直接催生了F. J. 柏图尔赫(F. J. Bertuch)的24卷百科全书《儿童图画书》。
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是首批为童书提供高质量的插画,而非简单木版画的英国出版商之一。1805年,他出版的萨拉·凯瑟琳·马丁的《哈伯德大妈和她的狗的滑稽冒险》便使用了铜版画。在之后出版的书中,这样的铜版插画在印制后会由艺术家(甚至是读者自己)手动填色。哈里斯的职业生涯始于纽伯瑞的出版社,至1801年,他开始自己经营这家公司。很快,他的出版理念便与前辈们秉持的洛克式教育理念分道扬镳,哈里斯的书大多仅供娱乐。由于色彩过于艳丽,他的书也常常受到指责。然而在19世纪初,他出版的图书依然受到极大欢迎,其生动的插画也成了后世插画的标准。
至19世纪中期,新的平版印刷技术使插画在儿童图书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更重要的是,它们重新定义了童书,使之从根本上变为带插图的书籍。彩色石印术最早出现于19世纪30年代后期,该技术将同一幅画的不同颜色用不同的石板相继印出来。德国的《蓬蓬头彼得》是最早使用彩色石印术的插画童书之一(1845年),而在英国插画师沃尔特·克兰(Walter Crane)手中,用这项技术印刷的一本本书,更是迸发出了强大的美学力量。
德文版《蓬蓬头彼得》,1845,Rütten & Loening出版社
克兰是早期伟大的童书插画师之一,其线条之生动、形象之奇特,以及近乎拉斐尔前派之精准,一直为学者与收藏家称道。与同时期的许多画家一样,他也受到了丁尼生的中世纪主义、约翰罗斯金和但丁·加百利·罗赛蒂的美学观念,以及当时流行的日本木版画的影响。作为中世纪研究者,我被他画中的某些特质深深吸引。比如,在1874年的《青蛙王子》中,一幅表现青蛙请求进入城堡的插画,便具备丰富的图像要素。这幅画视角简明,棋盘格的地板向后延伸到深处的消失点。它在艺术技巧上采用了象征手法,其中的盆栽柑橘树让人想到中世纪有关宫廷花园的画作中常见的伊甸园的果树。画面大部分由正方形、矩形、直线和直角组成,然而女子衣褶上流畅的曲线和斜线,打破了这种规则。在这幅画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只祈求进入城堡的青蛙,更是我们自己我们站在想象的门外,期望能够进入其中我们所在的这个由直线和简单透视掌管的世界,在想象的守卫面前弯下了腰。流动的裙摆与发丝,召唤人进入一个没有直角的奇妙世界。
克兰的画与同时代的凯特·格林纳威(Kate Greenaway)、伦道夫·凯迪克的作品一道,构成了许多现代读者对于儿童图书插画的印象。相对于克兰而言,格林纳威的作品更注重对家庭内部的描摹。她的作品往往勾勒家庭内部的景象,如厨房、卧室和客厅。《一个苹果派》中有一系列极为出彩的插画。在这些插画中,格林纳威运用字母读本的传统手法,描绘了理想中的家庭生活的模样。这是一个连衣裙与马裤的世界,它不同于19世纪晚期英国的社会面貌,而是格林纳威幻想中更为古老,甚至有可能是18世纪末的理想世界。她的脑海中仿佛存在着另一个萨拉·菲尔丁或萨拉·特里默在她的系列画作中,苹果派仿佛是一种近在咫尺,却又可望而不可即的愿景。或许,它象征着童年孩子们争抢它,渴望它,窥视它,歌颂它最终,六姐妹(以U、V、W、X、Y、Z这个不明所以的序列)每个人都品尝了“一大块苹果派”,满足地“进入了梦乡”。格林纳威的书,正如睡前的苹果派般贴心、香甜,给我们带来一大块想象的童年。
伦道夫·凯迪克,《The Babes in the Wood 》
自1955年始,英国便设立了格林纳威奖,用以褒奖杰出的童书插画作品。美国也有相应的奖项,就是著名的凯迪克奖。与克兰和格林纳威一样,凯迪克一直是童书插画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他凭借自己学院派水彩画的训练与经验(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展览过他的水彩画),成为连接大众品位与出版商需求之间的桥梁。他最为著名的作品是由爱德蒙·埃文斯印制、为劳特里奇公司所做的插画书,这些插画同格林纳威的画作相仿,幻想了一幅18世纪末19世纪初理想化了的过往英国。他的《这是杰克造的房子》出版于1878年,其中所呈现的生动的线条和色彩(尤其是对动物的刻画),影响了许多作者兼插画家,包括毕翠克丝·波特和莫里斯·桑达克。书中的猫(以写生及猫科动物的解剖研究为基础画的)蹲伏在掉落的苹果旁,唤起了人们对早期初级读本中伊甸园的印象,因为这只小动物清除了老鼠,使我们的圣地免遭侵扰。字母A一直是苹果的象征。
凯迪克的卓越,不仅体现在他的毕生作品本身,也体现在他在40岁英年早逝的情况下,依然留下了数量庞大的作品;体现在他的离世引起了公众与艺术圈极为强烈的反应,这种影响在儿童文学界的其他人身上恐怕很难再见到。从皇家艺术学院的校长莱顿勋爵,到《特瑞尔比》(19世纪末最畅销的书之一)的作者乔治·杜·莫里耶(George Du Maurier),几乎所有为英式品位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都对凯迪克赞誉有加。从他们的言辞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非常关注凯迪克作品那种亮丽的气质。他的画作包含着优雅、妩媚、美丽、诙谐、独特、高贵、愉悦和天真这些作品朴素、洁净、耀眼。人们在评论凯迪克的作品时使用了这些优美的词汇,他的人生仿佛从未沾染丁点污秽。奥斯汀多布森在1887年(凯迪克逝世的第二年)写道:“[凯迪克的作品]没有丝毫病态的矫揉造作,亦毫无苍白的无病呻吟它们真诚地表达出了刚强、乐观的本性。”
关于童书中文本与插图的关系,我们从这些评论背后看到了一个更深刻、更复杂的问题。插画是否能够真实地反映文字的意义呢?换句话说,通过线条和形式,它们是否真切地展示了幻想故事与诗歌中的世界?在凯迪克一本插画书的题词中,小说家G. K. 切斯特顿写道:“不要相信任何/彩色画不会告诉你的事。”这句话后来被广泛地用作论据,好似插画是为了创造可信的世界而存在,似乎插画家的美德在于真实感。
插画家凯迪克与凯迪克奖奖章。
20世纪以来,童书插画的创作冲动,有一部分已变成挑战迷人与耀眼的真实。实际上,它们挑战的是插画,只能反映现实这一观念。莫里斯·桑达克等人画中的智慧与讽刺,部分在于他们创造的视觉描述破坏了我们对于插画模仿现实的期待。我已提到过,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在《老水手波特》中展示的力量,某种程度上告诉我们,在画中寻找自己,往往是抽象的,而非实体的。艾瑞·卡尔(Eric Carle)的剪贴画让人想起昆虫世界的分节现象(在《好饿的毛毛虫》里表现得尤其精彩)也昭示了插画作品本身的分节本质。在莱恩·史密斯为约翰·谢斯卡的《臭起司小子爆笑故事大集合》(1992)所创作的插画中,可以看到一种现代(甚至后现代)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的意味。正如《诺顿儿童文学选集》所言,这是一种带有“刻意讽刺”的“拼贴手法”,它还“呈现出互文技巧”,使人物“试图冲破书本的束缚”。充满讽刺意味的距离感而非激起情感的模仿,成了近期儿童图画书的标志。然而,纵观儿童图书的出版史,人物冲破书本束缚的形式不止这一种。
立体书,也许是其中最显著的一种形式。其实书几乎从一开始就跳出了纸面。21在中世纪的手抄本和一些早期印制品中,人们有时会附上一些可以转动的圆片或折叠的几何图形,来解释关于数学、解剖学或神秘事物的知识。18世纪后期,出版商罗伯特·塞耶(Robert Sayer)创造了他所谓的“变形书”,这种书事实上是一张被折成四份的纸。在阅读的过程中,操纵其中的合页、切页以及翻盖,就可以呈现出被隐藏的图像。翻盖出现于19世纪早期,到19世纪中叶的时候,又出现了“可动书”,每翻一页这些会动的书,就会有图画跳出来。
收藏家与目录学家,都极其喜爱这些立体书。它们每一本都是珍品,每一本都是对制作工艺的最好印证。我也很喜欢,尤其是有高塔巨龙跳出纸面的那些。立体书最奇妙的地方在于,它们本身就是自己所想表达的事物。它们在讲述故事,它们也是故事本身。它们让阅读行为成了人与书的相互操纵,但又让孩子们始终记得他们是在阅读一本书,同时也使他们牢记生活中充满虚幻自己眼中真实的物品可能只是纸做的贴画和彩板,或是用金属片联动的纸条。阅读一本立体书,仿佛是骑马穿过西部电影的场景——只有正面而没有背面,或是穿过那个“波将金村”——为了取悦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而建造的虚假村庄。
罗伯特·塞耶设计的早期“变形书”
立体书具有美学意义,也具有社会学及政治学的教育意义,因此,它们中最富想象力的作品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欧,也就不让人意外了。在捷克的阿提亚公司的支持下,艺术家沃伊捷赫·库巴什塔(Voitech Kubasta)创作了许多极其形象生动的可动书。 他用出色的色彩描绘了许多遥远的地方: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19世纪的印度、诺亚方舟,甚至外太空。库巴什塔创作出的小小探险家们,比如蒂普、托普、莫科和科科,仿佛可以运用任一种工具去到任何地方。通过阿提亚与班克罗夫特英国分公司的安排,这些书进入英语市场,并在西方赢得了大批读者。但它们所传达的,不仅仅是虚幻的故事,更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东欧人民对脱离严格的计划经济的渴望。在那个时期,甚至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过后, 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水平在东欧都保持在上等层次——当然,他们的评判标准是拥有摩托车和电视的数量。然而,遭受压迫的记忆和对现实的失望没有消失。在赫鲁晓夫发表了著名的“去斯大林化”演讲之后,1956年4月,捷克作家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Jaroslav Siefert)在作家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说道:“在这里,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别人说,作家必须说出真相。这说明近年来,人们并没有书写真相……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噩梦已经被驱除了。”
儿童文学,一直是驱除噩梦的旗手。库巴什塔热闹的立体书,似乎成了灰暗的后斯大林时期的藏梦之地。它们不仅正好满足当时消费文化的需求,也满足那时现实生活的需求。它们的活泼生动只存在于薄薄的纸张上,一旦深究便只剩下虚假的幻想。有谁会不愿意坐在诺亚方舟上,同那些微笑的小动物,以及可爱欢快的小探险家们待在一起呢?在东欧儿童文学的历史中,尤其是成长于20世纪中叶的布拉格的独特的动画与插画流派中,这些捷克斯洛伐克的立体书也具有重要的地位。许多年代史编写者和参与者都认可,在那个时代,捷克有一种独特的美学嗅觉。其幽默风格,在于展现传统的童话和乡村故事,也在于它调和了对政治制度的批评。用伟大的动画师兹登卡·戴奇(Zdenka Deitch)的话来说,艺术家“总是想方设法(绕过审查),展现当局所忽略的东西”。还有什么形式比这些定格动画更适合展现当局看不到的东西呢? 在战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定格动画渐渐发展为一种高雅艺术。它同立体书极为相似,是让观众通过独立的画面片段塑造一个故事。它将生活分解成不可再分的经验,我们通过线条或分割的画面来阅读它。
20世纪中期的童书,带有强烈的东欧美学风格,痴迷于用色彩和线条与灰暗的城市形成强烈反差,关注匮乏时代里的富足,对以谨慎而又有趣的方式说出真相有需求。扬·平克斯基(Jan Pieńkowski)1938年生于波兰,在战争中与家人颠沛流离,最后在1946年定居英国,他的作品在快乐中隐含着痛苦的回忆。他尖锐的笔触和黑色的剪影,使他的画(如2005年出版的《童话故事》)让人感到奇异的恐惧,仿佛他笔下的人物都在慢慢失去肉体和鲜血。他1980年的作品《鬼屋》(Haunted House,获得了英国的格林纳威奖)取材于他童年时代东欧的监控氛围,富有超现实主义色彩。在故事中,有一只黑猫一直审视着一切,浴室和厨房里总是蹦出怪物,而衣橱里则藏着食尸鬼。
这些东欧的艺术传统,对现代立体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尽管英国和美国的孩子,可能从未有过20世纪中期东欧那种被剥夺了政治与经济自由的体验,但是这些作用超出单纯娱乐的书籍,阐释了最糟糕的噩梦也许会出人意料地开始。好在这些书也教会了孩子们另一点噩梦只是薄薄的纸片,可以由他们自己的力量去唤醒,或结束。
扬·平克斯基的《鬼屋》
童书的装帧是有政治意义的。如果说立体书的外在形式可以为批评20世纪的极权主义服务,那么其他形式的童书也有其表达政治和社会愿望的时刻。除了立体书外,在装帧上最接近让什么东西突出纸板的书,就数伟大的19世纪冒险小说了。这些书的封面是皮质的,并饰以金色字体,其中着以彩色的平面或压花图画。它们承载着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探险与征服之梦。但它们也体现了19世纪艺术品复制的机械化程度。机器装订书页,打印图画,印刷文字并镶金。这些书从根本上来说,已成为机械化的产物。它们将艺术与技术相结合而在很多时候,它们足以作为生产力的奇迹,与书本叙述的奇迹故事相提并论。
这些探险书,常常会细致地描绘用于战争和测量的工具,它们自身也是各种出版工具的产物。举例来说,英国格拉斯哥的布莱基父子有限公司(Blackie and Son)就借着新艺术运动的东风创办了一个综合性的工业设计体系。许多设计师,包括从1893年至1911年逝世一直担任布莱基设计总监的塔温·莫里斯(Talwyn Morris),为该公司打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简明外观。艺术家查尔斯·伦尼·麦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也为布莱基提供设计,他用简约的几何式样代替了过去金光闪闪的、印满压花的封面设计。
在法国,皮埃尔-朱尔·埃策尔的公司为儒勒凡尔纳的书设计了一系列精致的封面,以凸显凡尔纳的“非凡之旅”系列的国际视野。这些封面上印有环球图案以及奇特的动植物图像,成为人们通往未知世界的地图。而在巴黎,勒弗维尔和格林公司(Lefèvre and Guèrin)也用相似的方式,将书中所描述的旅程,反映在复杂的压花封面上。维斯的《瑞士鲁滨孙漂流记》和卡特琳·瓦伊雷(Catherine Woillez)的《鲁滨孙少女》(Robinson des demoiselles)这两本克鲁索式探险小说的诸多再版封面,都展现了书中梦幻般的场景。这些封面都采用了勋章式的圆形形制,标题呈拱形置于图像之上。这些图像使我想起了那些战争大勋章镀金的形象,被植物和动物主题的图案精心环绕图像,饰以圆形或椭圆形边框顶部装饰着鸢尾或花蕾。这些书,已经不只是书了。它们是代表成就的奖章,奖励孩子们在阅读冒险中表现出的英勇。
这些书是珍宝,让书架成了一座宝库。即使是那些远不及这些19世纪图书精致的童书,其封面和插画也使读者爱不释手。书籍成了人们珍惜与渴望的物品,于是识字便为自身带来了奖励。如今网络上有许多这样的书以图片的形式传播,我们或许因此失去了触及这些真实物品的机会。通过网络,一个人也许能在一个下午浏览上百本这样的书,但是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屏幕。这些书籍的厚度被抹平了,它们的颜色不过是一些虚拟数据,它们的重量也远不及纸质书。
作为一名研究书籍和阅读的历史学家,我想重申在本书开头提到的观点书籍能为孩子们提供一种独一无二的陪伴与交流方式。阅读能够调动我们的所有感官。我们常能忆起书页的气味、装订胶的噼啪声,以及封面上的颗粒触感。儿童文学史就是一部感官的历史。在我前面讨论的书籍中,很多书的目的是调动儿童对遥远国度的视觉、嗅觉、听觉、味觉和触觉。爱丽丝进入仙境后收到的最初指令,便是“把我吃掉”和“把我喝了”,我们与克鲁索一起坐在桌子旁,品尝着他岛上的美味食物。安妮·雪莉沉入水底的时候,我们与她一同颤抖。我们还能听到《秘密花园》中迪康吹奏的笛声。所有这些景象,以及其他更多的场景,都通过描写感官印象给予我们教诲。难怪爱德华·李尔和卡尔洛·科洛迪在创作人物形象时,都会特意放大他们的双手、耳朵,尤其是鼻子。李尔笔下的咚有发光的鼻子,科洛迪的匹诺曹拥有被无限放大的感官。最为紧要的,不只是说谎时鼻子会不会变长,而是任何形式的虚构故事,都需要我们的各种感官留心。当我在图书馆找到一本旧书时,潮湿的书页和冷冰冰的皮质封面弥漫着馥郁的麝香味,让我鼻翼大动。在这个意义上,小红帽中的大灰狼,是一种对读者形象较为可怕的变形,我们需要大大的双眼来阅读,大大的手来翻动书页,也需要大大的耳朵来倾听某处野生动物的呼号。
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当代日本动画艺术家设计的形象会这么吸引人。他们笔下的儿童,总是有着大眼睛和扁小的鼻子。这样的外观,重塑了西方对视觉和嗅觉的表现方式。它们展示了我们是如何睁大双眼,徜徉在一个布满了插画和奇特线条与色彩的世界中的。同时,这些作品也体现了献给全世界新一代读者的美学理念,似乎生活就是出色的立体书或连环画,似乎没有什么感受或画面是不适合儿童观看和儿童文学描绘的。
撰文 (美)塞思·勒若
编辑 徐伟
校对 何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