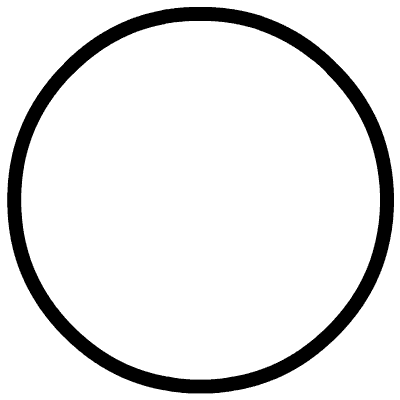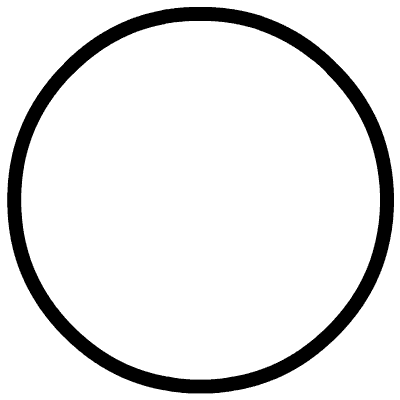 点击上面蓝字订阅本账号!
点击上面蓝字订阅本账号!
图:1987年的深圳
原创: 城不易
来源: 城不易(ID:Chengbuyi_)
文章已获授权
1987年,44岁的任正非上当受骗,亏掉了公司200万元,同时由于生活上的遭遇,与妻子的感情出现裂痕。最后的结果里,任正非与妻子离婚,离职下海,和几个老兄弟一起凑了2万块,在深圳的一个居民楼里创办了华为。
任正非创立华为,与其说是他想创办一家世界级企业,倒不如说只想混口饭吃。当时的深圳,许多人都靠倒买倒卖发了财,任正非也想成为其中的一员。
于是,华为先是卖过减肥药,后捣鼓过墓碑生意。幸好这两样生意都没做大,不然,中国可能少了一家通信公司,而多了一家减肥药公司,我们也少了:“华为牌减肥茶,排除毒素,一身轻松。”这句广告词。
虽然开局不佳,但任正非毕竟是技术出身,开始了自主研发。先打入香江、再进入欧美,随后扩展亚非拉,业务范围也扩展到了运营商网络、企业方案、智能手机这三大领域。开始了手撕三星,拳打思科,脚踢爱立信的历程。
在华为发家的这些年,原本还是个大工地的深圳,也从慢跑变成了加速跑,一直跑到了国际大都市的地位,GDP从55亿涨到了2.2万亿,经济体量翻了400倍。
城市培育企业,企业反哺城市。深圳给华为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华为又带动了深圳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两者如同道教的太极阴阳图,相融相通。深圳市长陈如桂,更是公开直言要“服务华为。”
然而,“服务华为”这四个字,由于部分人的私心,引导出了华为科技城的闹剧。让任正非不再对从深圳拿到更多土地抱有期望。2012年,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成立,华为投资100亿,开始打造东莞基地。
深圳民间沸腾,有人高呼“不要让华为跑了。”对此,华为嘴上说着不会走,身体却很诚实。该投资投资,该走人走人。这一事件已经尘埃落定,覆水难收。
然而,与其将华为转移部门的原因怪罪于某某某,倒不如探讨一下实业与房价的关系。在货币投放加速的宏观环境下,中国M2的货币供应量从10万亿涨到了177万亿。房价一日长一个头,作为经济翘楚的深圳,不但改革开放走在了前头,连房价也是遥遥领先。
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华为要建厂,没有地。华为员工要买房,买不起。树挪死,人挪活,1500辆车载着2700名华为人,从深圳驶向了松山湖,到了2018年11月,累计转移了1.8万人。
在房价暴涨的时代,专心做企业成了一个大难题。有些企业像华为一样,另寻他处,有些企业干脆就把眼光放到了国外,资金就像坐飞机一样,飞去了异国他乡。
01
到国外投资的企业家里,曹德旺和郭台铭无疑是最有名的2位。前者靠汽车玻璃发家,后者以代加工出名,两人旗下的企业市值分别是1000亿和4000亿。
2016年,曹德旺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建了三个工厂。而郭台铭手笔更大,信奉“市场就是祖国”的他直接投资了100亿美元。
钱可通神,更何况是钱能带来选票的美国。曹德旺和许多美国州长成了好朋友。郭台铭更是直接成了特朗普的座上客,后者特地出现在美国富士康破土的当天,两人谈笑风生。
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往往有一种“你行我也行”的想法,而曹郭两人的行为无疑给众人开了个好头,于是乎,众多上市、没上市的企业,一拥而上去了海外,在异国他乡遍地开花。
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到巴西的圣保罗,从越南的河内到印度的安得拉。一家家中资工厂,犹如春雨后冒出的笋尖,纷纷冒头。
对于投资海外,曹德旺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美国,地便宜、能源便宜、交通便宜,就是劳动力有点贵。然而,随着中国劳动力10年里10-20%的平均工资增长率,美国的工资看上去也不那么贵了。
而波士顿咨询公司则在5年前就从侧面佐证了这一说法,指出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
资本的套路千奇百怪,但不奇怪的是,哪里能挣最多的钱就跑到哪里。在中国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企业家们往国外纵身一跃,早已司空见惯。这其中,房价背的锅可不小。
众所周知,企业要发展或扩大产能,第一步就是建厂或租厂,但随着房价上涨,租金费用往往高了不止一倍。其次,原材料价格也被房价拉着,一路抬头。
除了场地、原材料,劳动力这一要素也至关重要。正如有了锅,有了菜,自然少不了一个掌勺的人。
但在近几年的东部,却是屡屡出现了民工荒。这出现的频率,往往与房价的快速上涨形成了重叠。毕竟,房价的升高往往会带动租金的提升,但工资却走的不疾不徐。既然挣不到什么钱,农民工自然也就不会外出。
厂房、原材料、劳动力,这三大实体经济的重要元素,深受房价其害。但若说影响最大的,却还是实体企业的资金流。
人可以几天不吃饭,但不能几天不喝水,对企业来说,资金一断,立刻完蛋。然而,现在的企业,想要能通过正常的渠道从银行贷款,却越来越难了。
2017年3月,原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列了一组数字,这组数字触目惊心:银行新增贷款12.65万亿,房地产贷款占了近一半。而工业占了多少?多的省份超不过20%,最少的省份更是只有13%。
没有银行的资金,但是企业仍要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为了生存或者发展,就被迫向一些民间的高利贷融资,进一步加剧了营业成本,甚至酿出了一幕幕惨剧。震惊全国的大案——于欢案,便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下。
2016年4月,于欢与母亲苏明霞被债主吴学占等11名催债人员限制住了人身自由,这些催债人对苏明霞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在长达一小时的凌辱后,杜志浩脱下裤子,当于欢的面用下体污辱苏银霞。
有人报警,民警进入接待室后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22岁的于欢求助无门,于是摸出一把水果刀乱刺,致4人受伤。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案件爆发后,由于其中涉及到各种错综复杂的元素,迅速吸引了全国人民的眼球。但少有人知道的,这起悲剧的背后,是房地产对实业的碾压,以及民营企业家借贷无门的困局。
于欢的母亲苏明霞,是一家钢贸企业的法人代表。这家企业最早从事圆钢(音)和刹车片的生产销售,后来圆钢价格暴跌,就改为只做刹车片,而刹车片的原材料主要就是钢铁。
2012-2015年这三年,由于钢价暴跌,全国60%以上的钢贸商被洗牌出局,在这个钢贸行业的冬天里,银行不仅停止贷款,并且提前将贷款取回。
苏明霞的钢贸企业也未能幸免于难,遭受了严重损失,举步维艰。苏明霞作为一名企业家,不仅要偿还拖欠工人的工资,还要保住企业。在难以向银行借款的前提下,她才走上了向民间借高利贷的道路,一步错,步步错,悲剧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
2017年6月,于欢因防卫过当判处5年,其母苏明霞因非法集资判处3年。全国人民更关心其中的社会伦理,却少有人关注背后的的实体危机。
泰戈尔在《飞鸟集》曾写到过:“你看不见你的真相,你所看见的,只是你的影子。”
在这起案件的影子里,不知道还有多少苏明霞们正通过民间借贷去挽救自己的企业,或是破产,或是跑路,或是仍被催债的黑社会胁迫殴打。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大众的视线之外。
许多专心做实业的企业家们倒了,不专心的,却往往却发了大财。
02
关于实业的困境,财经作家吴晓波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做《中国实业已死》,被广泛传阅。这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让人记忆深刻:
“年初,我去瑞士苏黎世旅游,那是全球公认的居住环境最好、也是物价最为昂贵的城市。在苏黎世的中心商业街上,我赫然被橱窗里的一只压力锅给吸引住了。它呈醒目的深蓝色,是德国双立人品牌,而让我停住的原因则是它的标价:290欧元。一只压力锅竟可售卖到如此高价,让我不由惊叹。
谁料,与我同行的一位企业家朋友告诉我,这只锅在国内中心城市的售价是3200元人民币,他的太太日前刚好看中一只。为了求证,我用手机把这只锅拍了下来。
凑巧的是,回到国内的几天后,我在一次座谈会上碰到了一家民营压力锅企业的董事长,这家企业位于东南沿海的一个小县城,二十年前我曾经去那里采访过,当时还是一间很不起眼的街道小厂,替沈阳的双喜牌压力锅做贴牌生产。
近十多年,这家企业自立品牌,扩张发展,赫然已成国内行业冠军,其产量在全球也排第四。座谈期间,我把手机中的照片给那位董事长看,提出的问题是,你的工厂能否生产出这样的高价产品?他回答说,质量和功能应该可以接近,可是价格却怎么也定不到那么高,最多不过千元。
接着,他突然告诉我,现在,他最大的兴趣已经从做压力锅转到资本经营了,前年,他已经把企业的大部分股份出售给法国的一个家电集团,得二十多亿元。我问,那么你现在正在做什么?他说,在家乡投资了一个岛,准备开发房地产和码头,政府对他非常支持,其盈利前景大大的好过生产压力锅。”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资本家永远是朝着能使资本增值的领域狂奔。在这篇文章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全球产量第四的高压锅企业是如何变成了一个小县城的房地产开发商。
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中国经济脱实入虚的悲哀。实业不挣钱,也难怪企业家拿脚投票。那么,实业到底有多不挣钱呢?我们来看看下面另一个例子——上海振华。
大多数人知道上海振华,还是从奥巴马的一次演讲开始。2013年3月29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迈阿密港口演讲,主题是鼓励美国人使用“美国制造”。然而一阵海风吹过,刮落了总统身后的星条旗,露出了一个“ZPMC”(上海振华重工)的标志。
幸亏奥巴马脸黑,看不出表情的他继续鼓舞made in America,然而,这一场演说仍然尴尬落台。有美国网友调侃:“我敢打赌,这面星条旗也是made in China”
故事归故事,上海振华重工这家企业,如同金庸笔下独孤求败一般,在世界市场上大放光芒。以港口机械这个领域来说,上海振华可以说是拳打南山敬老院,脚踢北海幼儿园。从2015年6月至2016年6月间,全球共有271台岸桥订单,其中222台订单来自中交集团所属振华重工,占比82%。
全球市场份额的80%,已经可以是独领风骚了。那么它的利润有多少?根据2016年上海振华的年报,净利润只有区区3亿元!!同样是在2016年,深圳水贝村拆迁,网传每户至少一个亿。
一个业务遍布全球,员工分布世界,多次登上《大国重器》等纪录片的企业,辛辛苦苦一年的利润,不如城中村3户居民的拆迁款。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制造业的利润有多稀薄了。
吉利董事长李书福就直言,“有的企业自嘲“辛辛苦苦一辈子,还不如在资本市场讲个小故事。”思前想去,如果可以把做实业的企业家请上吐槽大会,可以吐槽的点大概可以讲满三天三夜还不带重复的。
正如之前所说的,企业家是会拿脚投票的。与做实业的各种低三下四求人办事相比,炒房那点把戏,完全不算是个事儿。
于是乎,专心做实业的大企业,开始变得寥寥无几,如同暑天下大雪——少见。而上市公司、国企央企或各种中小企业,一个个如同泥鳅上水,争先恐后得进了楼市。就怕差人一步,少挣了一波快钱、热钱。
就像一只只的山羊,吃光了草根,荒芜了森林。
03
经济学上,有一个术语叫做羊群效应,通常用来描述经济个体的从众跟风心理。一旦羊群里的领头羊开始动作,那么整个羊群就会不断摹仿这个领头羊的举动,领头羊做什么,群羊也做什么。
而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里也有类似的表达:“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
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下,中国的众多企业家们,同羊群又是如何类似,小公司跟着大公司,穷公司跟着富公司,纷纷去追逐楼市的财富。而专心做实业,却往往成了异类。
几年前还被提倡的“企业家精神”,到今天成了濒危动物。甚至被玩地产的人笑称,这就是“武大郎精神”。自家漂亮媳妇都跟西门庆睡了,还傻不拉几地着坚持着匠人匠心起早贪黑做炊饼,除了令人感动之外,免不了服毒而死的悲惨结局。
不仅毒死了今天,还毒死了明天。
在中国,每天诞生1.5万家企业,然而往往3年不到,大多数的企业就如同飞蛾扑火,走向了破灭的边缘。这些数字的背后,往往是各种妻离子散的悲剧,东山再起者,永远只是少数。
耳濡目染,越来越多人开始恐惧创业,害怕失败。根据《全球创业观察(GEM)2017/2018中国报告》,中国创业者恐惧失败的比例从2002年的25%上升到2017年的41%,而认为自己具备创业能力的比例从2002年的37%下降到2017年的28%
创业艰难,而房价却搭上了高铁。创业和房价的关系,好像是汪峰的两首歌,一首叫做《生来彷徨》,另一首叫做《飞的更高》。
民间高呼“万般皆下品,唯有炒房高”。无数调侃实业的段子,也纷纷冒出了头:
“我的一个朋友,坚持做珠宝生意。当年为了弄几个柜台,买了一栋楼,现在楼的价值比做这么多年生意赚的还多。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做实业,资本有一天就会给你回报。”
笑话归笑话,却也看出了深深的无奈。然而,实业若是被房价压垮了,断供潮还会远吗?
就在不久前,近360套法拍房出现在了深圳,众多媒体大呼小叫这是断供潮。然而最后证明,这只不过是部分投资客的资金链断裂所引起的债务清偿。
见微知著,又有谁能知道这是不是只是尚未燎原的星星之火?这批法拍房的投资客是企业主还是个人?资金链断裂的原因是因为实业受损还是因为公司裁员?没有几个人知道这背后的真正原因。
以日本为例。在1989年,由于央行的升息以及海湾战争的爆发,大批沉迷于楼市和股市的日本企业由小到大纷纷倒闭。
企业裁员,员工降薪,众多企业和其雇工的贷款成为银行的大量不良贷款,断供潮出现在了日本各地。大量被抛售的房子出现在市场上,随同日本被戳破的经济一起,一路下滑。
日本走过的路,香港走过,美国也走过。而今天的中国,又会走向何方?
没有实业支撑的房价,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正如上文所说,日日高升的房价,却在一步步掐紧实业的喉咙,而实业,却为众多买房的年轻人们,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买房的月供。
如果实业倒了,房价大厦必然也会被一同抽掉了地基。
当然,无论我们这些普通人怎么感慨,这个时代的路,或许早已在未来的历史书上被注定。我们只能告诉自己,在这一场可能影响未来中国的经济变局中,不要轻易地拿自己的一生去做一场赌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