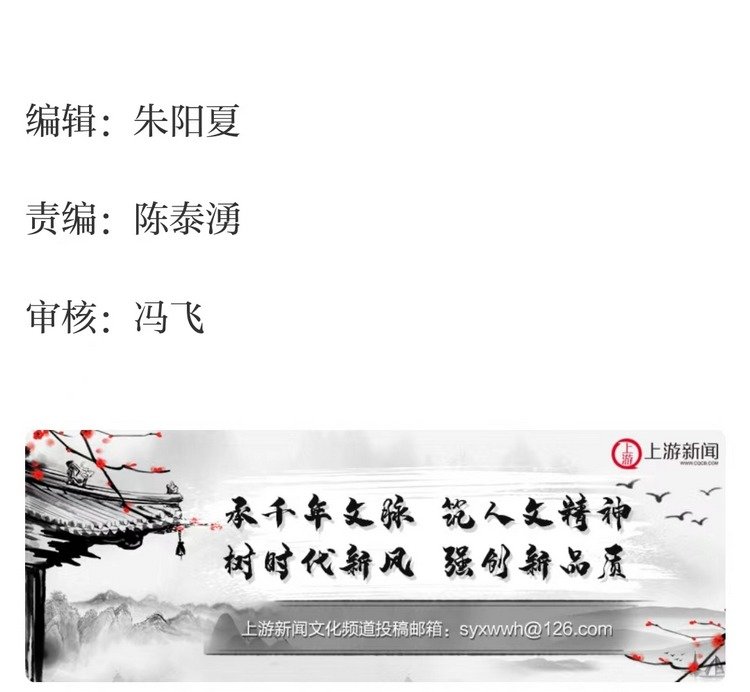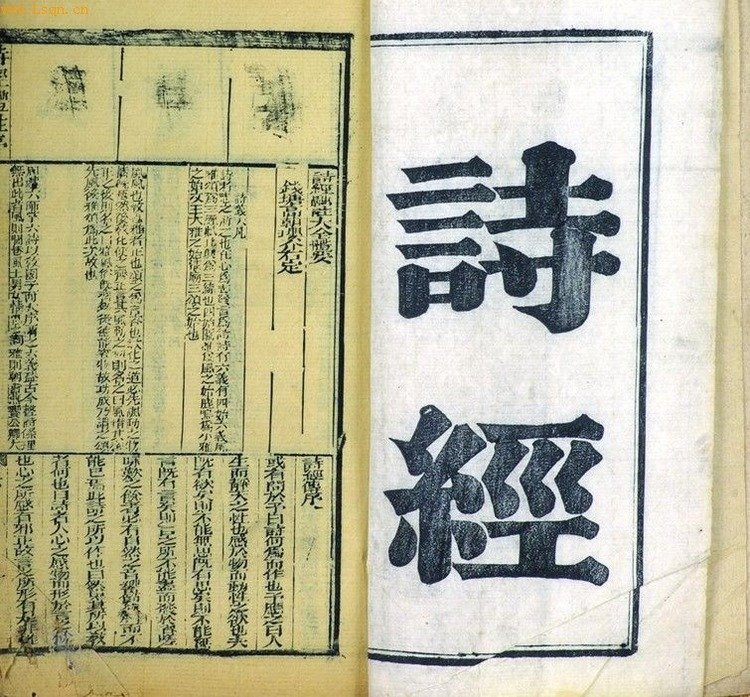
俗人也谈诗之雅
文/张跃
诗是雅品,写诗需要是雅人,最起码也要有雅心。读诗、谈诗大约也要有雅兴才配的。我是俗人,几十年来,因生计的奔波,油盐柴米等人间烟火味熏了心,也熏了手,现在无论怎样的洗手焚香,总雅不起来了。就来个俗人谈诗吧,我想诗倘若真能让俗人爱读、爱谈,使它不致演变成象牙塔里的“国粹”而需要加以保护,那于诗也该是有幸的吧。
我想,诗起源时也许并非是好高雅的。就看诗的老祖宗《诗经》吧。“风”篇即是民风民俗,是当时文盲的劳动者在劳动时的咏叹,作诗的人就是他们这些“俗人”。他们那时也是为油盐柴米等生计而奔波劳碌着,并没有走进宽敞有空调的象牙塔里去哼吟的福气。用“哼哈哼哈”以协调共同劳动的节奏,喊“杭育杭育”以减轻劳累和疲乏,在汗珠滚落中这诗(或叫做“歌”)就创作出来了,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杭育杭育”派。自然,他们也不觉得这歌有好“雅”,自己有好“雅”。因为俗人们不识字,这些诗就一直代代口传,自然在传承中也添加了些内容和形式创新。后来,遇着朝廷的采风的官吏来代帝王“了解民情”了,便用文字记了下来,带了回去。这口传之“诗”,一变成文字,那就不得了了,“雅”起来了。因为文字是俗人们不懂的东西,他们就崇拜。虽原是自己吟唱之作,但一成了别人文字里的东西,就崇拜了。其实他们此时崇拜的并不是这内容,是记载这内容的文字,自然连使用这文字的人也一起崇拜起来了。后经孔圣人一删定,且评价曰“《诗》,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诗就成经典了,是为《诗经》。诗此时岂止雅而已,它还神圣了起来,高了起来,俗人就更难且也不敢窥其门径了。其实,就《诗经》中的风、雅、颂三部分看起来,“风”还是最好的,也是其精华。因为它是俗人们的创作,更反映了俗人们的生活、俗人们的心愿、俗人们的情感。
后来使用文字的人们,借采风之机夹些自己的私货,以达到个人的目的,或借歌颂谋取利益,或借牢骚抒发自己的委屈,于是文人诗就诞生了。因为里面总可以看到自己的思想,于是圣人又定义曰“诗言志”。诗确实能发心声,“言志”向的,但志有鸿鹄燕雀之异,心有善恶之别,表达诗的手法也有高下之差,这为心声之“言”自然也就有了好坏之分了。
不过辨别这好坏的标准也着实让人有些为难。不但要看评判者的心境,还要看被评判者的地位等级。“云想衣裳花想容”的诗句,就很使唐玄宗喜欢。他饮美酒、赏名花、对美人,处温柔乡中听这温婉缠绵的诗句,“云衣花容”不但可赏,还能独揽、独占,自然会连声叫好的,然而这“清平调”三章却未必是李白最好的。有时,“一时诗名”也不能就“盖棺定论”,李白在世时诗名大噪,杜甫活着时诗却并不被看好,但后世他却就与李白齐了名。于是圣人又解释一句云:“诗无达诂”。
也许诗真的是“无达诂”的吧,但千百年来也竟有人们一致公认的这么多好诗,说明它还是应当有一些经本准则的。这些好诗或忧身伤时,或慨叹民生,或寄情山水,或仙或圣,或鬼或杰,不一而足,似乎的确有一条“准绳”。这准绳如果也能“一言以蔽之”的话,那是“得人气”。能写出“人人心中有”,就是人人“心有戚戚焉”的情感,自然会引起共鸣,自然会“得人气”。不过这里的“人人”,理论上是全体,实际上也只能是部分。诗的高下区分之一,大约就是这“人人”范围的大小吧。陶潜诗好,其实也只得了和他有相同或相近之心那部分人的“戚戚焉”的。白居易想得更多人气,便力争把诗写浅白,使老婆婆都能懂,扩大“人气”群。再说透一点,就是要胸怀大爱,才能得人气。哪怕自己茅屋漏雨,杜甫不是推己及人,想到了天下寒士吗?入美山美水,诗人们陶醉而抒发的不还是“人人心中有”的情怀吗?大约这算是好诗立世基点之一吧。
好诗有大爱的情怀大约还不够,还需能写出“人人笔下无”的境界来。自古以来什么“境界说”、“静穆说”等等纷繁复杂。说文一点就是写诗的“手法”和技巧,有“僧敲月下门”、“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炼字法,有杜甫那种“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炼句法,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的反常规思维法,有“这个婆娘不是人,九天仙女下凡尘”的一惊一乍法……不一而足,也玄乎其玄。如果也能“一言以蔽之”的话,那就是“翻新出奇”。句佳在哪里?语惊人处何在?就在于能写出的“人人笔下无”。
好诗也许还要是能流传的诗。我想好诗不但要能得当时的“人气”而传遍天下,还有能得后世的人气而流传千古。没“传下来”的好诗也许也有吧,因没见过,便不去妄测。据传下来的好诗看,真是能让千古以来的人都“心有戚戚焉”的。所以唐诗宋词是高峰。有唐以来至如今,平常的人们都能随时随口就可以“唐诗、宋词”一下,这就是它们不但得了当时的“人气”,还得了千古以来的“人气”的见证。可以肯定地说,这人气还可以“得”下去的,这就是它们的伟大之处。虽有人说“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但以他们诗篇得人气的指数趋势来看,还会万“万古”传的,你且奈之何?
自然诗也是需要演变的。自《诗经》以来,演变到了如今,形式虽变了,但诗的那魂并没有变。如果又能“一言以蔽之”的话,那就叫“接地气”。我这里指的“接地气”,既指来源于社会生活,还要能被社会认同、喜爱。《诗经》的诗最精华的部分是“接地气”来的,楚辞、汉赋至唐诗没能离了“地气”。唐末宋初,为适应大众,得当时人气,词这种歌体就开始出现直至鼎盛。“有井水处就能歌柳词”,你看它好“接地气”,且好“得人气”。虽然士大夫词得的是士大夫们的“人气”,但苏轼、辛弃疾等士大夫精英们接民间地气的作品也多,得民间人气的也不少。“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你看多“接地气”!“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你看多“接地气”!李清照的词更是大胆用当时的口语,加以精湛的表现,接了“地气”,得了更多的“人气”。由此,宋词也终于发展到了顶峰。
新诗出现的初衷,固然有时事变迁的需求,但据我猜测大半也是因为想让大多数民众(也就是俗人)喜欢它、掌握它,让更多的人能写、能读和喜爱。但新诗字句虽然白话了,这诗却离大众远了,读它的人越来越少。正如人们所说,新诗“无可背之篇,无可摘之句”(大意),“读诗的人和写诗的人一样多”云云,这不得不令人反思。如此下去,新诗真的要离开俗人而“雅”起来了,成了象牙塔里的雅人们“自娱自乐”的雅品了。新诗若弃了大众,自然也会被大众所弃的。真如此,那就真是“危”了,但愿这是“杞人忧天”吧。
新诗要活,必须要得人气、接地气。语言白话了,如何让俗人大众也喜爱,这正是新诗要突破的瓶颈。俗人谈诗,难免沾染俗气,和这“雅品”似乎是挺不相宜的。但我想新诗能接点地气、沾点俗气,多得些人气也许并不是坏事的。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现供职于万盛经开区文化旅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