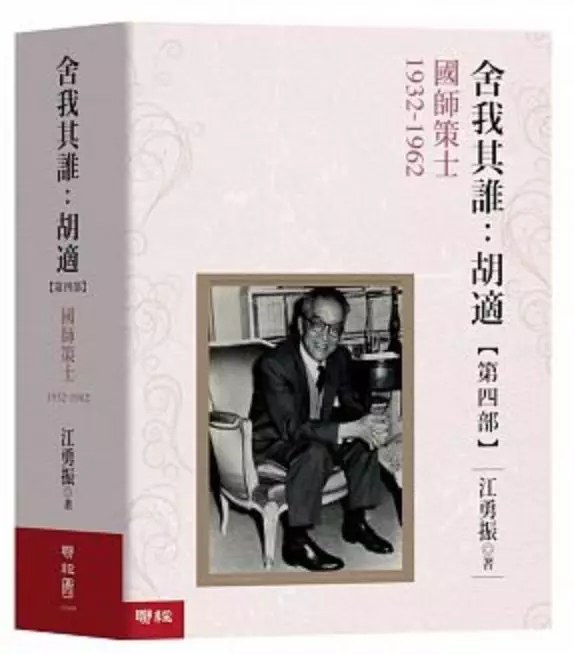
《舍我其谁:胡适【第四部】——国师策士(1932-1962)》,江勇振著,联经出版公司,2018年1月版,864页
为了把握日本学界胡适研究的程度,有必要了解中文学界的研究进展。为此,最近花了不少时间阅读江勇振的《舍我其谁:胡适》第四部《国师策士(1932-1962)》。先说总的判断:本书取材丰富(尤重英文材料和档案的利用),观点鲜明(有时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嫌),人物刻画比较细腻,言常人所不敢言,发前人所未发(褒贬义兼而有之),对理解和认识胡适的后半生颇有帮助,在胡适研究史上必将占有重要的地位。不过,本书在写作上存在诸多缺陷,在学术规范上存在一些疑问,这些缺陷和疑问无疑损害了它的成色。尽管如此,本书的价值和贡献不容忽视,无可否认,理应得到充分的批评和讨论。然而,本书出版已将近六年,迄今未见一篇书评,这长久的沉默十足耐人寻味。于此,笔者不揣谫陋,略陈鄙见,以就教于大方之家。本文略去敬称。
拙文分两个部分,先是内容简介,然后是评议。
胡适:从保守政论家到冷战斗士
江著长达八百六十二页,称得上皇皇巨著。不过要确切地把握其内容,却并不容易。这里只能聊尽介绍之责,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全书除前言、序幕、幕落之外,主体由四章组成。
在前言中,作者讲述了写作宗旨:
在这种过去与现在交会的意义之下,今天研究胡适最确切的态度,就是要适切地在历史与当代的脉络之间取其均衡点,并以之来评判胡适。(14页。按:直接引文中如有使用不当的标点、错别字、病句或不太通顺的地方,均原样抄录,不作更正。下同。)
序幕的主旨是,通过考察《胡适口述自传》的访问过程,说明胡适的老于世故——他到了晚年已经成了“一个三缄其口的金人”(20页)。
第一章
本章主要检讨胡适1930年代的政论,具体来说,是1937年9月赴美之前胡适关于民主政治和对日政策的言论。
在作者看来,胡适在1930年代以后日趋保守,1932年9月写《惨痛的回忆与反省》时已经和蒋介石同道相谋(54页)。西安事变后,胡适在《大公报》上发表《张学良的叛国》,“已经不是一个学者的口气,而更像是一个政治打手”(62页)。作者认为,这个时期有两件事可以证明胡适“一面倒向蒋介石”,一是他并不同情1932年底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70-71页),二是他劝《独立评论》的朋友充当蒋介石的幕僚(76页)。换言之,1930年代的胡适是以“王者师”自期,而以“诤臣”期许那些从政的朋友,因此他在“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只谈理论不谈实际,或者说,只谈欧美的实际而不触及中国的实际”——蒋介石独裁(98页)。
作者主张,“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上联)与“专家政治是研究院的政治”(下联)必须联在一起,才构成胡适完整的政治哲学(98页)。而且,上联是为中国作的,下联则是为美国作的(115页)。作者将杜威、胡适师徒的自由主义相对比,认为杜威重视“民治”,而胡适注重“民享”(142页):
全民参与对杜威来说,是民主政治一个不可妥协的原则。对胡适来说,“民享”既然是民主的目的,专家政治既然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方法,则“民治”就成为一个无关宏旨的枝节。……从这个角度看来,胡适对民主的看法是接近二十世纪美国民主现实主义者(democratic realists)。(143页)
民主政治之外,这一时期最让中国知识分子忧心的,毫无疑问是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作者认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9月,胡适对日本的策略经历了八次变化(40页)。关于前三次转变(从“九一八”到1933年春),胡适在1934年4月11日写的《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一文里作了交代(156页)。1933年5月迎来了第四次改变,胡适主张对日妥协(169页)。1935年6月,第五次转变——和、战并提(185页)。1937年1月,第六次转变——以区域性的和平机制来抵抗日本的侵略(200页)。7月底,胡适改而主张放弃伪满洲国,以此作为和谈的条件(205页)。不过这个看法只维持了一个月,9月初,胡适迎来了对日策略的第八次转变——“苦撑待变”(213页)。
第二章
本章主要聚焦作为驻美大使的胡适。不过,在担任大使之前,胡适就被蒋介石派去美国执行秘密任务。这个任务就是蒋介石要求罗斯福总统出面调停中日战争(220页)。这是本章第一节的核心内容。
第二节“以夷制夷、长期抗战”,书中有如下一段概括:
胡适的“苦撑待变”跟蒋介石的“长期抗战”,使的就是一个“拖”字诀。胡适跟蒋介石就是志同道合地要拖到列强出面干涉,以求取最后的胜利。不管称之为“苦撑待变”还是“长期抗战”,这种引日本入甕,然后借列强之力来打败日本的策略,就是“以夷制夷”。(220页)
第三节“伟哉《慕尼黑协定》”。从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订到1939年9月欧战爆发,胡适在这一年间为张伯伦大唱赞歌,殷切期盼远东也有这么一个协定来消弭中日之间的战火(220-221页)。
第四节“新官上任就惹祸”。胡适1938年10月28日正式就任驻美大使,但因不谙外交,刚上任不久,就两度因言惹祸。一言以蔽之,胡适泄露了中国有向日本求和之意,与政府继续抗战的宣言相矛盾,甚至可能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支援(328页)。
第五节“苦撑待变”主要讲述了胡适的大使哲学。作者认为,胡适在驻美大使任内的基调是被动的,他的“苦撑待变”着眼于促成美国的“变”,而不是积极、主动地以中国为本位(333页)。欧战爆发后,胡适的“苦撑待变”不再是单纯祈求美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而是希冀建立集体安全保障体制,重新整顿世界秩序(345页)。
“苦撑待变”一节长达一百二十页,涉及内容甚多,但因本书一团浆糊似的写作手法,眉目不清,要准确把握其重点,颇为费力。在上述“苦撑待变”思想内涵的转变之外,我们可以读出同僚陈光甫、上司蒋介石、竞争对手宋子文等人(按叙述前后为序)眼里驻美大使胡适的形象。一句话,这个形象与很多学者、写家笔下的口才绝伦、长袖善舞、恪尽职守的胡适大使截然不同——作为外交官的胡适为德不卒(337页)、情报失灵(353页)、严重失职(364、400页)、一问三不知(405页)。
其中,对我来说感觉比较新鲜的是毛邦初《在美见闻》中对胡适的揭发:
胡大使之口才与学问,虽可补救政治上及外交上所缺乏之经验,但彼向未服务国民政府,易持在野政客批评之态度。彼既不十分明了我国惨淡经营之苦衷,又不熟谙军事情形。故对于长期抗战,始则疑惧,继则惊讶,现在渐渐信服。在昔美国舆论未一致同情援华之时,胡大使对于我国抗战宣传,并无特别努力。现美国舆论既一致援华,而胡大使不肯努力向政府方面活动,以收舆论同情之效。仍依旧到各学校、及学校团体演讲。计得各校名誉博士学位,已有十四个。胡大使每对客言,彼由大学教授降格为外交家,颇有不屑政治外交之意。虽近诙谐,远非美国政府官吏、及政客之所乐闻。……(380页)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节第388页至439页主要叙述了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与美国国务卿赫尔长达八个月的非正式谈判,以及蒋介石政府对美日谈判的回应。美日谈判的失败导致了珍珠港事件的爆发,而胡适日记中没有任何关于美日谈判的记载(398页)。作者认为,美日谈判最终破裂,主要是由于蒋介石的强烈反对。而蒋介石之所以对美日谈判的结果勃然大怒,一是因为他担心日本从法属印度支那进军中国西南,二是中美之间沟通不善,而胡适担负的责任最大(404-405页)。
第三章
本章描摹了胡适在抗战后由“过河卒子”变成蒋介石的“棋子”、冷战斗士的经过。
第一节首先详细分析了“国府委员加官记”(蒋介石1947年1月委任胡适为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傅斯年坚持独立思想,苦劝胡适不要进入政府,胡适本人则愿意为蒋介石“撑面子”、当“幌子”、作“棋子”〔476-490页〕)、“再度使美惊魂记”(蒋介石1947年12月请胡适第二次担任驻美大使,胡适为之动心〔494-496页〕)、“蒋介石让贤记”(1948年3月蒋介石将总统大位出让,胡适怦然心动〔497-509页〕)。
对胡适这个时期的表现,书中作了相当严厉的批判:
胡适在“蒋介石让贤记”这出戏里所扮演的角色,说穿了其实相当不堪。他不但曾经一时怦然心动,而且甘愿作为蒋介石的一颗棋子、一个傀儡,任其摆布。更惊人的是,他在这整个事件的过程中,不但为虎作伥,连署那阉割了宪法、给予蒋介石宣布戒严全权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而且还作了一个两面人,做过一件言不由衷的事情。(496-497页)
作者认为,1946年胡适回国后,“在政府之外只是其表,他跟蒋介石政府暗通款曲才是其实”,“不但跟蒋介石是志同道合,而且他还是蒋介石不挂名的智囊、参谋”(511页)。
接着,本节最后四十页着重刻画了胡适以武力对付共产党的“鹰派”形象。本书指出,胡适赞成国民党出兵东北打内战(511页)。作者强调,胡适1945年8月24日在纽约写给毛泽东的信,其重点在于警告共产党“万不可小不忍而自致毁灭”(512页)。而且,胡适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在1947年7月4日通过的戡乱动员令,“对他而言,这个命令只不过是老实承认了武力是唯一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法门”(517页)。到了1948年初,东北战况已开始扭转,胡适却相当乐观,并表示“和比战难”,仍然相信共产党必败(518-520页)。与此同时,局势的急转直下,也影响了胡适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和立场(523-533页)。
面对残酷的战场形势,蒋介石一边考虑使用化学武器,一边派宋美龄出马请求美国介入内战,但遭到拒绝(535-540页)。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直到蒋介石政权崩溃前夕,胡适仍坚决支持剿共(540页),甚至梦想划江而治,“做成南北朝局面”(549页)。
第二节以浓重的笔墨描绘了胡适“冷战斗士”的偏执狂形象。1949年4月胡适逃到美国后,仍与蒋介石保持联系。蒋介石给他的任务是,争取美国的援助,阻止美国承认中共政权(563页)。在此期间,胡适拒绝了“外交部长”“行政院院长”的职位(568、576-577页)。
这一节的重点是胡适如何理解和解释1949年的历史巨变。胡适原先主张,共产党之所以能席卷中国,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主要是因为国民政府是“一个腐败、迟疑、士气全失的政府”(578页)。经过长期痛苦的挣扎和酝酿,胡适于1950年8月完成了《斯大林战略下的中国》(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在这篇著名的冷战文献中,胡适认为过去二十五年有两个历史转折点,一是西安事变,二是雅尔塔密约(597页)。总之,胡适将国民党的失败归因于斯大林征服世界的战略,以及美国人的援助不力,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无能和不得民心却缄口不言。作者认为,胡适这篇长文的中心概念的灵感来源,是章柏林(William Chamberlin)为《征服世界的蓝图:共产党的官方计划》(Blueprint for World Conquest:The Official Communist Plan)所写的《引论》(598页)。此外,如何消化、批判美国政府1949年8月发布的《对华白皮书》(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是胡适等人的另一个课题(618-625页)。
疯狂使人盲目,胡适也不例外。对于胡适的反共偏执狂,普通的美国公民也不堪忍受(629页)。作者认定:“在胡适的晚年,在他的反共偏执症的缠绕之下,胡适变成了一个恨不得立即全面展开反共‘圣战’的鹰派里的鹰派,冷战斗士里的冷战斗士。”(627页)胡适一直不相信中国大陆1953年的人口普查数据(634页),可以看作这种症状的一种表现。
第四章
本章对胡适晚年的思想作了一次深度扫描,书中有如下主张:
胡适晚年的思想不是自由主义——不管是“社会化的自由主义”或是传统的自由主义——所能形容的。胡适晚年的思想必须放在美国冷战的脉络之下来理解。最适合用来描述他晚年思想的,是美国在196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保守主义”。美国这个“新保守主义”的特点不在于其对内的经济政策,而是在于其外交政策,亦即,反共,以及用军事、政治、经济的力量来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648页)
由于反共至上的立场,胡适晚年的政治思想是非黑即白。不是反共,就是亲共、或者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所有的自由主义者、第三势力,对胡适而言,都是非愚即诬,都是适足以壮大共产势力的同路人。因此,所有可能违反反共这个最高目标的个人、报刊杂志、与团体,他都跟他们保持距离。(648-649页)
作者认为,“晚年的胡适已经是到了自由诚可贵,反共价更高的地步。为了反共,其他原则都可以放弃”,并举了两个案例来说明胡适的“反共至上”。其一是,1952年胡适为了表明其坚决反共的立场,婉拒了英国牛津大学讲座教授的提名(718页)。其二是,1954年吴国桢事件发生后,胡适不再对自由主义者虚与委蛇,他在美国充当蒋介石的打手,发表文章回击吴国桢,而这是“一篇集说谎、抹黑、栽赃之大成的作品”(723页)。眼见胡适堕落到这般田地,作者不禁高呼:“反共、反共、多少学者的罪行假汝之名行之!”(734-735页)
据作者推测,胡适在1959年留下了一篇手稿大纲,题为《今日政论家应有的态度》。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我们对于政府、对于政府党,都应该自居于“诤友”的地位。“友”是主要的,“诤”是次要的。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不念旧恶,成与维新。”有一善,必赞扬它,使它发扬光大。(742页)
紧接着列了政府的七条“善”,诸如“陈诚的政府是应该鼓励的”“金门事件的胜利是应该赞扬的”“俞大维是应该赞扬的”“王世杰的入阁是应该赞扬的”之类。于此,作者批判道:
晚年的胡适会写出这样不堪的一篇《今日政论家应有的态度》的手稿,完全葬送了他经营了一辈子的二十世纪中国第一自由主义者的英名。胡适晚年何止是节节败退,他根本就是崩盘式的暴退。(742页)
以上大体是本章第一、三节的主旨。
第二节“反攻大陆:胡适、蒋介石有志一同”着重指出:“从某个角度来说,胡适对反攻大陆的信心比蒋介石更加的强烈、更加的持久。”(699页)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中共的参战,让胡适倍感振奋,他以为历史的转机即将到来(703页)。1952年11月,胡适在台北发表《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胡适提出了“他一生当中最为雄心勃勃的一个摧毁共产主义全球性的宏图战略”(704页)。按照这个大战略,“一直要到解放了苏联以后,才是凯旋班师之时。这种全球性的反共策略,远比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要更为彻底、更为极端”。讽刺的是,胡适的这个战略,与他批判的斯大林征服世界的战略,本质上是一致的,同为“以暴制暴”(707页)。
第四节“从毁党造党、毁党救国、到永远不想取得政权的在野党”,考察了胡适晚年的政党思想。一方面,胡适反对组织政党,特别是反对党,这在他对待蒋廷黻和雷震的态度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748、776页)。1958年5月27日,胡适在“自由中国社”的欢迎宴会上演讲《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最淋漓尽致地说明了胡适的言论自由的局限,以及他反对成立反对党的立场”(777页)。
另一方面,对于国民党,胡适先后提出了“毁党造党”和“毁党救国”的理论。这无异于与虎谋皮。胡适的建议让蒋介石怒不可遏,他在日记中破口大骂:“此种文人政客真是无耻共匪之不若矣……”(764页)
对于蒋介石的独裁,胡适也是一退再退。书中主要谈了两件事,一是胡适一开始持反对意见,但终究还是屈服,不得不推选蒋介石为非法的“总统”,不得不昧着良心说:“我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跟老百姓一样的高兴。”换言之,在蒋介石的淫威下,同样没有“沉默的自由”(792页)。
第二件事是雷震案。雷震被捕之初,胡适摆出一副不惜与蒋介石决裂的架势(799页)。但他终归本性“懦弱”,对雷震事件“始终是内疚弥深”(唐德刚语)。然而,作者的态度要决绝、严苛得多,直言胡适“冷血”“没有心肝”:
更值得省思的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大师,他说他所要营救的,是那根本没有自由的“自由中国”。其所显示的,是他心目中的自由、民主,其实只是功利主义的自由、民主。或者用更老实的话来说,只是为了得到美国的承认与援助的目的而必须去讲究的手段而已。(802页)
第五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作者认为,胡适1959年发表的《容忍与自由》“是一个人人拭目以待却让人败兴而归的结局(anticlimactic)”(816页)。与穆勒(John Stuart Mill)一百年前写的《自由论》相比,胡适的《容忍与自由》“根本就是诡辩”(831页)。
幕落写了胡适的遗嘱和死亡,同时仍不忘批判胡适的糊涂。在雷震案覆判宣布前一天,胡适谈及《自由中国》的“发刊词”,反而责备雷震没有“做到平易而正确的见解”(837-839页)。另外,胡适1961年9月接受报纸采访时作伪,谎称一个叫池田纯久的日本人说卢沟桥事变的第一枪可能是共产党开的(844-852页),或可反映晚年胡适的阴谋论偏执狂已病入膏肓。
不得不说,本书的内容十分丰富,以上只是一个非常粗糙的概括。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对江著的这套叙述和议论,必须时刻带着质疑和批判的态度来阅读,这也是本文标题加一问号的缘由。
“幸运”“神话”与“舍我其谁”
以下是评议。不过,要对江著作出比较全面、精准、到位的评价,远非笔者力所能及。这里只能谈一点粗浅的读后感。本节尝试通过三个关键词——“幸运”“神话”“舍我其谁”——来呈现作者的史料工夫、研究旨趣及个人性情。
总的来说,相对于第一、二章,第三、四章显得更精彩。其中,对《斯大林战略下的中国》写作过程的分析,可圈可点,这个视角值得称赞——不像绝大多数研究者那样“胡云亦云”。对胡适“鹰派”形象的塑造,对其晚年“暴退”的描摹,都相当细致,有些段落可谓入木三分。另外,胡适对《慕尼黑协定》的狂热,为了反共而放弃牛津大学讲座教授的荣誉,这种种细节让人震惊的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认识那个仿佛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胡适——历史上的胡适,绝不只有一顶“自由主义者”的帽子。
依我之见,本书最大的特色在于作者对研究对象的质疑和批判。这本是学术研究的题中之意。然而,具体到胡适研究,“自由主义者”仿佛成了一顶神圣不可触碰的皇冠,必须戴在胡适头上,绝不容许摘去。其实,胡适是不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者,首先应该作为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答案。否则很容易先入为主,用“自由主义者”这个框架去套胡适的一言一行,于是不符合这个形象的史料就在有意无意中被忽视、被轻描淡写,或者牵强附会,曲为之说(黄克武《胡适的顿挫》即有此病)。
由于跳脱了这个巨大的窠臼,江著在史料的运用和解读上就获得了比较大的解放,因此能言常人所不敢言,发前人所未发。譬如,因为打破了“自由主义”的紧箍咒,江著才会主张,胡适所谓的“超然”“独立”在1930年代以后已成为一种文字游戏,到了晚年则是“利用他的名声、地位,以‘超然’作为护符,而行效忠一独夫之实”(16页)。同样的,江著强调,“胡适晚年的思想,不是一个笼统的自由主义所能概括的”(647页)。当然,这些论断是否得当,是否逾越了界线,有待于全面的评估和深入的检讨。
如果说上面这一点属于研究理念,或许有些玄虚,而要贯彻这一理念,史料的查核和利用无疑是重中之重。与胡适相关的史料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历史学者首先需要做的无非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而在这方面,江著也给人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别的且不说,本书时不时出现的“幸运”“幸好”的字样,大致可以反映作者勤于“找东西”,兹举数例:
很幸运地,我在“胡适外文档案”里找到了胡适在杜威八秩寿辰祝寿学术讨论会上所宣读的《工具主义的政治概念》这篇论文——有草写涂改、但不全的手稿,也有最后改订了的打字稿。(117页)
幸好,我找到了一篇美国的新闻评论,内容极为火爆。(153页)
可惜,《美国外交文书》并没有印出胡适的“注疏”。幸运的是,史丹佛大学“胡佛档案馆”里的“洪贝克档案”存有胡适给洪贝克的原信。(300-301页)
胡适所改写的“备忘录”可惜《美国外交文书》没选登。幸运地,我在“罗斯福总统图书暨博物馆”(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 Museum)的网站上找到了胡适这篇“备忘录”。(314页)
非常幸运地,蒋廷黻的英文日记留下来了。(454页)
我想,每个做过研究的人都不难体会这种“幸运”背后的甘苦。
“幸运”之外,另一个在江著中频频出现的词是“神话”。近几十年的胡适研究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累积了许多神话,而江著花了很大的工夫,试图让这些神话现出原形。例如,有不少学者、写家津津乐道胡适赴美宣传的“威力”,出现了“日本需派出三个人一同出使,才可能抵抗得住胡适”的神话(237页),这无疑是昧于日本近代史、习惯于“脑补”造成的。再如,作者认为齐锡生的著作《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戳破了很多胡适使美时期的“神话”(334页)。又如,书中直指“日本偷袭珍珠港是因为罗斯福受了胡适的影响”,其源头是查理·毕尔德(Charles Beard)的阴谋论(439-441页)。另外,第二章、第四章的结尾都不忘破除胡适和金钱之间的神话,前者是美国《生活》杂志的记载,说胡适在担任驻美大使的时候,退还国民政府给的六万美元宣传费(446-449页),后者是指胡适去世后只留下了一百三十五美元(859-862页)。
对于“神话”,本书末尾有一番恳切的话:
神话之所以成为神话,而且为人所津津乐道,就是因为神话动听,让伟人看起来更加崇高、伟大,同时也有一定程度的诠释力。然而,神话总归是神话。除非我们宁愿活在神话里,我们还是终究必须走出神话。(862页)
我不敢说江著完全戳破了胡适下半生自由主义的神话,只能说它尽力做了这项工作,而读者是否接受,尚有待检验。我也不赞成书中的一些论断,比如,说胡适、蒋介石“志同道合”“暗通款曲”——过分强调了他们的合作,对两人的分歧关注不足。胡、蒋的关系问题十分复杂,有待跨学科的深入探究。再如,作者认为“新保守主义”的概念可以鞭辟入里地诠释胡适晚年的政治思想和态度(652页),我则认为这个词太cliché,远不如吴炳守的“冷战自由主义”来得锐利而明确(详后)。
然而,如我们所知,对一项研究来说,比结论更重要的是它能否挣脱教条的桎梏,引导人们重新审视这一课题,甚至开启新的研究领域。表现在历史学上,就是众人常说的新史料、新方法、新视角。就此而言,不得不说江著确实能让读者不带着“自由主义者”的标签去理解和认识胡适,以怀疑和批评的态度审视相关史料——大概有不少史料首次被使用。
《舍我其谁:胡适》四部曲是对近二三十年来胡适研究的“反拨”,其对抗学界主流言说的姿态不言而喻。不消说,本书也充分展现了作者“舍我其谁”的气概。譬如,书中有如下几段话:
“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这句话,恐怕是历来对胡适误解之最。贾祖麟(Jerome Grieder)对胡适早年自由主义的分析,至今仍然是最为细致,而且也是拿捏最为得当的。然而,即使如此,他也被胡适这句话给绊倒了。……(86页)
如果,出任大使那些年,是胡适一生中最被人误解、不解、乱解的阶段,则从他1946年从美国回到中国,然后又在1949年回到美国去以后的那几年,就是他一生当中第二个最被人误解、不解、乱解的阶段。(452页)
胡适晚年的思想,是历来研究胡适的人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个大混沌。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懵懂于胡适晚年的思想的来龙去脉。(647页)
首先,请注意这些话中的“最”字——这么多“最”,到底哪个是真正的“最”?其次,这几段话所要传达的意思很明确:“历来的”胡适研究都没有解决这些繁难的问题,而本书给出了清晰的答案——至于是否如此,读者可自行判断。这种“舍我其谁”的精神,一方面促使作者勤于爬梳史料,与各式各样的“胡适神话”奋力搏斗,另一方面也导致作者过于自信,乃至流于自负。在写作上,在学术规范上,似乎都显露无疑。
写作上的弊病
我曾批评《日当正中:1917-1927》在写作上存在不少弊端,引起作者强烈的反弹。这部《国师策士》似乎有所改进,怎奈仍然继承了前面几部的老毛病。比如目录,这是一本书最重要的门面之一,可是有的标题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如果说第一章的标题“舆论界牛耳,保守政论家”还算差强人意,第二章“苦撑待变兮,引领望美师”未免让人皱眉,第三章“斯大林狡谲,美国真无邪”则显得不伦不类,只有第四章“自由诚可贵,反共价更高”为这个目录略微挣回了一点面子。
书中很多差错显然是作者过于急躁,书稿没有仔细通读,萝卜快了不洗泥所致。比如,作者似乎特别喜欢“已经”这个词:“胡适对蒋介石一面倒的另外一个例证,就是他已经不但已经对蒋介石称臣,而且他也鼓励他《独立评论》的朋友当蒋介石的幕僚。”(76页)再如,“这时的他不但已经是中国驻美大使,而且也已经参与争取桐油贷款”(317页)。对一部长篇巨作而言,这种失误在所难免,不过没有编辑肯为他承担“责任”了。下面这段话,三个“已经”其实都可删去(严格来说,都应该删去)——这对于“已经”成瘾的作者,要求似乎有点过高了:
到了1930年代大步迈向保守、与蒋介石妥协的胡适,早就已经不是一个透明、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的人了。1946年从美国回到中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他,更已经是一个极其不透明、躲躲藏藏的人了。到了1949年流亡美国以后,他就完全已经成了一个三缄其口的金人、密不透风。(20页)
另外,表达不准确,读起来很别扭,甚至不知所云的句子也时有出现:
他1933年在保定听蒋介石说他没想到日本比他还了解汤玉麟、张学良的兵力以后在日记里所说的话。(150页)
〔1938年〕10月8日,蒋介石在胡适上任第一封给罗斯福的信抵达:……(294页)
前面那句话大概需要查阅胡适日记,才能弄明白。后面这句话其实是想说,蒋介石在胡适就任驻美大使后,立即给他拍了一个电报,要胡适将他的旨意传达给罗斯福总统。可是作者硬要把这几层意思塞在一句话里,“信”和“电报”不分,自然不便于读者理解。
这种字句上的问题,只要稍加斟酌,就可化解。比较严重的是行文牵连夹缠,一个话题一会儿这两页说一下,一会儿隔几页又重复一下。这种恼人的毛病,全书比比皆是。例如,蒋介石在日记中严厉指责胡适的一段话,445页抄了一遍,只隔了十二页,在457页又抄了一遍。另外,《舍我其谁:胡适》前面三部提出的论点,本书经常花不少篇幅重述一遍——有的地方由于论题的关系或有必要,但更多的地方点到为止即可。
由于不分小节(像第三章将近两百页,只有两个小标题),没有更详细的次级标题,加上文章本身也不够清爽,未免加重了读者的负担——归根到底,是作者的不幸。比如,第一章讨论胡适“保守的政治哲学与立场”,可是读罢全文,只记得作者主张“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和“专家政治是研究院的政治”像一副对联,对胡适政治哲学的核心关切和具体内容却很难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这当然要怪读者愚笨,可是作者行文不加节制、疏于总结,恐怕也难辞其咎。再如,这章最后一节“对日策略变、变、变:妥协与抵抗的两难之局”,全文将近八十页,讨论了胡适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到1937年9月赴美之前的对日主张。根据作者的分析,胡适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八次变化,但读者要准确捕捉这“八变”却非易事,因为没有小标题提示,篇末也没有小结。除此之外,这一节开头花了三四页来讨论“太平洋学会”的年会是否要延期的问题,跟胡适的对日策略相距较远,其实可以化繁为简。
第二章的叙述也不尽如人意。作为驻美大使的胡适在外交上具体有哪些得失,书中完全没有总结。比如桐油贷款,一开始明确指出这是陈光甫的功劳(309页),后面又说胡适也有贡献,证据是驻美大使馆秘书说这是胡大使“画龙点睛”的结果(321页)。可是,书中却没有详细的描写。另外,有些地方读起来感觉很突兀。例如,讲述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的经过时,中间突然插入了胡适悼念徐新六的一首诗(287-288页),对作者来说这也许是得意之笔,文似看山不喜平,希望有跌宕起伏的效果,可是读到这里,我总觉得情感一下子顿住了,隔了好一阵才能进入下文。还有,第四节“新官上任就惹祸”,“铺垫”了二十多页之后,才算进入正题。总之,本章的篇幅相当大,读后却无法对胡适在外交上的成绩和教训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外交史的研究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查阅档案,然而由于写作上的弊病,那些付出和努力在相当程度上打了水漂。
第三、四章也有不少问题,恕不一一指出。
说实话,这种种疏忽和毛病,有的可以放过,有的可以理解,有的则让人难以接受。不过人吃五谷杂粮,谁没有局限,谁不会犯错呢。要命的是,作者“舍我其谁”的态度——借用书中的“胡适说过就算主义”,作者的气势全然可以称作“江勇振说了就有道理主义”。
必须指出,这里说《舍我其谁:胡适》在写作上存在比较严重的缺陷,并不是说作者没有写作才华。实际上,本书有若干段落相当扎实,叙述也很精彩。但是,由于作者长期养成的写作习惯,加上急于求成,导致这部传记未能达成比较好的效果,至少呈现出来的不是“读者友善型”的作品。两百三十万字的洋洋大作,换作懂得剪裁、善于整理的学者来写,大概一百万字就可以办到了。八百六十多页的《国师策士》,可能一半的篇幅就绰绰有余了。在关于胡适的论著中,像余英时、罗志田的作品我都读过不止一遍,但像江著这样条理不清、不事剪裁、冗沓夹缠的,甚为少见,叫人徒唤奈何。作者投入巨量的精力,理应完成更上层楼的杰作,却在写作上用力不足,把关不严,殊为可惜。不过对于这些指摘,作者恐怕不会承认,而会怪罪批评者“不懂”“不知学术为何物”。
史坛巨匠钱穆晚年在完成逾百万言的《朱子新学案》之后,自觉该书“牵涉太广,篇幅过巨”,遂写了一篇十万字左右的《提纲》,“撮述书中要旨,并推广及于全部中国学术史”,后单行出版,即为《朱子学提纲》。钱穆在朱子学方面的成绩如何姑置勿论,他的这种写作理念、学术构想,在中文学术界俨然已成绝响。“舍我其谁”的江勇振只会“敝帚自珍”,绝不会有此念想。至少《舍我其谁》四部曲完竣之后,我们没有看到著者提要钩玄,贡献一部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别出心裁的胡适传。
有违学术规范
作者肯定希望自己的胡适传是一部纯粹的学术著作,因此在脚注中列了很多原始文献和一些二手文献。然而萝卜快了不洗泥,书中仍存在一些纰漏。比如第101页正文反驳了罗志田的观点,却没有出注。第309页正文提到何光诚在香港大学的博士论文,但没有给出具体的论文信息。再如,第249、251页脚注中虽列出杨天石论文的篇名和页码,却没有书名和版本信息。这类疏忽可以归结为作者的粗心和急躁。
然而,江著更大的弊端可能隐藏在这些看得见的脚注之外。
读了江著后,我接着读了《胡适与现代中国的理想追求:纪念胡适先生120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下文简称“《追寻》”),深感这次会议对江勇振写作胡适传应有很大的启发,但江著却罕有提及,让人深感困惑。这次研讨会是2011年12月16、17日在台北召开的,江勇振也出席了会议,并作了报告。《追寻》中有多篇论文涉及胡适的后半生,奇怪的是,本书脚注中只提及黄克武的《一位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与〈文星〉杂志》(650、716页)和吕实强的遗稿《浅论胡适的自由思想》(766页)——前者是作为批判的对象,后者是作为史料。那么,其他论文对江著丝毫没有帮助吗?
在阅读《追寻》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几个细节,产生了若干疑问,诉诸笔端,以就教于高明,亦是读书一乐。
其一,与“容忍”有关。
汪荣祖的《当胡适遇到蒋介石:论自由主义的挫折》,是一篇相当精到的论文,可以当作一篇袖珍版“胡适的下半生”来看。该文对胡适的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有所批判。其中提及法国革命家米拉波(弭拉坡):
曾经参与法国大革命的弭拉坡(Comte de Mirabeau,1749-1791)认为任何足以容忍别人的权势之存在,就是对思想自由的侵犯,因为容忍者同时具有不容忍的能力。(《追寻》,45页)
根据脚注,可知这句话出自米拉波的Discours et opinions de Mirabeau(Paris, 1820)第328页。
有趣的是,江著谈及“容忍”时,也引用了意思相同的一句话,不过作者是另一位Mirabeau:
“容忍”这个概念所假定的,是容忍者有权镇压,只是决定不用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国的米拉伯爵士(Marquis de Mirabeau, 1715-1789)会断然地说他要把“容忍”这个字从字典里去除。他的理由是:“只要有那么一个握有权力来容忍的权威存在,就是对思想自由的侵犯,这是因为它既然可以容忍,它也就握有不容忍的权力。”(810页)
根据脚注,这最后一句话转引自Guido de Ruggiero的The History of European Liberalism(Boston: Beacon, 1967)第18页。
笔者不懂法文,限于条件,一时也无法查核英文和法文原著。——难不成这两位年龄相差三十余岁的Mirabeau真的说过同样意思的话?蹊跷的是,江著后出,只字未及汪荣祖的名讳。作者是怎么注意到十八世纪法国的Mirabeau的?书中没有解释,读者自然不明就里。
其二,胡适“China in Distress”系年。
潘光哲在《胡适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回应(1949-1952)》一文最后附了一则简短的考证。胡适“China in Distress”一文的系年,胡适纪念馆定为1952年,周质平认为是“约1952年4月”的作品。经潘光哲考证,该文是胡适1950年2月17日在The Executive’s Club of Chicago讲演的文稿。(《追寻》,260-261页)
江著也提到了这篇演讲稿(586-587页),但只字未提潘氏的考证。当然,江著利用了胡适好友洪贝克(Stanley Hornbeck)的档案,档案中恰好保留了这篇文稿,上面还附有胡适的便条。也许“China in Distress”的系年对江勇振来说丝毫不成问题,独力就能解决。但就学术规范而言,仍应在脚注中提及潘氏的考证。而且有了这个考证,对江著有益无害,为什么会视而不见呢?
其三,胡适反共思想的来源。
在我看来,吴炳守《冷战时期胡适的反共自由主义路线的形成(1941-53)》(《追寻》,282-314页)大约是迄今讨论胡适反共思想最深刻的一篇论文了。该文认为,自由主义可以分为启蒙性的和体制性的(这是我的概括),前者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建设、政治社会的改革,而从西方引进的思想资源,后者则是在冷战形势下,以反共优先,为证明威权体制的正当性,将自由主义扭曲化的一种体制性思维。
该文格外重视胡适的思想体验,尤其关注他1938年以后长居美国一事,认为应全面探讨胡适在抗战、内战、冷战时期的思想经历。作者明确指出了胡适反共思想的美国来源:从1954年3月5日的演讲《从〈到奴役之路〉说起》,可一窥胡适的思想资源及其端倪。这个演讲提到了哈耶克(F. A. Hayek)、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以及美国保守主义杂志《自由人》(Freeman)。哈耶克和米塞斯的思想在1930年代末开始通过伊斯特曼(Max Eastman)等人频繁介绍到美国,战后则通过《纽约时报》《自由人》《国家评论》《读者文摘》等媒体盛行于美国。
作者认为,哈耶克是胡适反共自由主义的原典,其根据是1941年7月8日的演讲《意识形态的冲突》(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这篇演讲稿还引用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0年11月和1941年1月发表的两次演讲,以及伊斯特曼的极权主义理论。作者还指出,胡适对罗斯福理论的全盘接受,是因为他早已具备接受美式自由主义并将其信念化的心理机制。其缘由是,胡适在留学时期就青睐威尔逊主义,而罗斯福通过介入二战,重建战后秩序,将威尔逊主义化为现实,合乎威尔逊主义者胡适的期望。因此,胡适对战后世界秩序的想象,也就是在美国领导下建立一个抑制战争的集体安全保障体制。
由于反共优先的策略,胡适对储安平创办的《观察》杂志冷眼相待,对关系较为亲近的周鲠生的国际观也提出了批判。而且,胡适在抗战后始终反对知识分子的在野党运动。胡适认为,为了有效推进反共活动,自由主义势力必须团结合一。所以他对张君劢、蒋廷黻等人组织反对党均持批判态度:在反共斗争中不可能存在第三势力。
从以上粗略的介绍可知,江著中有关胡适反共的内容,吴炳守这篇论文差不多都涉及了,尽管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看法不同。比如,吴氏认为哈耶克对胡适反共自由主义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追寻》,298页),而作者认为胡适的“新保守主义”(大体相当于吴氏的“反共自由主义”)并不来源于哈耶克(672页)。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江著中只字未及吴氏这篇见解深邃、视野开阔的论文。更不可思议的是,江、吴两人都参加了在台北举行的纪念胡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学术会议,而且论文收在同一个论文集里,在正常的情况下,江勇振没有理由不清楚吴氏的论文。
当然,江著也未提及周质平《胡适的反共思想》一文(载《国史浮海开新录:余英时教授荣退论文集》,联经出版公司,2002年)。对于周氏此文,作者显然是心存不满的,书中关于胡适1945年8月24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件的解读(511-512页),就是针对周氏(及其他学者)而发的。周质平此文可议之处甚多,但这个论题是他首先探讨的,而且很长时间内后无来者。即使看不上这篇论文,也应该在脚注中提一笔的——有可能从中受到“反面启发”。
顺便说一句,1950年代大陆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肯定刺激了胡适的反共思想。上述潘光哲和吴炳守的论文(后者提了一笔),应该可以提供灵感和线索的,不知为什么江著却轻忽了。
我甚至觉得,江著其实是将吴炳守的“反共自由主义”的概念化为己有,改称“新保守主义”,以大量史料加以充实、证明——最后这一点是江著的真正贡献所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江著充分利用了吴炳守的概念,堪称汪荣祖论文的超级增订版——将汪文中强调自由主义的内容改成了胡适与蒋介石“暗通款曲”“精诚合作”,以及胡适晚年“崩盘式的暴退”。
无论如何,江著这种作法不足为训。对学术著作(包括学术性传记)来说,在脚注(或尾注)中标明参考文献、思路来源,是学术诚实、也是学术自信的一种体现。有了这样的注释,可以增加学术专著的分量,反之则显得“轻薄”,让人不由得怀疑其学术诚信。即使真有贡献,也不方便学术共同体检证。譬如,江著对胡适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比较详细的描写,其中将《群众周刊》与《申报》的报道相对照(527-529页),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胡适的面目。不过由于学术规范上的疑问,孤陋如笔者无从判定《群众周刊》那则材料是作者自己爬梳报刊所得,还是看了二手文献转引而来。
当然,笔者并不想以学术失范来否定江著的学术贡献。只是,学术失范和写作缺陷无疑使这部著作的价值大打折扣,洵属遗憾。
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善,胡适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不过,在这期间“胡适神话”也是层出不穷,腾于众口,“胡适=自由主义者”的公式化、脸谱化“常识”满天飞,本来是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结果却出现了无数木雕泥塑的胡适神像。有形无形之间,我们的文化界还弥漫着这样一种气氛:批判胡适,就是反对自由民主;推崇胡适,就是反抗独裁专制。这种截然的二分法,在思想上是相当幼稚的。殊不知,在学术上批判胡适,也可以是为了追求自由民主。
从这个角度说,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四部曲,尤其是《国师策士》一书,在摧毁“胡适神话”上“重拳出击”,对今人走出“胡适崇拜”的怪圈大有裨益,居功甚伟。然而,如本文开篇所述,该书出版至今,学术界尚无一篇书评,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想想中国大陆有多少胡适的“粉丝”)。不过稍作分析,即可了然。这种沉默,大概可以分三种情况:其一,对沉浸于“胡适神话”的人来说,江著犹如眼中钉、肉中刺,沉默对维护胡适的光辉形象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其二,由于江著在学术规范上的问题,学界同道耻于提及,不想拉下脸皮,故沉默以对。其三,这种沉默也要“归功于”江勇振自己。他写的胡适传,篇幅长得让人望而生畏,难以卒读,加上他对待批评的态度(参阅《舍我其谁:胡适》第三部的前言)——在他眼里,几乎所有批评者都是懵懂无知的,睥睨同侪、轻蔑读者——大家自然避而远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作者毕竟在胡适研究领域摸爬滚打了数十年,就像其缺点不容粉饰一样,其贡献也不容抹杀。对于胡适的后半生,我一直期望深入了解,本书可争辩、可批判的地方很多,虽难称杰作,但静心细读,确有所获。
(承京都大学彭皓兄帮忙从京大图书馆借出《国师策士》一书,特此致谢。另,拙稿承一位“深藏功名”的朋友批评,谨致谢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