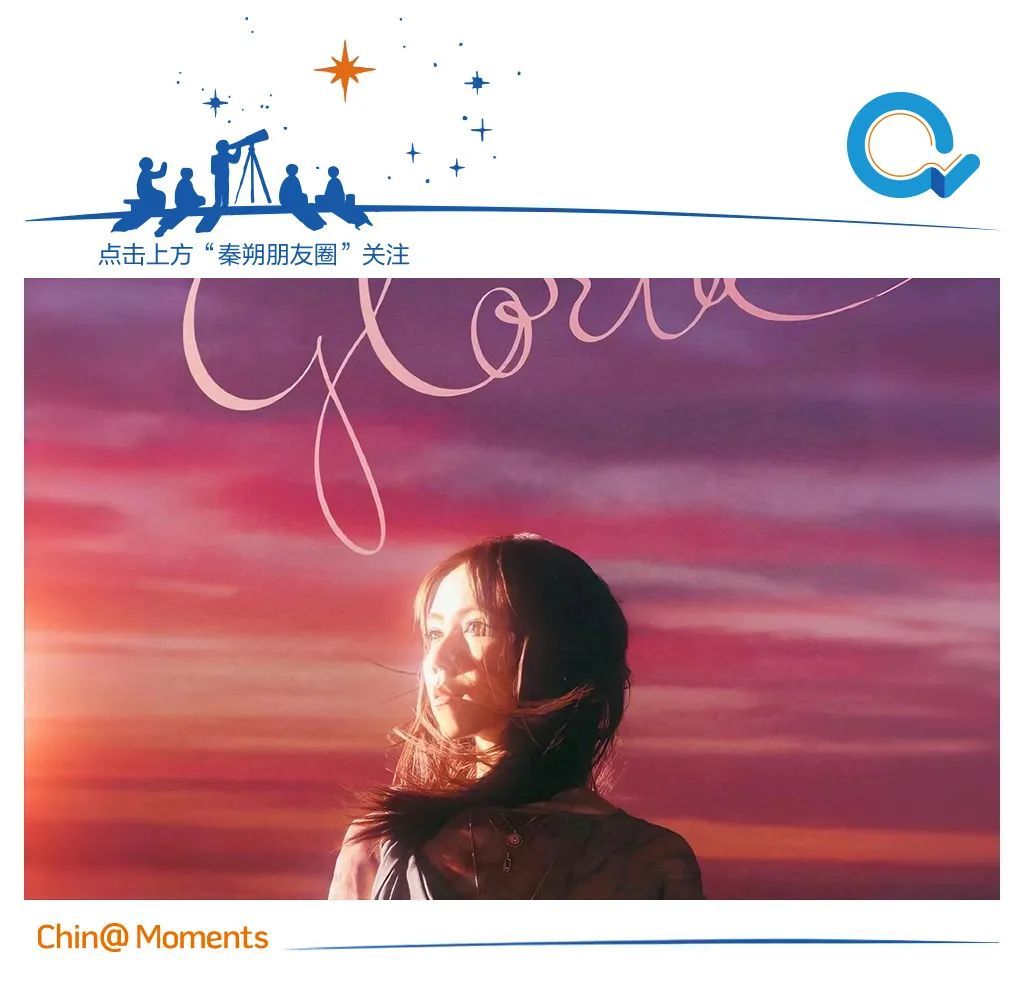
邓紫棋发布科幻新书《启示路》,第一天就卖了20万册,据说GMV达到4000万+。让我等一众职业作家尴尬汗颜——原来取代你的不是AI,是明星和网红。
意大利文里有一个词,叫“diletto”,意思是“愉悦”,后来引申成“跨界的业余者”,就是那种能从任何工作中获得愉悦的人。像邓紫棋这样,提前一步获得社会认可和能量的人,做成了这样的人,未来可能每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潜能开发力吧。
为什么要观察这些公众人物的动向,因为他们是社会财富和心理的显化。最近,好多有头有脸的人都下场带货(连高冷的韩雪都在带货),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农耕社会的集市”,原来村口有的八卦和菜,现在悉数搬到了网上、云上。人人都产自己的品,带自己的货……
这网络仿佛只剩下了豪门的瓜,娱乐的果。我也只能在写热点人物的时候,夹带私货,我们普通凡人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少,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的定力得越来越强。
不过,我个人是乐见有人能够突破自己的维度发展出新的可能性的,一个文艺创作者一通百通,作词作曲编剧小说写字画画什么都能信手拈来,是真本事,本就符合我们国度里“百科全书派”的传统。
“琴棋书画戏诗酒花茶香”,生活方式就是创作方式,古代男人拥有的精神世界,现代女性可以生出新姿态、新样本来,倒也是可喜的。
我对邓紫棋,印象最深刻的话是:“每天都有人跟我撒谎,以为是家人的在欺骗你,以为是兄弟的在利用你,不经历风浪的关系是不牢固的,一切关系都需要用时间验证”“庆幸自己经历过低谷,才懂得如何用音乐安慰别人”……
这个时代,她有疗愈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其实,一个人确实要先让自己有光芒,无论如何绽放自己,“辉辉朗耀,炳炳照临”,但只有经历过“存亡俱泰”,才能“力济无穷”。这个世界不仅仅只有斗争和交易,还有抚慰和寄托人心的人事物情境。
她曾经找不到意义,15岁签约经纪人和公司,别人给她灌输的理念是,“你离开我们就什么都不是”“你只是我们打造的商品”“只有一直好和成功,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在这个商业社会里,被物化是必然的,突破物化和异化则是偶然的。
人要挣脱别人和自己的“意识”和“潜意识”何其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有智慧也过不好这一生,因为智慧之人都会远离是非对错纷繁复杂,而在人际关系的局中,自己是很难看清楚的,自缘身在此山中。自以为英明的人,反而是谁都劝不了的人。
男人觉而不醒,女人醒而不觉。在某个巨大的意识困境面前,比如感情和事业的挫折和考验之下,女人会突然醒来,发现自己很茫然。人间清醒是相对容易的,但觉醒很难。因为觉醒,是掌握生命的主动权。
所以,这才有了她后面的叙事,当她的名字、她的音乐,都可能不再属于她的时候,她必须蜕一层皮,甚至重构血肉——“我的人生的故事就是见证,我真的见过光,所以我只想把光反射出去。”
经历过重大考验的人,才有厚度,不然都是扯淡。
纵观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女孩的十三四岁很重要。
比如,宗馥莉在美国留学,监护人是杜建英,她的情感的考验应是巨大的,内心的小老虎就这样养起来了;比如孟晚舟12岁后父亲去深圳创业,她在贵州都匀果乡村生活,抓蚱蜢、挖野菜,所以后来她能坚韧吃苦、平和自然;比如邓紫棋,她13岁有个作家梦,14岁觉得自己很酷,参加了香港作词作曲协会,她都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干什么,导致自己关在房间里的作品著作权不属于她自己。
我发现每个人的作家梦其实都生于13岁附近。比如J.K. 罗琳11岁写了第一部小说《兔子》,13岁立志写故事谋生,如今《哈利·波特》系列全球销量超过5亿册;村上春树13岁左右沉迷欧美文学和爵士乐,开始尝试写短文;阿加莎·克里斯蒂童年就热爱写故事,13岁时已尝试创作短篇小说;甚至连玛丽·雪莱,科幻文学之母,也是十几岁参加文学沙龙,21岁创作《弗兰肯斯坦》开创科幻小说先河。我自己也是13岁,开始沉浸在庄子的世界里,想做遗世独立的哲学家。
后来,她重录儿时的那些歌的时候,她知道自己已经很强大了。天无绝人之路,她用法律确认了自己歌曲作品的传播权。
很多年来,经纪公司给她洗脑——她只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商品,没有他们她就会死。她害怕,恐惧,也认为自己除了音乐什么都不行,这种惧怕像山一样压着她。其实这不是移山就行的,是需要在思维上飞起来。
你看如今,她重新拥抱了掌控权的自由。控制权、被认可、安全感,是所有人的精神世界里绕不过去的底层需求。
如今的她,做了多元的尝试,现在连科幻小说都写完了,让自己长出很多羽翼,才能化解掉内心里存在了很多年的阴影。
对,那是“化解”,离“解决”和“解脱”还很远。但一步步地去“觉”和“化”的本身很重要。
她觉得:“上天不会给你你承受不了的挑战,虽然内心很强大了,但还是有过不去的事情,只不过站起来的速度比以前快了。强大是站起的速度。”
她化成:“无论辉煌还是落魄,只是一瞬间,跨过这一瞬间有的是未来”“人生最重要的是爱,带着爱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它就会变得有意义。”对抗虚无主义,只能靠内心里的一步步的“化”。
从她边学习边写小说的创作路数来看,她化解的方法多了很多层次感。原来她是靠灵感写歌曲。比如《泡沫》是最惨痛的分手经历之后,她去纽约街头散心,看见小丑吹的泡泡,觉得自己为什么已经不能像街上的人那样快乐。回到酒店就开始写歌。
而现在的科幻创作,是靠时空的惯性,她甚至说,这不是创作,这就是研究实质。她说她学习了很多AI,元宇宙,暗物质,暗能量,黑洞之后,她不是在创作,而是真的这么认为的、定义的。这种惯性就是对场域的觉知,一切都是流出来的,而不是编出来的。
对于我们地球人而言,实际上时间都是有共识的,但是空间不一样,遇到的人事物情境都不一样。语言只能表达7%,55%左右都是场域决定的。比如孔子说登泰山时的“一览众山小”,是指那个场域给了他无穷无尽的对于宇宙、人生的启发,而不是山的绝对高度和表象。
为什么这个人会遇到那个人,其实都是对于场域的共识。对,她想控场,且已经能控场。
她的I AM GLORIA巡演,以4.24亿美元(30.4亿人民币)的票房,成功超越麦当娜的Sticky & Sweet Tou,成为全球史上票房第4高的女性艺人巡演。
Gloria也是她小说里面的虚拟主角名字。《启示路》讲述的故事构建了三重世界结构元宇宙中的“乐土”与“废土”,以及真实世界。虚拟角色Gloria与现实中名为秋的女孩,在两个世界中各自挣扎、彼此照映。她们经历了身份的寻找与撕裂,也经历了情感的失落与重建。
她全面地建构了自己的场。所谓“龙在田”,始终保持初心在场,是让自己的内在能量和外在机遇相逢的最好的方式。我们也应该如此,通过自己的内核觉醒,在各种场域里布置自己的天赋和角色。
她建立“觉醒三部曲”式结构表达:
1、迷失阶段。主要体现情感与身份危机。代表作为《泡沫》《你把我灌醉》《好想好想你》。
2、挣扎阶段。开始觉察并寻找出路。《光年之外》《来自天堂的魔鬼》《画》。
3、觉醒阶段。找到自我,重构信念。《倒数》《差不多姑娘》《Gloria》。
她的知识结构基础,大致是:
音乐+情感+语言=表达底层;
心理+信仰+冲突=哲思中轴;
美学+技术+视觉隐喻=输出工具。
她的创作核心思想,大致是:
意识觉醒是人生最重要的课题;
时间、记忆、情感是灵魂的入口;
真实表达是唯一可穿越维度的载体;
未来主义与伤痛本质并不冲突,而是互相成全。
她的音乐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就是“宇宙与内心”。可能这个命题无论古今中外,精神维度高的人,都会去想。
《光年之外》是借外星人爱情寓言,描绘失落与自救;
《另一个童话》重构爱情为系统崩坏下的数据投射;
《回忆的沙漏》MV以多重时间线折叠来表现失控与轮回;
《Full Stop》隐含“清除过去程序重启自我”的自剖;
《Gloria》系列则是最具“概念小说化”的视觉哲学作品。
她说,三思而后行,代表你愿意去承受代价。承受早年父母离异原生家庭的代价,承受人际关系破裂,安全感需要自己步步营建的代价。
其实,人的内核比较原始自然的话,能够变出来的花样和玩法更多。
她说“人生没有找到意义,就会不满足。我只要每一天还在做有意义的事情,就已经很好,就不会空虚。”她说,她希望自己是世界的一些新鲜血液,能够推进一点什么。
她对AI也有自己的感知——AI能无止境地扩大人的欲望,而人类的优势在于人文情感——感知、体验、成长、痛苦,基于这些,慢慢地发展出不同的可能性。
AI是中立的,都是工具,取决于用它的人。科技时代的“自我认知”和“爱的本质”,她企图用量子力学、神学和哲学去融合。她33岁,这个境界不错了。
其实,中国人自带自我启示的基因。在中国传统哲学语境里,人能够通过几种方式获得启示。
第一,心智的启蒙,有良师益友帮助我们破除迷茫,虚心受教,主动探求才能获得真知(“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放下偏见成见,接纳指引,在积累中逐步开悟。
第二,观察与洞察。通过静观自然规律、社会现象,领悟宇宙运行的法则,“观其生”,内观自省达到通透澄明的境界。我们始终要保持客观与敬畏,把自己的视野放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都会自动渺小。
第三,迷雾消散,心智清明。困惑的消散,如狂风驱散迷雾,突然看清真相,危机中借风力化解僵局,豁然开朗。在动荡中保持冷静,让纷乱自然沉淀,真相自现。
第四,迷途知返,回归本心。在错误或迷失后,通过自省发现初心。接纳失败,在反思中获得方向,顿悟常生于绝处,所谓绝处逢生。
可惜,很多人都在乎一时成败,忘了人生,身前身后名都太重了,不如安静平和地对待成败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