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职责,我们的使命,不是奴役,而是解放;我大可不带着任何自夸或不冒犯任何人地宣称,我们正立于道德、社会与政治文明的顶点。我们的任务是引领并指导其他民族前进。
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后来成为首相的巴麦尊子爵(Palmerston)在1848年曾以如上这般近乎傲慢的口气吹嘘着不列颠的使命。尽管并非所有国家都愿意接受这份傲慢,但1848年的英帝国确实如同“初夏的太阳”一般,自信地展现着对于世界的统治力。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大英帝国及其主宰下的19世纪确实在各个方面塑造了我们今日的世界。通过阅读英帝国的历史,观察它犹如四季的生命周期,我们得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发现连接的桥梁。而在其中,我们既能发现最高尚的解放事业,也能见证最卑劣的奴役与谎言。
关于英帝国史的研究开始于英国史学家西利(J. R. Seeley)。他于1883年出版的《不列颠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Macmillan and CO., 1883)为后世的英帝国研究开创了诸多经久不衰的母题。不过让他这本书为一般人所铭记的却是他那句著名的论断,即英帝国是在“漫不经心中征服了半个世界”(have conquered and peopled half the world in a fit of absence of mind)。这种英式“低调陈述”(understatement)或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让人们几乎忘记了英帝国本身是充满血与火的军事征服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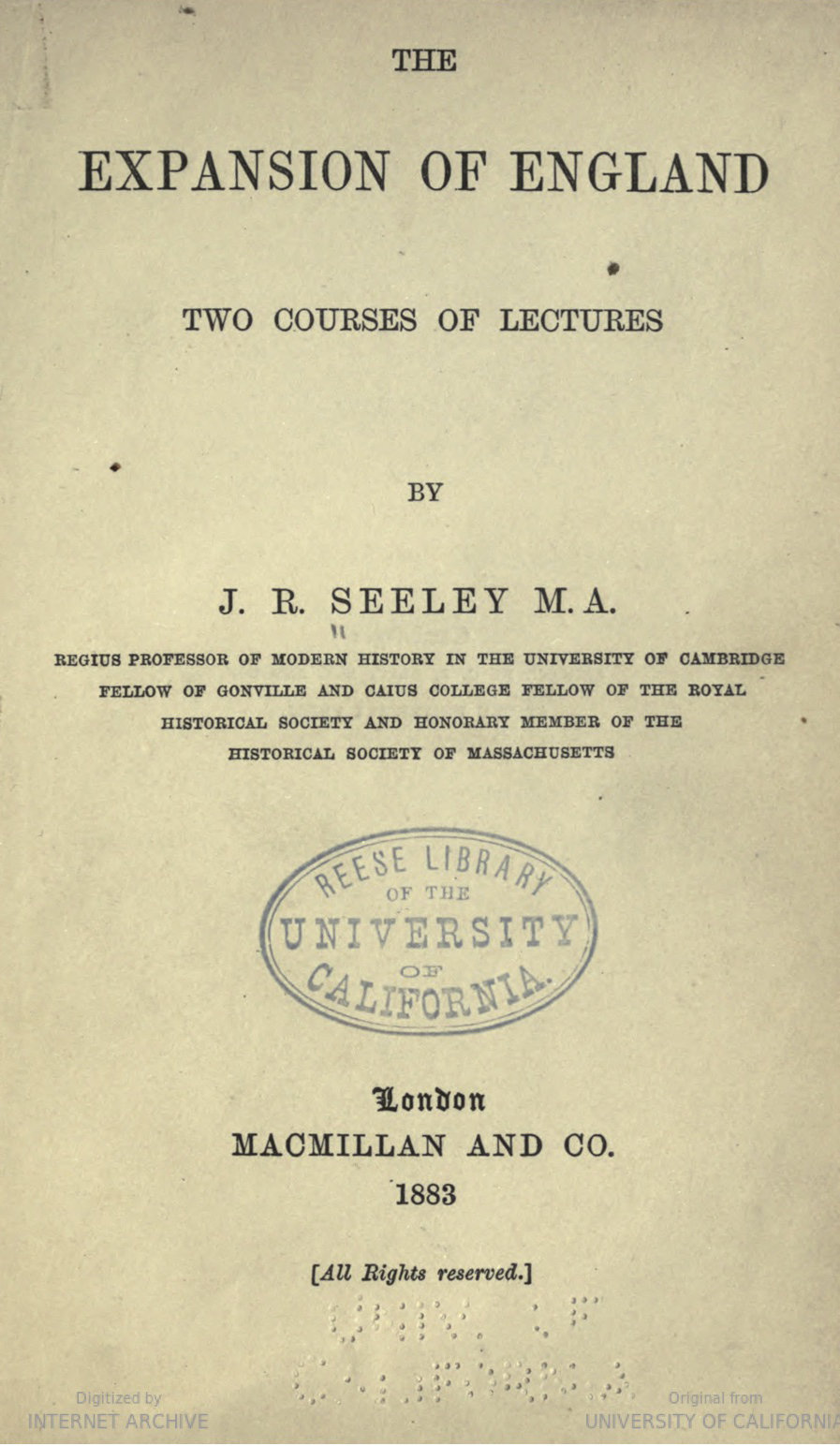
当人们讨论“不列颠统治海洋”时,自然会把荣光归于帝国建立的首要功臣:皇家海军。本·威尔逊的《深蓝帝国:英国海军的兴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就以史诗般的语言,描绘了英国海军自创立之初以来参与的所有战争。不过《深蓝帝国》时间跨度很长,若要集中了解皇家海军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即17-19世纪初的风帆战舰时代,那么安德鲁·兰伯特的《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无疑是相当好的入门研究。兰伯特在书中详细讨论了这一时期欧洲各国海军的组织与后勤、战术战略以及不列颠海军力压群雄最终得以统治海洋的过程。当然皇家海军也不是未尝败绩,至少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失败使得当时的许多人指责英国海军的糟糕表现。克里夫·威尔金森(Clive Wilkinson)就借用这一指责为引子,在《英国海军与18世纪的国家》(The British Navy and the Stat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oydell Press, 2004)一书中探讨皇家海军与英政府的关系、财政的运转模式与帆船时代海军所面临的技术难题。威尔金森指出,造船木料的朽烂周期(decay cycle)使七年战争期间所造的军舰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正好都处于不良状态。突如其来的战争不仅打破了时任海军大臣三明治伯爵(对,他就是发明了三明治的人)的改革计划,还让他背上了战争失败的黑锅。可见时运不济的改革者在古今中外都有类似的命运。美国在独立之后继承了英帝国的海权思想,彼得·卡斯藤的《海军贵族:安纳波利斯的黄金时期及现代美国海军至上主义的出现》(海潮出版社,2011)向我们介绍了19世纪美国海军军官的培养模式与军官集团所持的意识形态。卡斯滕在结论中提醒我们,美国的海权思想并非马汉一人的创造,而是海军的集体意识,美国海军凭借自己强大却不威胁国内民主(这主要是相对于可能威胁民主的陆军而言的)的形象将自己推销给国家,与此同时却在海外肆意践踏其他国家人民的权利。就这一点而言,英美海军的霸权确实是一脉相承的。
以英帝国为代表的欧洲对于其他地区的征服,如卡尔·施米特在《大地的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中指出的那样,实现了“秩序与场域的结构导向性汇合”,以欧洲为中心所划分的法权之外,暴力便肆无忌惮地使用,即所谓“一条经线决定了真理”。施米特在刺破政治虚伪时从不手软,比如他在《政治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中就毫不讳言地指出“政治的本质就是划分敌友”,而在另一本作品《论断与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中则进一步指出“英国海战具有整体性是从它有能力激发整体敌意的意义上而言的。它像动员某一种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战争方式一样,善于动员宗教的和世界观的、心灵的和道义的力量”。
或许正是这样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才让不列颠如伯纳德·波特(Bernard Porter)的书名所比喻的那样,咬下了“最大的一份”。《最大的一份:英帝国主义简史》(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2004,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4)相当全面且扼要地介绍英帝国19世纪扩张与20世纪的衰退。如果你觉得类似《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这样质量尚可的通俗作品已经不能满足时,那么波特的这本书就非常合适,尤其是对于那些初入该领域,想要积累专业词汇的本科生而言。但如果要进一步理解英帝国的扩张机理与性质,那么伦纳德·海厄姆(Ronald Hyam)的《理解英帝国》(Understanding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则是难度更高但更值得推荐的作品。海厄姆作为最负盛名的英帝国史研究学者之一,在讨论英帝国时观点独到有趣,尤其是他对于边陲“在场人员”与中央决策机构互动模式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英帝国扩张的内在机制。
上述的几本书都是关于英帝国的整体性研究。若要进一步深入的话,就必须分领域专题讨论。西利之后英帝国史研究的第一代学者集中讨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动力。霍布森(J. A. Hobson)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A Study, James Pott & Company, 1902)无疑是帝国主义经济学解释的开创性作品,对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霍布森看来,帝国主义最大的价值就在于输出国内过剩的资本,贸易与工业资本反倒不是帝国主义的主要动力。霍布森的观点在凯因和霍普金(P. J. Cain, and A. G. Hopkins)的《不列颠帝国主义,1688-2015》(British Imperialism, 1688-2015, Routledge, 2016)中被进一步理论化,并将资本输出的主体定义为土地贵族和伦敦金融城联盟而成的“绅士资本主义”。这一传统而保守的力量,而非“进步的”工业资本,才真正掌握着19世纪英帝国的命脉,进而主宰世界。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激进的帝国扩张是如何与维多利亚时期的保守主义紧密结合的。
这种保守主义的典型就是英国首相迪斯雷利与索尔茨伯里。二人的传记,詹金斯(T. A. Jenkins)的《迪斯雷利与维多利亚保守主义》(Disraeli and Victorian Conservatism,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与迈克尔·宾利(Michael Bentley)的《索尔茨伯里的世界》(Conservative Environments in Late-Victorian Brita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保守主义者与帝国之间的关联。艾尔德里奇(C. C. Eldridge)在《英格兰的使命》(England’s Mission: The Imperial Idea in the Age of Gladstone and Disraeli 1868-1880, The Macmillan Press, 1973)中进一步论证了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与自由党党魁格莱斯顿之间看似分歧的政策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支持着帝国主义,迪斯雷利关注的是为帝国带来更大的荣耀以维系一般大众的支持,甚至不惜为维多利亚女王戴上名不副实的印度皇冠;而格莱斯顿则更重视帝国本身的成本与收益,试图以更为有效的方式管控日益庞大的帝国。格莱斯顿对于财政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18世纪欧洲的财政-军事国家》(The Fiscal-Military State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Ashgate, 2009)的诸多文章分析指出,英国正是通过强大的财政能力才最终在百年竞争中击败法国。相比之下黄艳红的《法国旧制度末期的税收、特权和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与威廉·多伊尔,《捐官制度:十八世纪法国的卖官鬻爵》(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就十分细致地解释了法国专制王权下财政的脆弱性。英国的代议制民主与公开的财政预决算制度增强了信心与稳定性,而依赖强制人头税与卖官鬻爵的专制主义法国则难以在困难时期重建债权人的信心,进而获得低息贷款。因此,信任是比强制更为有效的整合资源的力量,斯塔萨维奇在《公债与民主国家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中所做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帝国主义扩张的“经济决定论”在二战后就失去市场。本杰明·科恩(Benjamin J. Cohen)的《帝国主义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Imperia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nce and Dependenc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4)中详细的学术回顾可以说为战前较为单一的帝国主义研究范式盖上了棺盖,之后的帝国主义研究开始向更为多元的角度发展。首先是与技术与物质文明相关的帝国史研究,奇波拉(Carlo M. Cipolla)的《枪炮、帆船与帝国》(Guns, Sails and Empir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Early Phases of European Expansion, 1400-1700, Minerva Press, 1965)与亨德里克(Daniel R. Headrick)的《帝国的工具》(The Tools of Empire: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都是从技术史角度理解帝国主义的入门佳作,结合威廉·麦克尼尔的《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学林出版社,1996)我们就能深刻地领悟军事技术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物质文明史方面,布罗代尔在恢弘的三卷本《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中,为我们打开了近代早期世界衣食住行与日常生活的多彩画卷。布罗代尔常常用富有灵魂的评论,把原本枯燥的物质史描绘得生动活泼。例如他在谈及技术与社会的变化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时,打趣地举例说“眼镜的普及并不能让十五世纪的读书人变多,并助益文艺复兴,如果要继续这些笑话,还可以说室内照明的普及为读书赢得了多少时间!但问题在于阅读和求知的激情到底源自何处。事实上在眼镜风靡之前的彼得拉克时代,不照样有人研究古代手稿吗?”寥寥数语便凸显了技术背后的思想动因才是让技术得以发挥其社会效用的根本原因,读之令人莞尔同时引发深思。
就物质文明史而言,几乎任何商品都可以构成一种诠释角度。莉齐·克林汉姆的《饥饿帝国:食物塑造现代世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与西敏司的《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商务印书馆,2010)就是从食品生产的角度讨论全球化的经典作品。埃里克·多林的《皮毛、财富和帝国:美国皮毛交易史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则追寻了毛皮贸易与北美的社会-环境变迁。
斯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更是探讨了“战争资本主义”所打造的全球网络如何让原本在棉花生产领域微不足道的欧洲,却能在棉纺织业的引领下走向工业革命之路。英国的棉纺织业的繁荣看似源自于曼彻斯特彻夜轰鸣的机器,但实际上却高度依赖于美国南方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资本主义不仅需要自由劳动力,也需要奴隶。正如贝克特所言:“奴隶制弥补了机械化制造业的需要和前现代农业所能提供的供给之间的鸿沟。”奴隶制与其他所有同资本原始积累相伴而生的强制劳动一样,如同剪刀一般刺穿传统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并防止人们在雇佣劳动体系之外找到其他生存策略。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强制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迈克尔·佩罗曼的《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得到了充分的阐释。事实上,强制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低效。福格尔与恩格尔曼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作品《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就利用计量史学理论,雄辩地论证了庄园奴隶制时代的南方经济实际上具有高度的秩序与效率,同时黑奴的生活水准也不见得比一般自由劳工要低。反倒是内战后重建时代的美国,废除了奴隶制的枷锁却同时增强了种族歧视的矛盾。当然,这本书完全回避了奴隶制本身的道德缺陷,并且本书的结论意味着进步主义并不必然带来物质上的优越性,但剥去了功利主义外壳的进步主义反而证明了废奴主义在道德上的纯粹性。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经济决定论”过时之后还带来了帝国主义政治史的复兴。罗宾逊与加拉汉(Ronald Robinson and John Gallagher)在提出了标志性的“非正式帝国”理论后,在《非洲与维多利亚时代帝国主义的官僚思维》(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1)中进一步用“官僚思维”这一概念分析了出于战略与国家安全的官僚考量如何决定了在经济上看似无利可图的瓜分非洲运动。瓜分非洲运动意味着麦金泰尔(W. David McIntyre)在《帝国的热带边疆》(The Imperial Frontier in the Tropics, 1865-75, Palgrave Macmillan, 1967)一书中所讨论的英帝国诸多间接控制亚非的手段正逐渐失效。导致这一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欧洲内部的平衡被德国的崛起所打破。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名字稍显野鸡,但内容充实而有趣的《不含传说的普鲁士》(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与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更为详细且偏重于社会史的《钢铁帝国:普鲁士的兴衰》(中信出版社,2018)都是关于普鲁士从边陲小国走向中欧巨无霸的历史过程的佳作。德意志的统一使其摆脱了徐健在《“往东方去”:16-18世纪德意志与东方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中所描绘的那种德意志商人在国际贸易与殖民中的附属地位,而直接参与到了“阳光下的地盘”的争夺中。除了咄咄逼人的德国,英帝国也在同法国的长期缠斗中发展出了一种“亦敌亦友”(frenemies)的关系,竞争的同时,在面对共同的殖民地民族主义敌人时精诚合作。詹姆斯·费克特(James R. Fichter)主编的论文集《英法在非洲、亚洲与中东的殖民主义》(British and French Colonialism in Africa, Asia and Middle East: Connected Empires across the Eigh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Palgrave Macmillan, 2019)用大量案例说明了这种相互关联的帝国主义体系。
新的帝国史研究还出现了文化、社会与思想史的转向。帝国史中的性别议题是特别有趣的案例。辛哈(Mrinalini Sinha)的《殖民地阳刚性》(Colonial Masculinity: The ‘Manly Englishman’ and the ‘Effeminate Bengali’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就从性别主义的视角来探讨英帝国在印度的殖民政治文化。这本书关注的是英属孟加拉社会中为英国殖民当局服务的本土公务员“巴布”(Babu,类似于英语中的“Sir”)尽管巴布对于英国的统治不可或缺,但却也因为缺乏欧洲人眼中的“男性气概”而背负了“娘炮”的污名。因此英侨社群,尤其是女性,激烈地抵制巴布被赋予针对欧洲人的执法权,担忧这些“娘炮”孟加拉人会摧毁欧洲人统治所必须的阳刚气质。在性与帝国的问题上,英帝国处处浸透着虚伪与双重标准。海厄姆(Ronald Hyam)在《帝国与性》(Empire and Sexuality: The British Experienc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中就讽刺英帝国一面向世界输出维多利亚时代最为保守刻板的家庭伦理,另一方面却又在全世界建立起最完善的妓院网络,为驻扎在各处的英军服务,传播着骇人听闻的疾病。的确,英帝国主导下的19世纪全球化加速了商品的流通,也加速了疫病的传播,但同时亦促进了卫生、人种理念的普及。张仲民的《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坂元ひろ子的《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人種·身体·ジェンダー》(岩波書店,2004)以及克里斯托弗·劳伦斯(Christopher Lawrence)的《医疗与现代英国的诞生》(Medicine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Britain, 1700-1920, Routledge, 1994)都是关于这一问题的有趣研究。
英国人时刻注意着自身的阳刚与统治气质的构建,哪怕是生活的细枝末节处也是如此。比如麦肯齐(John M. MacKenzie)的《自然的帝国》(The Empire of Nature: Hunting, Conservation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从狩猎运动出发讨论了殖民者男性气质的构建。拉马穆尔蒂(Anandi Ramamurthy)的《帝国说客》(Imperial Persuaders: Image of Africa and Asia in British Advertising,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别出心裁地从殖民地产品的广告中解读英帝国自我形象的建立,例如用肥皂将黑人“清洁”为白人的隐喻,在茶叶中寻找东方主义,以及烟草所代表的男性气质。康纳汀(David Cannadine)的《装饰主义》(Ornamentalism: How the British Saw their Empire, Penguin Book, 2002)与麦肯齐的另一部作品《宣传与帝国》(Propaganda and Empire: the Manipulation of British Public Opinion, 1880-1960,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用英国与殖民地举办的庆典,及其背后的君主制与贵族体系所发挥的作用来凸显英帝国统治的“软实力”甚至音乐都可以成为帝国主义史的研究对象,杰弗里·理查德(Jeffery Richards)的《帝国主义与音乐》(Imperialism and Music: Britain, 1876-1953,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介绍了诸如《统治吧!不列颠》这样带有帝国主义气息的歌曲的前世今生。这些例子都表明,帝国主义的权力并不仅仅表现为宏观上的国际政治与战争,还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不起眼的角落中悄然塑造了我们的生活。
尽管大英帝国如此深刻地型塑了我们如今这个世界,帝国本身却逃不过如四季般的生命周期。当历史走入20世纪,英帝国“往昔的光荣”似乎如诗人吉卜林在《退场诗》中所预言的那样,“都被归入尼尼微和推罗的行列”。戴维·吉尔摩的《漫长的谢幕:吉卜林的帝国生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为我们描绘了这位最负盛名的帝国主义诗人戏剧性的一生。但若要说哪一位英国人最深刻地体验了英帝国从如日中天到明日黄花的过程,那无疑就是丘吉尔。坎蒂丝·米勒德在《帝国英雄:布尔战争、绝命出逃与青年丘吉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中为我们呈现了少年丘吉尔参与阿富汗和布尔战争的传奇经历。而正是在布尔战争中,英帝国的颓势第一次为世界所知。甚至远在中国的政治家们都感受到了大不列颠已经不再是那个战无不胜的国家了。马丁·威纳的《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试图从文化角度理解英帝国的衰败。他认为英国文化除了带有“清教、工业城市”特质的“北方隐喻”外,始终存在着与之相抗衡的“国教、乡村非工业”特质的“南方隐喻”。这种“南方隐喻”始终质疑资本主义与工业化对于效率与扩张的无尽追求,其保守性既滋养着保守主义者,也浸润着左翼,进而使英国的工业革命走向停滞,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可以看作是“驯化了工业文明”。
去殖民后的英国社会代际间的撕裂在《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这份研究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意识形态上的无所适从导致了无政府主义的复兴,斯科特在《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用极为生动的小故事诠释了无政府主义的合理性与挑战。格雷伯的《毫无意义的工作》(中信出版社,2022)则怒斥现代社会中所产生的“狗屁工作”对人类精神的摧残,以及这个社会不尊重热爱反而奖励痛苦的病态价值观。若对比何柔宛在《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中用人类学的笔法所描绘的华尔街最疯狂的贪婪,以及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新星出版社,2019)中忧虑的人与工作的全面异化,我们或许就能明白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抵抗策略的意义。
英帝国虽然现在早已解散,但帝国给世界留下的遗产却历历在目。许多人批判帝国主义,不过是因为自己尚不够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而已,就如同埃斯吉尔森(Robert Eskildsen)在《日本与东亚的帝国转型》(Transforming Empire in Japan and East Asia: The Taiwan Expedition and the Birth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19)所告诫的,日本正是在抵抗与模仿帝国主义的过程中自己成为了新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帝国的教训是深刻且有益的,去殖民后的帝国犹如冬日落尽了树叶的树干一般,但去殖民过程中已然化为“春泥”的“叶片”,又是否会成为新帝国破土而出的养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