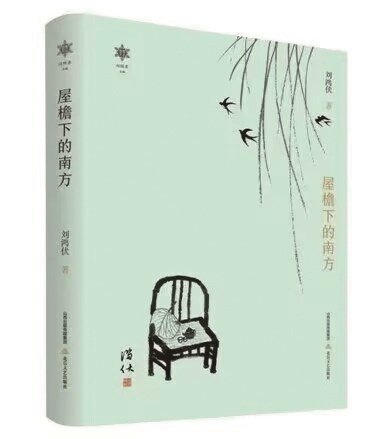
文/刘鸿伏
近年来写作得不多。有行政工作忙的原因,有新冠疫情对心情的影响,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作为一名非专业作家,我的时间不由我掌控,包括节假日或周末,剩下的,还有家人要照顾。我拾掇起时间的碎片,试图让它们也能发出光亮,写作、书法、绘画,还有收藏和阅读。当然也偶尔与新老朋友煮茶论道。这样算起来,留给写作的时间已少之又少,更何况,从40岁开始就给自己立下规矩,晚上绝不写作。写作需要时间,需要燃点,更需要一种心情或者激情,文学创作不是挤牙膏也不是写公文,没有强烈的写作冲动与欲望,创作不出好作品。这种时候,搁笔是最明智的。
中国的作家和写作人实在是太多了,多得像沙滩上的沙子;中国能发表的报刊和平台太多了,多得数不清楚;中国每年出版的书和发表的文章太多了,也多得数不清楚。我们真的不缺作家更不缺出版物,反而是少了能懂得适时搁笔的人和一种清醒的自觉。少出几本书或多几个不怎么勤奋的作家,尽可能少制造一些可有可无的文字,也是对祖先创造的伟大汉语的一种敬畏吧。
有时候我在想,当今这么大体量的文学创作,真正优秀或杰出的作品又有几部呢?包括那些层出不穷的各种大奖和好书榜,能在时间长河里存活几十年或上百年的经典又能有多少?曹雪芹只写了《红楼梦》前八十回,花了一生时间;蒲松龄穷尽一辈子,也只留下了一部《聊斋志异》。文学史上不朽的作品和人物,毕竟是寥若晨星,像苏东坡那样的天才和全才,这么一个泱泱古国,也就一人而已。所以老天爷是吝啬的,而时间更是苛刻和残酷的。文学创作如农人种地,区别只在农人是种地的而写作者是种字的。写在纸上或键盘上敲出的文字,有的落地就死了,有的可以活,但存活的时间很短,有的却可以长生不死。种出的字能长生不死,就是流传的经典。
一个真正对文学有抱负或使命感的人,他最不愿看到自己种下去的文字落地即死,对自己的作品总是有着期许,他们把作品当作个体生命的延续。古人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期望能流传千古,所以古人对于写作的态度与用心用力,以及不敢妄作,甚至如孔夫子这样的圣人竟“述而不作”,从中足以见出古人对文字的敬畏与审慎。老子这么伟大,《道德经》只有五千言;周敦颐是一座理学高峰,平生著述也就五千字左右。比起近现代著作家的创作体量天遥地远,更遑论当今写手尤其是网络写手一部作品动辄几百万字甚至是上千万字了。
我讲古人,并不是想否定今人,但无论今人古人,对于文字,都应该具有同样的审慎与敬畏。少制造文字垃圾,即是对母语应有的尊重,也是对自己、对社会甚至对后代负责任。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一直希望自己种下去的文字能存活得稍微长久些,尽量少生产垃圾,回归写作的纯净状态。佩服那些每年都有大部头问世的作家的勤勉,但自己却总是提醒自己尽量压制写作的冲动,要少写,如果觉得写出来的东西可有可无,那就干脆不写。这世间不会因为你少写或不写而缺了写作的人。写作者永远在写作的路上,最好的作品永远在下一部,大家这么做这么想,我同样不能免俗。
现在出版市场似乎遇到一些困难,没有了从前的火爆,但还是选出一些散文短章并破例选出一些自己的书画习作,合而为一,成为我的第一本书、画、文合体也即新“三体”作品集。读者看文章累了,可以翻翻书法或者绘画;翻看书画高兴了,可以读几页更能让你愉悦的文字。这样,我就不会给读者带来负累。希望这本“新三体”能带给您不一样的生活态度与快乐。
(《屋檐下的南方》,刘鸿伏 著,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