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蝉按:此推文后一篇文章《丘奇—图灵论点与人类认知能力和极限》与刘晓力老师的文章观点不同,本人在《丘奇...》文中有点评。欢迎阅读。
人工智能的逻辑极限
刘晓力
作者简介: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5
人大复印:《逻辑》2002 年 02 期
原发期刊:《哲学动态》2001 年第 .增刊 期 第 22-25 页
关键词: 人工智能的极限/ 哥德尔定理/ 认知可计算主义/ 认知的算法不可完全性/
摘要:“人的智能和人工智能的极限”已列入21世纪需要解决的重大数学问题清单,本文试图从 逻辑的角度对人工智能的极限问题进行探讨,特别指出哥德尔定理与人工智能极限之间的关 系,并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可计算主义”研究纲领提出质疑。
1.斯梅尔第十八数学问题
过去几十年计算机技术的巨大成就正在向人类智能发起挑战。“电脑能否代替人脑”,“ 人类心智是否会永远胜过计算机”,“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是否设定了人工智能不可克服的 逻辑极限”?这是哲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及其反对者们激烈争论的话题。
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是为了解决1900年希尔伯特提出的20世纪需要解决的23个数学问题之 一所得的数学结果。事隔100年,曾任美国数学会主席的斯梅尔又向全世界数学家提出了21 世纪需要解决的24个数学问题,其中的第18个问题是,“人类智能的极限和人工智能的极限 是什么”?并且指出,这个问题与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有关。
哥德尔定理告诉我们:在任何包含初等数论的形式系统中,都必定存在不可判定命题。有 了图灵机概念之后,它的一个等价命题是,任何定理证明机器都至少会遗漏一个真的数学命 题不能证,这就是数学的算法不可穷尽性。这一性质被许多人用来作为“在机器模拟人的智 能方面必定存在着某种不能超越的逻辑极限”的论据。
那么,哥德尔定理与人工智能的极限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哥德尔本人对此如何评价的?人 工 智能是否存在它的逻辑极限?
2.人工智能研究现状
人工智能方案起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1936年图灵首先以“图灵机”概念对算法概念给予 数学刻画,1950年又在《计算机器与心智》中提出“机器能思维吗?”这一重要问题,并设 计了“图灵测验”,为人工智能的研究提供了某种理论依据和检验方法。1948年维纳创立“ 控制论”,研究动物与机器中的控制和通讯的反馈控制原理及信息传输、信息交换和信息加 工过程等规律。1954年艾什比出版《大脑的设计》,开辟了以行为模拟的观点研究人工智能 的途径。1956年夏季,人工智能的先驱者麦卡希、明斯基、香农等人发起,在美国达特茅斯 大学举办“如何用机器模拟人的智能”学术会议,正式使用“人工智能”术语,成为这门新 的研究领域诞生的标志。从此以后,人工智能的研究分别沿着三个方向深入:
(1)机器思维方向;包括机器证明、机器博弈、机器学习启发程序及化学分析、医疗诊断、 地质勘探等专家系统及知识工程的问世。(2)机器感知方向;包括机器视觉、机器听觉等文 字、图象识别、自动语言理解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以及感知机和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3) 机器行为方向;包括具有自学习、自适应、自组织特性的智能控制系统、控制论动物和智能 机器人的研究开发。
半个世纪以来,人工智能在理论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三大研究纲领的变迁:
(1)符号主义学派主张思维的基本单元是符号,智能的核心是知识以及利用知识推理进行问 题求解,智能活动的基础是物理符号运算,人脑、电脑同样都是物理符号系统,人的智能可 以通过建立基于符号逻辑的智能理论体系来模拟;(2)联结主义学派断言智能活动的基本单 元是神经细胞,智能活动过程是神经网络状态的演化过程,智能活动的基础是神经细胞之间 的突触联结机制,智能系统的工作模式是神经网络模式,智能系统理论是基于非线性动力学 的系统论;(3)行为主义学派坚信智能行为是以“感知-行动”的反应模式为基础,智能水平 可以而且需要在真实世界的复杂境域中进行学习训练,在与周围环境的信息交互作用与适 应过程中不断进化和体现。
尽管1965年人工智能的领袖人物西蒙就曾预言,“20年内,机器将能做人所能做的一切。 ”1977年明斯基也曾预言,“在一代人之内,创造人工智能的问题将基本解决。”但是,几 十年里,虽经研究纲领的几次变迁,但三大派研究纲领仍未超出“认知可计算主义”的核心 ,因此在人工智能领域至今没有出现真正的革命性突破,而且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时地陷入不 曾预想到的各种困难。显然,关键之点仍是人的智能和计算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人类认知 的本质究竟是否是可计算的问题。
3.关于人工智能极限的鲁卡斯论证和彭罗斯论证 关于人工智能极限问题的争论也许最早可见1921年波斯特关于人心比机器优越的猜想。193 6年图灵发表重要文章《论可计算数》指出,“我们将假定需要计数的心的状态数是有穷的 。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承认心的状态有无穷多,它们中的某些状态就会由于‘任意接近’而 被混淆”。图灵的这段话曾被看作“人类心智活动不可能超越任何机械程序”的一个论证。 1950 年图灵在《计算机器与智能》中指出,我们不能因为一台机器不能参加选美大赛而责备 它,就像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没有飞机跑得快就责备他一样,机器也能够思维。这篇文章还 隐含着“人心等价于一台计算机”的论断,图灵的观点对当时刚刚兴起的人工智能方案无疑 是一强有力的声援,也自然引起了一场大争论。
1961年美国哲学家鲁卡斯在36卷《哲学》杂志上以极其激烈的言辞首先撰文《心、机器、 哥德尔》,试图用哥德尔定理直接证明“人心超过计算机”的结论:“依我看,哥德尔定理 证明了机械论是错误的,因为,无论我们造出多么复杂的机器,只要它是机器,就将对应于 一个形式系统,就能找到一个在该系统内不可证的公式而使之受到哥德尔构造不可判定命题 的程序的打击,机器不能把这个公式作为定理推导出来,但是人心却能看出它是真的。因此 这台机器不是心的一个恰当模型。这就是著名的鲁卡斯论证。随后,另一位美国哲学家怀特 利在接下来的37卷《哲学》杂志上发表了强有力的批驳文章《心、机器、哥德尔——回应鲁 卡斯》,遂引起许多人卷入并长达几十年的争论。1979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大奖的美国畅销书 《哥德尔、艾舍、巴赫,一条永恒的金带》将艾舍尔义蕴深刻的版画、巴赫脍炙人口的乐章 与哥德尔定理戏剧性地连接在一起,试图从多个视角阐明如何用哥德尔定理否证强人工智能 方案。1989年,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在风靡全球的《皇帝新脑,计算机、 心智和物理定律》中,对鲁卡斯论证又作了进一步扩展,指出计算机不过是强人工智能专家 所钟爱的一副“皇帝新脑”而已。被称为“哥德尔定理令人吃惊的强应用。”引发了1990年 《行为和大脑科学》杂志上许多人介入的一场争论。1997年和1998年当代语言哲学家塞尔相 继出版《意识之迷》和《心灵、语言和社会》两部书,断言,仅仅依靠单纯的输入输出,绝 不能担保人的意识,特别是意向性的呈现,因此计算机不可能完全模拟人的意识活动。
4.人工智能的极限不是哥德尔定理的直接推论
对哥德尔定理与人工智能极限之间的关系,哥德尔本人如何看待?从哥德尔的部分重要手稿 和70年代与王浩的谈话记录中我们得知,哥德尔在严格区分了心、脑、计算机的功能后作出 明确断言,“大脑的功能不过像一台自动计算机”,“心与脑的功能同一却是我们时代的偏 见”,但不完全性定理不能作为“人心胜过计算机”的直接证据,要推出如此强硬论断还需 要其他假定。
于是,“人心是否胜过计算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转换为几个子问题:(1)是否大脑和心的 功能等同?(2)是否大脑的运作等同于计算机的运作?(3)是否心的活动都是可计算的?这三个 问题实际上就是心脑同一论问题、大脑的可计算主义和心的可计算主义问题。
心脑同一论是50年代末以来西方颇为流行的占据主流的一种理论,也是人工智能的理论基 础。但哥德尔认为,心脑同一论是今日普遍接受的时代偏见。其中的一条理由是,根本没有 足够的大脑神经元来实现心的复杂的运作。在哥德尔的手稿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心的可计 算主义的批驳。
首先,哥德尔曾在多种场合申明,他本人并不反对用不完全性定理作为证明“人心胜过计 算 机”这一结论的部分证据,因为在他看来,不完全性定理并未给出人类理性的极限,而只 揭示了数学形式主义的内在局限,但是,仅仅使用他的定理不足以作出如此强硬论断。在 1972年的一篇评论中哥德尔指出,图灵给出的“心智过程不能超越机械过程”的论证在附加 以下两个假定之后才有可能:(1)没有与物质相分离的心。(2)大脑的功能基本上像一台数字 计算机,他认为(2)的概然性很高;但无论如何,(1)是将要被科学所否证的,是我们时代的 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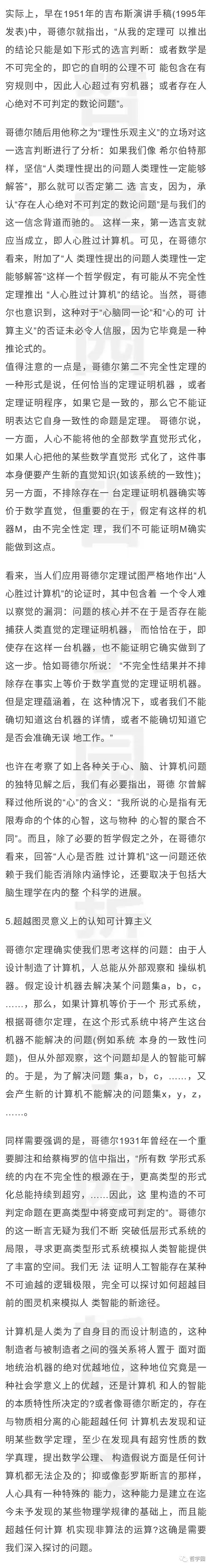
我认为,现在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们以上的讨论都是建立在图灵意义上的可计算 概念基础上的,目前人工智能领域也完全是在图灵意义上可计算概念基础上产生的“认知可 计算主义”的范式指导下工作。即使不论用一个形式系统表达图灵机的方式不唯一,我们也 应当考虑到,对于模拟人类智能的计算机,完全可以采用某种新型的形式系统,采用包含非 古典逻辑的具有动态性质的形式系统。同样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形式系统至少应当 保证紧致性定理成立,应当在原始递归的范围之内,这样一来,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就自然 成立,因此仍然没有超出哥德尔所言的逻辑极限范围。
那么能否构造新型的形式系统,它不是哥德尔构造不可判定命题的静态的古典逻辑的形式 系统?而且在这种系统中哥德尔定理不成立?更进一步,可计算性的概念是否可超越图灵机可 计算概念的范围,我们是否可寻求某种非图灵机理论模型去模拟人类心智,计算是否是人类 认知和智能活动的主要,甚至是全部内容,计算概念是否只能意味着图灵机可计算?
我们认为,人工智能,甚至整个认知科学正在面临着一场研究范式的转换,基于图灵可计 算概念的“认知可计算主义”研究纲领已经显示出其极大的局限,必将代之以“认知的算法 不可完全性”为核心的研究纲领。人类必将探索新的非图灵机概念来尝试解决人工智能更深 层的问题,以摆脱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困境。目前西方学者已经在探讨“超越(图灵机)计算” 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
丘奇—图灵论点与人类认知能力和极限
老蝉按:个人认为,这篇文章似乎是针对刘晓力《人工智能的逻辑极限》(今日上一篇发文)的。这篇的主要观点是:“能够与人类智能媲美的计算机完全可能问世。”;并引用图灵的话说“图灵早就指出:‘尽管它(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已经证明任何一台特定的机器都是能力有限的,但它并没有任何证据说,人类智能就没有这种局限性。‘”;“在我们看来,不可计算或不可判定问题的存在(以及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不仅是对计算机的限制,而且是对我们人类自己的限制——对人类认知的限制。”
这里的错误理解是:图灵机恰恰是必然受到哥德尔不完全定理制约的,即停机问题的不可判定,也即,这个不可判定是必然的(图灵机本身的设计就是01打孔,哥德尔构造的基础是算术形式系统,这些都是确定的。但人是否等价于这些,这本身还无法判定)。而图灵说哥德尔并没有任何证据说人类智能不受这种局限性,也是对的,同时,肯定性的答案---人类具有突破限制的能力也是没有充分证据的,这就意味着,人类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可判定性不是必然的,也即,这个不可判定性是不可判定的不可判定的......----至此,我们又看到了神秘的递归,就如哥德尔构造的命题 【 P:S中的一个命题,定义为:P在S中不可证,即 P:P在S中不可证】。这就是一种元思维,元思考。
本人更赞同今日发的刘晓力的文章中的观点(《人工智能的逻辑极限》),即:根据哥德尔不完全定理以及图灵1936的论文,根据他们各自的构造(图灵打孔机以及算术形式系统)已经证明图灵通用机和算术形式系统的局限性。而人,在此局限性上是否受限----肯定的或否定的答案或不可判定的回答----都还是不可判定的!而图灵机的停机问题(不可判定问题)已经是被证明了的(即,此不可判定问题已被“判定”)。
丘奇—图灵论点
与人类认知能力和极限
郭贵春 郝宁湘
作者简介:郭贵春(1952-),山西沁县人,山西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030006 郝宁湘(1963-),山西太原人,山西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湛江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030006
人大复印:《科学技术哲学》2004 年 11 期
原发期刊:《齐鲁学刊》2004 年第 05 期 第 65-70 页
关键词: 丘奇—图灵论点/ 人类认知能力/ 极限/ Church-Turing thesis/ human cognitive ability and limit/ countable infiniteness/ recursive rule/
摘要:丘奇—图灵论点是论述人类认知能力及其极限的一个重要背景。在此背景下,人类认知的无限性是一种可数无限性,人的认知能力受递归规律的限制,并且只能在递归的意义上认知事物。 对于非递归结构或非递归性质的事物,人只能做递归性的认知。计算神经科学为计算主义认知观提供了一定的证据。
一、引言
“计算”的概念对于认知科学的基本重要性,就像“能量”和“质量”的概念对于物理学的基本重要性一样,就像“蛋白质”和“基因”的概念对于生物学的基本重要性一样。没有计算的概念就没有把智力的研究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认知科学。马尔曾举例说,要理解人类的知觉如果仅仅研究人类的神经细胞,就像要理解鸟的飞翔只研究鸟的羽毛一样,是不够的。要理解鸟的飞翔我们必须理解空气动力学;只有理解了空气动力学才能真正理解羽毛的结构和翅膀的形状。计算理论的分析对理解认知和智力过程的重要性,就像空气动力学对理解飞行的重要性一样[1](P27)。无论人脑和计算机在硬件层次乃至在软件层次可能是如何的不同,但是在计算理论的层次,它们都具有产生、操作和处理抽象符号的能力;作为信息处理的系统,无论是人脑还是计算机都是操作处理符号的形式系统。这种符号的操作过程就是图灵机意义下的“计算”。
丘奇—图灵论点是可计算性理论中最重要的基本结论。它的确立,回答了计算的本质是什么、哪些问题是可计算的、哪些问题是不可计算的等这些人类曾长期探索过的具有重大哲学意义的问题。其意义不仅体现在数学、逻辑学、计算机科学等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大脑与认知的哲学方面。丘奇—图灵论点的人工智能形式是霍夫斯塔特所做的最后一个哲学拓展,也是其之所以给出这一系列哲学拓展的最终目的。我们认为,其拓展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接受的,它们为人们理解人类认知之本质提供了有意义的哲学观念。西方认知科学领域中占中心地位的计算主义学派,最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哲学思想。我们相信,计算主义这条路是颇有前途的。这里我们并不是说计算主义是唯一可行的途径。我们相信并认为,在探索人类认知、意识和大脑之谜的过程中,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理论会有着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积极作用。霍夫斯塔特是一位对人工智能持乐观、积极态度的学者。相信丘奇—图灵论点为人工智能的最终实现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不过我们与霍夫斯塔特有所不同:他所关注的问题是,能不能制造一台像人一样思维或认知的计算机。对此,他的答案是肯定的。而我们的兴趣或所关注的问题是,一种怎样的理论才能有效地解释人的认知。我们认为,丘奇—图灵论点对于人们创建一种有效的认知理论是极富启示性的,尤其对考察人类的认知能力和极限更有着最直接的指导意义。
二、不可解性与人类认知的可数无限性
我们认为,丘奇—图灵论点以及可计算性理论乃至整个数理逻辑科学,在哲学上,尤其在认知哲学上均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可以说,它们在最抽象的意义上有效地解释了人类认知的诸多现象和特征。特别是对人的认知能力和极限的认识有非常重要的启示。现实中,许多人似乎从来就没有经过认真地思考便不由自主地接受了人的认知能力是无限的、没有根本性限制的观点。我们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受了人的认知能力是无限的这种思想影响的人,当他面对20世纪许多最深刻和最令人难忘的“限制性或否定性”科学结论时,他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通常人们最熟悉的这种限制性成果大概要数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和海森柏测不准原理。不过我们这里要提到的是可计算性理论中的丘奇—图灵论点。从表面上看,丘奇—图灵论点是一个肯定性命题,但也正是基于这个论点,人们才有了对什么是不可计算性的明确认识,并在此基础上相继发现了一大批不可计算或不可判定的问题或命题,丢番都方程有无整数解问题、半群(群)的字问题、四维流形的同胚问题等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些事实的确定,逐渐让人们体会到,在数学和逻辑领域中,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度的。
首先,有了可计算性的精确定义,也就等于有了不可解性的精确定义,即对于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证明了其“没有相应的一般递归函数”或“没有相应的一般递归谓词”,那么就可以确切地说该问题是不可解的。这是在数学史上人类第一次认识到,从逻辑意义上讲数学中存在着不可解的问题。以往人们总是以为,任何一个精确表述的数学问题,总是可以判定它是对还是错,是有解还是无解。暂时没有解决,以后也一定会解决。现在看来,有一些问题是根本就不存在算法的,这无疑是对人类智力的一次最深刻、最严峻的挑战。在我们看来,不可计算或不可判定问题的存在(以及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不仅是对计算机的限制,而且是对我们人类自己的限制——对人类认知的限制。
其次,根据计算复杂性理论与丘奇—图灵论点,数学家把各种数学问题从其复杂性、难解性的角度作了如下一个分类:一是现实可解问题,即具有多项式复杂性算法的可以有效地解决的P类问题;二是理论上可解但现实不可解问题,包括仅有指数复杂性算法的较难的NP类问题、特殊的最难解的NPC类问题及“NP难的”问题和完全无法有效地解决的超NP类问题;三是理论上不存在任何算法的被证明为不可解的问题。这一结论无疑使任何数学问题都是可解的、甚至都是具有有效算法的幻想彻底破灭了,而这意味着:当我们费尽心思去求解一个数学问题时,我们可能是在求解一个不可解的问题;当我们绞尽脑汁去判定一个数学命题时,我们可能是在判定一个不可判定的命题。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可能已经包含了某些超越我们的智力所能把握的困难。而且由于数学家们还认识到,可计算函数共有可数无穷多个,而全体函数的个数却是不可数无穷的,因此不可计算的函数要比可计算的函数多得多(多无穷多个)。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可以求解的问题尽管是无穷的,但不可求解的问题更是无穷的,而且是更高层次的无穷。这便是可计算性理论等数学理论告诉我们的一个铁的事实。
最后,数学和科学是不完备的。基于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没有一个演绎推理系统能够回答所有的利用该系统的语言所描述的问题。每一个足够有力量的、一致性的逻辑系统都是不完备的——人们已经认识到数学是不完备的。同样,自然科学也是不完备的——自然科学的不完备性主要表现在存在着许多不可解的科学问题和一些否定性的科学结论。在一篇文章中,我们一方面根据人的认知的不完备性说明数学、科学的不完备性,另一方面又根据数学、科学的不完备性说明人的认知的不完备性。这似乎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循环论证之中,但我们认为,与其把这视为一个矛盾的循环论证,毋宁把它看作一个真实的现状。不完备的人创造了不完备的数学和科学,这不显得更真实、更符合逻辑吗?人类认知的不完备性正好通过自己的不完备的创造物得以显现,自己的创造物正是反观自己的最好镜面。
由此我们得到启示:(1)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是可求解的,一个问题没能求解,并不总是因为人们没有找到求解它的方法。我们相信,有些问题无法求解、是由该问题的本性所至,即使将来人类的思维更加发达,技术更加先进,这些问题也依然是不可解的,或依然是没有求解它的方法的。(2)理论上可解决的问题并不一定可现实地解决,因为任何问题都有它的时间复杂性和空间复杂性,时间和空间的极限就是求解问题的极限。在我们看来,理论上可解但现实上不可解问题的存在,更主要是对人类计算技术的挑战。无疑,计算不论是现代计算机的计算,还是中国古老的算盘计算,或是人脑的计算,它们在本质上都有一个物理的操作运行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需要最起码的运行时间和计算装置(空间),即计算存在一个基本物理极限。计算的时间复杂性和空间复杂性的存在正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对计算技术的深刻挑战。(3)人类认识(认识主体)的无限性是可数的、不完备的,而有待人类去认识的对象(认识客体)的无限性是不可数的、完备的。也就是说,尽管人类的认识是无限的,但人类认识(认识主体)的无限性远远小于有待人类去认识的对象(认识客体)的无限性。因而人类总有着永远也无法穷尽的世界奥秘,世界上存在不可知的部分或客体。换句话说,也就是人类不可能成为万能、全知的上帝。注意,我们这里并没有否认人类认识的无限性,人类的认识确实处于无限的发展过程之中。但是,如今从丘奇—图灵论点对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我们进一步看到,人类认识的无限性是一种递归无限性,有待人类去认识的对象的无限性是一种非递归的无限性。
三、丘奇—图灵论点对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
我们认为,丘奇—图灵论点最根本的哲学意义,就在于它表明了人类认知的一种计算主义特征,预示了人类的认知能力和极限,即它不仅是对机器认知的限制,而且是对人脑认知的限制。在具体论述前,我们首先明确一个前提,大家知道,认知科学的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方法论原则是,对认知和智力的理解应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来分析研究:第一个层次是最抽象的“计算理论”层次,它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计算的本质是什么?或认知的本质是什么?;第二个层次是“表征和算法”的层次,它关注的主要问题则是:计算或认知的具体方法是什么?是如何操作的?完成计算任务的效率如何?第三个层次是“计算的物理实现”层次,它关注的主要问题又是:实现计算的物质载体是什么?它是如何运转的[1](P24-25)?我们的论点主要是在最抽象的第一个层次即计算的层次上言说的。当然,也不排除其他两个层次。
确切地说,丘奇—图灵论点具体地表明了:(1)人的认知结构是一种递归结构;(2)人的认知过程是一种递归计算过程;(3)人的认知能力是受递归规律限制的,即人只能在递归的意义上认知事物。我们不妨把它称为“递归认知假说”。基于篇幅所限,这里我们仅就“递归认知假说”的第三部分做一论述。我们说人的认知能力是受递归规律限制的,人只能在递归的意义上认知事物,这包含两个含义:一是指人只能认知(计算)具有递归结构或递归性质的事物;二是指对于非递归结构或非递归性质的事物,人只能做递归性的认知。何以这样说呢?其实只要接受了认知计算主义纲领,上述观点便就是很自然的推论。因为认知计算主义纲领中所说的“计算”就是“递归计算”或“图灵计算”。西方认知计算主义学派的基本口号是“认知就是计算”,说的更具体些更确切些,实际上就是“认知就是递归计算”。既然认知就是递归计算,那么说人的认知结构是一种递归结构,人的认知过程是一种递归计算过程,以及人的认知能力是受递归规律限制的,即人只能在递归的意义上认知事物,便也就是很自然的了。不过下面我们还是给出我们何以提出这一更加具体明确的看法的几点理由;
(一)可计算理论或递归论是研究计算的最一般性质的理论,即并不是专门研究现实中具体的计算机的计算能力的,因而它的结论具有很强的普适性、抽象性。由丘奇—图灵论点所揭示的计算本质,它不仅包括数值计算、定理推导等不同形式的计算,而且包括人脑、电子计算机等不同“计算器”的计算,尤其在理论上还包括了DNA计算机、量子计算机等新型计算机的计算。大家不要忘了,以丘奇—图灵论点为基石的可计算性理论是在电子计算机诞生之前的30年代提出的,即它不是在对电子计算机进行总结与抽象的基础上提出的,但它又深刻地刻画了电子计算机的计算本质,如今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在本质上就是一台图灵机,并且人们又进一步认识到,目前尚在实验室阶段的DNA计算机、量子计算机,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图灵计算。这说明不同形式的计算、不同“计算器”的计算,在计算本质上是一致的,这就是递归计算或图灵计算。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丘奇—图灵论点是对一切“计算器”的计算能力的限制,进而也就是对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我们想,这或许正是由威格纳所说的“数学那不可思议的有效性”决定的。数学是研究模式的科学。这个模式既可以是一种现实世界的模式,也可以是一种逻辑可能世界的模式。而数理逻辑研究的模式是一种思维的模式、认知的模式和推理的模式。基于数学那不可思议的有效性,数理逻辑研究的这种思维的模式、认知的模式和推理的模式不仅是指人脑的思维、认知和推理模式,还包括一切非人脑——动物、机器等的思维、认知和推理模式。即具有高度的普适性、抽象性和有效性。另外,数理逻辑是人类大脑的产物,我们猜测,这种人类大脑的产物正好是反观大脑自身的最好镜面。我们相信,数理逻辑中许多具体的理论、定理,尤其是递归论、模型论中的理论、定理,均有着丰富而深刻的认识论意义和认知哲学的内涵;而且数学中人们只能解决具有递归性的问题,而对非递归性问题不可解的这一事实,是对我们上述观点的有力支持,亦可看作是一个例证。
(二)尽管理论上和现实中存在大量不可解的问题,但对这些问题人们也不是无所作为的,人们依然可以从计算的角度将问题按其计算的难易程度和复杂性进行分类、分层,从而进一步了解有关问题的特征或解的性质。另外,无论是理论意义还是现实意义上的不可解,指的无非是无法得到精确解、解析解,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得到近似解、概率解和局部解或弱解。对于一个不可解的问题,人们通常可以采取以下研究途径:(1)不去解决一个过于一般的问题,亦即不妄图去解决一大类问题,而是通过弱化有关条件把问题限制得特殊一些,来解决这个一般问题的特例或更窄的小类问题。(2)寻求问题的近似算法、概率算法。这是目前十分流行的研究方法。这就是说,对于不可计算或不可判定的问题,人们并不是袖手无策,而是依然可以从计算的角度,把不可解的问题——或为非递归问题、或为高指数复杂性问题——转化为递归问题或非指数复杂性问题,从而给予解决。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对于非递归结构或非递归性质的事物,人只能做递归性的认知。
(三)质疑和反对认知计算主义的人们的一个错误在于把某些问题计算机不能解决而人能解决这一暂时的事实绝对化。他们认为,尽管今天的计算机可以做人不能做的许多复杂工作,但在模式识别、感知和在复杂境域中决策的能力远不及人。确实,今天的计算机在模式识别、感知和在复杂境域中决策的能力远不及人,但这并不从逻辑上或从根本上构成对计算主义纲领的否定。因为今天的计算机在模式识别、感知和在复杂境域中决策的能力正在不断提高,至多只是提高的速度还不能让大多数人满意。这里我们也想提醒质疑者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计算机在模式识别等方面的发展还不足50年,而人的大脑却已进化了数百万年。要想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让计算机全面地达到人脑的水平,是不是太苛刻了些?在我们看来,从这个角度质疑认知计算主义纲领的朋友们实际上是对计算机提出了一个不现实的极其苛刻的要求。谁能料想得到百年后、千年后计算机的模式识别能力将会是什么样的?无疑,计算机不是万能的,计算机不能做的事有很多。但是,我们对这些计算机所不能做的事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比如非递归函数它是不能计算的,具有高指数复杂性的问题它也是很难解决的,不过这些也是人脑所无法解决的。质疑和反对认知计算主义的人们的另一个错误在于默认和假定了人脑能解决任何问题。这种假定实际上把人想象成了充满无限真理的一个无限复杂的有机体或无所不能的“上帝”,认为人脑可以进行无限复杂的各类认知(计算)。在我们看来,认为人的认知是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局限性或限制性,这是毫无根据的形而上幻想,是一种乌托邦。因此,只要放弃这种没有根据的幻想,我们就不难体会到丘奇—图灵论点也会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种限制。
(四)更有人认为,数理逻辑中的一些结论,尤其是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证明了计算机的能力是有限的,甚至认为,该定理表明了人工智能的极限,宣告了“人心永远胜过计算机”。对此,图灵早就指出:“尽管它(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已经证明任何一台特定的机器都是能力有限的,但它并没有任何证据说,人类智能就没有这种局限性。另外,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是不是表明了人工智能的极限,宣告了“人心永远胜过计算机”,这也不是像某些人说的那么简单。“电脑能否代替人脑”,“人类能否沦为机器的奴隶”,“人心是否永远会胜过计算机”?这是哲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及其反对者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的问题。在这一争论过程中,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一批具有数理背景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很难抵御用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论证“人心胜过计算机”的诱惑。因为哥德尔定不完全性理告诉我们,在任何包含初等数论的形式系统中,都必定存在一个不可判定命题。在有了图灵机概念以后,它的等价命题是,任何定理证明机器都至少会遗漏一个真的数学命题不能证,数学真理不可能完全归为形式系统的性质。这似乎表明,在机器模拟人的智能方面必定存在着某种不能超越的极限,或者说计算机永远不能做人所能做的一切。那么,依据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真能直接推出人的智能必定超过人工智能的结论吗?心、脑、计算机、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哥德尔本人对此又是如何评价的?有人依据近年来公布的哥德尔的重要手稿及私人谈话纪录,探讨了他对心—脑—计算机问题的认识[2]。根据有关材料介绍,哥德尔本人认为,仅仅依据他的不完全性定理不足以推出如此强硬的论断,需要附加其他的假定。在哥德尔看来,附加了“人类理性提出的问题人类理性一定能够解答”这样一个哲学假定,就能从不完全性定理推出“人心胜过计算机”的结论。即便如此,哥德尔也意识到,这种对于计算主义的否证未必令人信服,因为它毕竟是一种推论式的。然而在我们看来,想要附加的假定“人类理性提出的问题人类理性一定能够解答”本身就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数学中大量被证明不可解或不可判定的问题,难道不是由人类理性提出来的吗?只要承认丘奇—图灵论点,丢番图问题等的不可解就不得不承认。当然,寻求丢番图问题的近似解、局部解或弱解是可以的,但这已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不相干了。这个结果也许多少会超出某些人士的想象。我们认为,这是大家应该接受的一个十分客观的结论。
以上我们简要地阐明了我们何以认为“人的认知能力是受递归规律限制的,人只能在递归的意义上认知事物”的几点理由,类似的理由还可以举出不少,但我们知道,这些都主要是一些哲学思辨,而且很粗略。它的确认还需要更为严谨的论证和大量的例证。尤其需要从一般意义上确认“认知就是计算”这一基本纲领,使其不仅是一个科学假说,而且是一个能够通过各种检验和实证的科学命题。
四、来自计算神经科学的证据
确实,人们一直对计算机能否像人一样思维存在争论,目前已经问世的各种人工智能计算机远未达到人类的智能。但最新的研究表明,能够与人类智能媲美的计算机完全可能问世。根据这些新发现,一些科学家提出了生物计算机的设计思路。这些设想中的生物计算机运算速度和贮存容量将大大超过现有的电子计算机。而在这些生物计算机中科学家虽看中的就是DNA计算机。因为DNA上含有大量的遗传密码,它通过生物化学反应完成遗传信息的传递,这一过程是生命现象的基本特征之一。科学家认识到,DNA分子中的密码相当于存储的数据,DNA分子之间可以在某种酶的作用下瞬间完成生物化学反应,从一种基因代码变为另一种基因代码,反应前的基因代码可以作为输入的数据,反应后的基因代码可以作为运算结果,如果控制得当,那么就可利用这种过程制成一种新型计算机。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伦纳德·阿德拉曼博士提出的“DNA计算机理论”,就是这方面的开创性工作。生物计算机是人们多年来的梦想,它可彻底实现现有计算机所无法真正实现的模糊推理功能和神经网络运算功能,是智能计算机的一个突破口之一。当然,生物计算机的实现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DNA计算机理论的提出,以及个别案例在实验室中的成功运算,无不说明生物大分子不仅存储着大量的数据(信息),而且是按照“计算”的方式在处理数据(信息)。这一切为我们从分子水平上说明认知、思维是一种递归计算,提供了现代生物学的支持。
收稿日期:2004-05-05
[1] [美]D·马尔.视觉计算理论[M].姚国正,刘磊,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
[2]
刘晓力.哥德尔对心—脑—计算机问题的解[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11).
[3] 郭爱克.计算神经科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